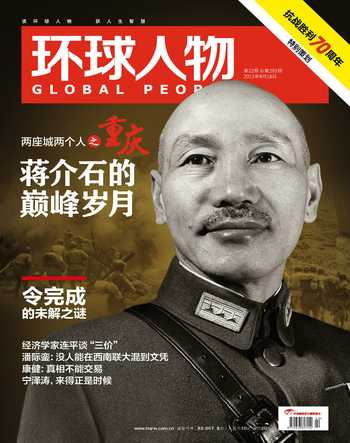姚遠,用筆保衛古城
王晶晶

姚遠,古城保衛者。1981年生于南京,1999年就讀于北京大學政治學專業,負笈燕園十二載,獲博士學位。其間曾赴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習。現任教于南京大學。
在文保圈里,姚遠是個特別的存在。其一,他年輕,正兒八經的“80后”。在為古城、古建、文化遺址奔走呼號的人里,白發蒼蒼的老頭居多,這么年紀輕輕的,少見。其二,他既不以歷史為專業,也不以建筑、規劃為專業,而是政治學出身,現在的本職工作,是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政治學系副教授,似乎和古城保護扯不上什么關系。
實際上,姚遠已有10年以上的“護城”歷史。他為家鄉南京奔走過,也為讀書期間生活過的北京而呼號,古都西安、韓城……都曾是他筆下的保護對象。
坐在《環球人物》雜志記者面前的姚遠,看起來平和而理性,說話字斟句酌。說起文保專家謝辰生等前輩學人,記者說是他的“盟軍”,他想了一下,感喟道:“是我格外尊敬的老前輩,算是同道中人。”
出生在一座著名的城市里,這是一個人幸福的首要的條件。——歐里庇得斯(古希臘哲學家)
姚遠是土生土長的南京人,小時候住在莫愁湖邊。明太祖朱元璋曾在南京修建了100萬平方米的宮殿,堪比現在的北京故宮。這座氣勢恢宏的宮殿,在曇花一現般地輝煌過之后,便隨著明朝遷都北京而衰敗,如今只剩遺跡。但南京城里,還留下一些珍貴的文化遺跡。姚遠年少時,喜歡在街巷里找古建、碑刻、柱礎,如同尋寶。
1999年,姚遠以南京市文科狀元的身份考上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來到另一個古都。他喜歡文史,旁聽過不少歷史方面的課程。閑來便在北京城四處逛,景山、鐘鼓樓、白塔寺……“我生活的南京、上學的北京是中國最后兩個古都,那些遺跡都是勾連現實的歷史,身在其中,你不自覺地就會有很多思考。”
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去探訪府學胡同的文丞相祠。姚遠看見了一塊石碑,上面鐫刻了文天祥的絕筆:孔曰成仁,孟曰取義。為其義盡,所以仁至。讀圣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后,庶幾無愧。“這種歷史‘現場’,具有一種讓人穿越時空與歷代先賢對話的魔力。”姚遠愛上了這種與時間對話的感受。他快樂地徜徉于歷史之中,沿著營造學社(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研究中國古代建筑的學社,朱啟鈐、陶湘等人創立,成員有梁思成、林徽因等)的足跡,踏訪大江南北的名勝古跡,并拍下很多照片帶到北大課堂上,引起了西方政治思想史任課教師許振洲的關注。許老師提醒姚遠:瀕危的不是這些名勝古跡,而是歷史名城里的那些尋常巷陌。
南京秦淮河沿岸的仿古建筑。
仿佛是在印證許振洲的話。現實中,一場“舊城改造”的運動在全中國轟轟烈烈地上演。2000年,北京出臺了危舊房改造五年計劃,整片整片的老城胡同在推土機巨大的鋼鏟下轟然倒塌。“大概是在2001年的冬天,一片殘陽之下,我看到從東直門到朝陽門兩個城門之間,方圓幾公里,一片廢墟,只有幾個文保建筑孤零零地殘留下來,特別痛心與震驚。明明兩年前去看的時候還很完整。”
回到家鄉,情況也令人堪憂。從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南京的歷史街區就因舊城改造而遭到嚴重破壞,剩下為數不多的明清街區,彌足珍貴。大四那年暑假,他拿著數碼相機,在南京顏料坊開始了古城保護的第一次拍攝。
一座城市就像一棵花、一株草或一個動物,它應該在成長的每一個階段保持統一、和諧、完整。——埃比尼澤·霍華德(《明日的田園城市》作者)
姚遠真正沖到“護城”一線是2006年的“南京保衛戰”。
那一年,南京市“建設新城南”城市改造項目啟動,將秦淮區、白下區的門東、顏料坊、安品街、釣魚臺、船板巷5處秦淮河沿岸歷史街區納入“舊城改造”的范圍,即將拆除。眼看著僅存的明清街區將被徹底清空,姚遠坐不住了。他拿起筆,寫下《關于保留南京歷史舊城區的緊急呼吁》,文中他寫道:“秦淮老街的拆與留,關系著老南京的死與生。”“秦淮之于南京,正如什剎海之于北京,城島之于巴黎,始終是南京最繁華的歷史城區,可謂是南京的城市之源、城市之根、城市之魂。”“這已是老南京僅存的最后的一點種子。如果這些秦淮老街都在舊城改造中蕩然無存,南京歷史文化名城也就名存實亡了。”他犀利地詰問:“600多年來,秦淮老街沒有毀于清軍入關、太平天國等歷次內戰,也沒有毀于日本侵略者的炮火,難道卻要徹底毀在我們這代人的手上嗎?”
這封飽含深情的呼吁信,姚遠發送給了300多位文物保護專家、政協委員、人大常委等,他希望他們能挺身而出,阻止拆毀老城。郵件寄出后的第二天早上8點多,姚遠一打開手機,就接到了第一個回復電話。對方說:“我是謝辰生啊。”姚遠一聽,就知道南京有救了。
那封呼吁信,最后得到了歷史地理學泰斗侯仁之、兩院院士吳良鏞、建筑學家傅熹年、考古學泰斗宿白等16位前輩學人的聯名響應,他們作為呼吁人,促成時任總理溫家寶派人到南京調查。2008年,在國家領導人的批示下,《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條例》出臺。
2010年,姚遠獲得國家文物局指導、中國博物館學會等幾家單位評選的“中國文化遺產保護年度杰出人物”。對他的評語這樣寫道:“一支筆,是他的武器;一份堅持,凝聚著他的毅力。曾經的高考狀元,如今用行動保護城市靈魂,用努力傳播文保理念,用執著維護城市的古樸。”
由于城市太復雜了,所以你可以設計房子,但永遠設計不了城市,而且也不應該去設計城市。——凱文·林奇(美國知名城市規劃師)
雖然有法規、文件、學者的呼吁,“拆舊仿古”依然是當今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重頭戲。不要說歷史街區,連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蔣介石在重慶的行營都遭到“保護性拆除”。據謝辰生的整理,2010年以來在陜西、河南、山西等十幾個省份,共有40多個城市啟動古城改擴建項目。
姚遠很慶幸自己早年沒有轉專業去學歷史。“你會越來越感覺到一個問題:如果只是在書齋里而沒有行動,真正的歷史可能已在推土機下消失。我曾對一位歷史學教授談了我的看法:當我們研究北京寺廟和胡同的關系的時候,如果寺廟都沒有了,胡同也沒有了,討論的基礎也就消失了。”
和謝辰生聊天時,謝老也跟姚遠講過類似的問題。當年,鄭振鐸叫謝辰生去做文物保護工作;謝說:“我可以做學術啊,比如跟你去中科院考古所做研究。”鄭先生說:“保護是第一位的,沒有保護就沒有研究。”所以謝辰生做了一輩子文保工作。
在姚遠看來,保衛古城,政治學是必須要介入的。“古城在過去二三十年里遭受的破壞,是幾千年來從未有過的。這背后有文化因素,但只是小部分,更多是利益原因,背后有各種博弈、對利益的分配,這就涉及政治權威的選擇、衡量和強制,要國家權力的約束,這都是政治學的問題。從更大的層面上說,是公眾領域的問題。只有走出書齋,和政府打交道,你才能推動這些事情,同時才能知道我們的政府運作出了什么問題。”現在,他正在將這些政治學的思考,用學術論文的方式一一呈現。
在姚遠新出版的作品《城市的自覺》里,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在序中評價他“顯示出‘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難得的不僅是情懷,更是行動。古建改變了姚遠,姚遠也在改變著他身處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