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芾:安靜是一種氣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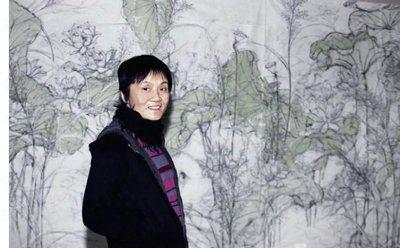
在萬芾的藝術作品中,追求完美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而完美的追求最終所要體現的,還是平凡中的美麗。
每一次在各大畫展中看到畫家萬芾的花鳥作品,都會給人以美的享受。在琳瑯滿目、五彩紛呈的展品包圍中,她的作品總能以安謐和寧靜打動每一個觀眾。那些看似簡約的畫面,糅合著平面構成的因素,精心營造出的溫暖氛圍,烘托出那些生機勃勃的小鳥,蘊含著生命的律動。常常會令人想起蒙田的那一段話:“在我看來,最美麗的人生是以平凡的人性作為楷模,有條有理,不求奇跡,不思荒誕。”因為“知道光明正大地享受自己的存在,是神圣一般的絕對完美”。因為悅目畫面的背后,是美麗的人生;美麗人生的背后,是平凡的人性。可以說,在萬芾的藝術作品中,追求完美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而完美的追求最終所要體現的,還是平凡中的美麗。正如上海美協主席施大畏所評價的那樣:“紛繁喧囂的都市生活,反襯出萬芾繪畫的平靜和安寧,這是一種脫俗的意境,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萬芾的生活態度和藝術理想。”
的確,萬芾用她的七彩畫筆,將天地間的花樹飛鳥邀集到宣紙上,向世人展現出氣象萬千的奇美景象。她的畫作中,生靈飛動卻幽謐靜美。繁花在云霞中靜靜綻放,枝葉在月光下自由纏綿,神態安然的鶯雀在花香樹影中駐足、踱步、鳴唱、飛翔……面對這樣的畫面,感覺到的是大自然的優美靈動和寧靜祥和。而這富有詩意的美好,來源正是傳統繪畫的滋養與時代氣息的潤澤。兩宋時期的院體花鳥畫以嚴謹的構圖、生動的形態、富麗的色彩、嫻熟的技法一直是工筆花鳥畫學習者的范本,萬芾也不例外,在進入上海工藝美術學校中國畫專業學習時,她接觸了宋代工筆花鳥畫,后又觸及南宋院體畫家李迪、明代院體畫家呂紀等名家作品,通過臨摹與研習,寫生與創作,授課與編寫教材,使她對于傳統花鳥畫有了較為深入的理解。后來,萬芾又到中國美術學院裝潢設計系、華東師范大學美術教育系學習,先后完成大學專科、本科學業。這些學習經歷在她以后的藝術創新中都起著頗為重要的作用。
在“98上海百家藝術精品展”和“海平線98繪畫、雕塑聯展”兩個重要的市級美術展覽中,萬芾的作品開始引起人們的關注。鮮艷、豐富的色彩,現代而不失傳統韻味的構圖,令人耳目一新。萬芾始終覺得,傳統雖好,但是與我們所處的時代畢竟相隔太遠了。現代人身處的城市環境、時尚的審美趣味、面臨的生態困境,以及多元的藝術影響,都使得今天的藝術創作不得不考慮現代人的精神需要,創作出順應于現時代社會生活的繪畫作品。于是在新世紀里,萬芾帶著她的花鳥畫開啟了一個新的里程,向著當代審美趣味遷徙。
她先是吸取了西方現代藝術中的構成主義,在畫面上,拆散了傳統花鳥畫的折枝架式,營造了一個帶有一定秩序的花鳥世界:花卉被重新組合,構成一組組具有相對獨立,又相互之間有關聯的群體,花草舒展著柔美的姿態,小鳥們棲息在猶如童話般的世界里,安寧、平和。可以說,萬芾在這一時期的花鳥畫中所表現的已不是傳統繪畫中的文人情懷,也不是對大自然美景的真實描繪,而是意在透露畫家心中的美好情感和愿望。在這種似真實又非真實,似虛幻又非虛幻的畫面中,洋溢著畫家的理想主義精神。
接著,萬芾的藝術探索又深入一步。這一步是把花鳥的形態減弱到最簡練的境地,色彩變得更為單純,畫面變得更為空靈,意境由寧靜轉為純凈。與此同時,在花鳥的背景上開始隱隱約約地顯出抽象的幾何圖形,虛幻空間的作用有所增強。可以說,此時畫面所體現的象征意義、比興的傳達含義已被完全消解,代之而起的是突出表現了現代人的心靈感受和精神體悟,城市的象征性漸漸地清晰了起來。借由此,萬芾表達了她對于現代城市建設的一個觀點:即有水的、鳥語花香的生態環境,才是理想的宜居城市。
與自然對話
《新民周刊》:我們知道,出生于上世紀60年代的萬老師從小喜愛繪畫,但您的求學道路卻頗為漫長,連續進過三個學校,是么?
萬芾:對。記得那時剛恢復高考,工藝美校繪畫系就招收了我們這一批學生。至今我的同學依然活躍在上海畫壇的已經不多,不少人都很好奇,問我怎么那么有耐心,哈哈。其實我就是喜歡畫畫,畫我喜歡的花鳥畫。
我們在學校的三年,接觸了不少老先生,包括申石伽、曹簡樓老師等等,還有許韻高、蔡天雄等老師。花鳥、山水、人物、書法、理論……都要學習。在求學時期,我開始喜歡上了工筆畫,覺得這樣安靜、雅致的創作方式很適合自己,也符合我的性格,于是就開始花比較多的精力在這上面。畢業后我被分配去畫絲綢圖案,工作了三年。隨后學校又把我招回來,就這樣從事教學工作至今。
后來我又去了中國美術學院裝潢設計系進修,又去了華東師范大學美術教育系讀書。一方面是因為工作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對自己的一種進修,學習。
《新民周刊》:從對傳統中國畫全面的學習繼承,到選擇花鳥畫為主攻方向。您是如何考慮的?
萬芾:我從小喜愛繪畫,后來選擇花鳥畫,因為這一科特別強調寫生、觀察的重要性,自然界的花鳥草蟲,不經意間有著屬于自己的獨特之美,我的愛好就是去觀察、發現自然界中往往令人注意不到的細節之美,并將此表現出來。所以在創作中,我有一種“來自自然,融會自然”的心境。
《新民周刊》:的確,中國的花鳥畫,古往今來,繁華似錦,萬涓成海,名家輩出,無論工筆寫意,出類拔萃者前赴后繼。每個時代,都有大家引領風騷,讓后來者欽服驚嘆。新生代的中國畫家,要在這古老而強大的傳統中獨辟蹊徑,畫出新的風采意蘊,絕非易事。而您的花鳥畫,讓人感覺到一種新鮮的氣息。善于以小見大,以靜思動,于繁復中顯單純,于工整中見飄逸,能把人引入美妙的天然勝景。
萬芾:前幾年我畫了一百種花卉,現在開始打算畫一百種鳥,計劃今后出一本大畫冊。為什么想做這樣一件事?我就是希望,在藝術多元化的今天,能讓喜歡畫畫的年輕人看到,原來運用傳統繪畫方式,是可以把大自然表現得很美的。
說起我們的繪畫傳統,前提就是如何繼承發揚,因為傳統很成熟很偉大,很難超越,同時畫者又很難另起爐灶。因此,如何在新時代畫中國畫,成了一個核心問題。目前,我的繪畫還是尊重傳統的,但會在材料上做一些探索,比如線條運用上,我喜歡在生宣上勾線,因為這樣有韻味感,包括設色,也不是很傳統的,學習了一些西方裝飾色彩的原理,變得更鮮活明快一點。我一直對學生說,要想中國畫的色彩用得好,一定也要去了解西方的繪畫色彩和裝飾色彩,要了解色彩的語言和處理方法。其實用顏色與畫線條一樣,用的不同,表現出來的情感變化就不同,所以我主張應該都去學一些,各種顏色都去畫一畫。
《新民周刊》:正如作家趙麗宏所說:“萬芾是一個性情安靜的女畫家,她不張揚,不浮躁,雖然生活在熱鬧的都市,卻能以一顆沉靜的心觀察自然,諦聽天籟。天地間的樹木花草,在她的眼中都是曼妙可親的摯友,而棲息翔游于花樹中的花鳥蟲魚,都是她的知音。自然彌漫在心田,天籟回漾在胸臆,她的筆墨才會如此豐沛傳情。”我想,在您的花鳥畫藝術中,除了對傳統技法的繼承,在創新上,您也是做了大膽的嘗試的,使之更具有現代感。
萬芾:我覺得,繪畫與設計有差距,畢竟是兩個領域,但之間是有相關聯的東西。設計對我的創作就有影響。我曾就讀中國美院設計系,后來對我花鳥畫的構圖的確有幫助。我在畫面上借鑒了一些現代設計中構成的元素,畫面上的花卉開始有一些橫向、縱向交疊的排列,有時候帶學生去園林里寫生,看到許多窗格也是這樣排列的,就很受啟發。后來有一次去山里寫生,發現真有我畫里的那種九十度彎曲的枝條!我們說,心靈感知自然,沒想到有時候自然也能印證我們的心靈,那真是很開心的。就像徐明松先生所說的那樣:“萬芾的作品具有一種通感,源于其作品畫面充滿節奏和諧的意象構成。她的作品畫面已非傳統花鳥畫的構圖,尤其她的水墨作品,構圖簡約而意象豐富。頗有現代構成性,規整而不失趣味,線面結合空間織體,化平面為三維空間。諸如,折枝的交錯與掠風而舞的橫枝斜葉形成了節奏明確而深具書寫性的線條組織,與此同時,烘染點皴而成的墨色塊面如水中之渚,若平林阡陌,意象層層疊疊雋永無窮。而畫面上的留白,界破稍顯滯重的墨塊,造化成往復上下貫通左右的一股靈動之氣,似光非光,似云非云,將紙上繁華幻化出一片諦聽天地萬籟,洞觀宇宙生靈的別樣世界。這是生命的歡歌。”
《新民周刊》:您將這種流動生變寄情于筆墨,在西方構成與東方書寫性的結合上相契合,臻成意境。這是自然生機蓬勃的再現與抒寫,無疑也是人與自然的和諧對話。
萬芾:一幅藝術作品,無論是傳統的還是當代的,首先是要耐看,也就是技法上的成熟與豐富。然后就是意境,要體現畫家的所思所想,表現出畫家獨特的審美與趣味,這是很重要的。
為城市思考
《新民周刊》:盡管在花鳥畫上成就斐然,但其實您還是個畫壇多面手。仕女人物、靜物山水,甚至現代城市的風景等等,都有所涉獵。特別是您曾為《上海文學》連載的小說畫插圖,精心構思的那些工筆白描人物,畫出了作家筆下人物的各種情態,令人稱贊。
萬芾:從我的經歷來看,越發體會到,堅持很重要。我選擇畫畫,一直在堅持,當然過程中必然有曲折和困難,但總的來說很開心,而且一路走來,好多老師、朋友始終在鼓勵我,幫助我,令我感動。在上海中國畫院高研班進修時期,像施大畏老師、韓碩老師、馬小娟老師等,對我的創作幫助都很大,他們對我既嚴厲批評又不乏熱情鼓勵,還提出很多具體的意見幫助我,讓我收獲很大。再比如作家孔明珠老師,是我的好朋友,她也常常鼓勵我,還幫我寫了不少文章。還有趙麗宏老師,就是他邀請我為他主編的《上海文學》畫插圖,從中我也得到了很多鍛煉。
《新民周刊》:近年來,在形成鮮明藝術風格的基礎上,您又求新求變,把自己的工筆花鳥從五彩繽紛中拉到了純粹的水墨世界里。然而,在熟悉您的人看來,這一步看似走得突然,其實又是在情理之中。這是為什么?
萬芾:因為當象征城市的抽象圖形出現之后,當筆下的花鳥脫離了大自然的懷抱之際,我所追求的藝術表現就脫離了現實的束縛,力求做到介乎傳統與現代之間的自由境地。而水墨形式也許是表現這種境界最為合適的一種選擇。同時,為了避免象征城市的幾何圖形出現的硬邊化和平板化,我就借用了傳統的點墨法,集點成面,使得這些大小不一、橫豎各異的矩形塊面泛起粼粼波光,猶如建筑物的水中倒影,閃爍著城市的光影……有趣的是,我畫上的小鳥卻始終保留著傳統的工筆技法,勾勒,渲染,平罩,絲毛,一步不缺,朋友們戲稱“小鳥儼然成了傳統的守衛者”。 因為小鳥們見證了我在藝術上的起步,所以在這些小鳥的圖像上,我忠實地保持著傳統繪畫的痕跡,顯現著現實生活的真實,這應該說是我的有意為之。同時,為了讓工筆花鳥與水墨抽象的城市圖形和諧地相處,我又對生宣作了熟化處理,使得兩者的融合更為自然。
其實水墨畫的表現效果是十分豐富的。傳統里說墨分五色,其實不單單五色,像西洋畫一樣,水墨也是有高低調的,我覺得如果研究進去的話很有意思。水墨畫如果按照調子來處理,變化會非常豐富,這種探索與發現讓我很愉快。
《新民周刊》:可不可以這樣認為,您是用獨特的,屬于您自己的花鳥畫藝術語言,來為這個城市的生活環境而思考?
萬芾:是的,盡管這樣的畫法很累,需要花巨大的精力與時間。但我覺得,城市山林的概括及抽象,與充滿舞蹈感和書寫性的折枝、片葉,以及顧盼生情的禽鳥的工筆寫實相對位,會使畫面在靜謐之中變得一下子生動起來。將冷厲的城市空間架構與柔和的花鳥相遇,是古典的矜持與當代開放的相遇,沒有尷尬,也沒有城市的喧囂,留下的是安靜的審美意趣。這也是我對城市生活與自然世界相融合的一種愿望。
《新民周刊》:您置身于城市的水泥山林中,心里看見的是出塵的花鳥世界。靜以修身,悠然入畫。使得您本人仿佛也成了花鳥世界的一分子,生機盎然,華滋豐茂,給人以不凋的美感。
萬芾:由繁入簡,表現的是生命的體驗,自身的感受。安靜是一種氣質,一種意境,這其中包含著謳歌生命萬物的灼灼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