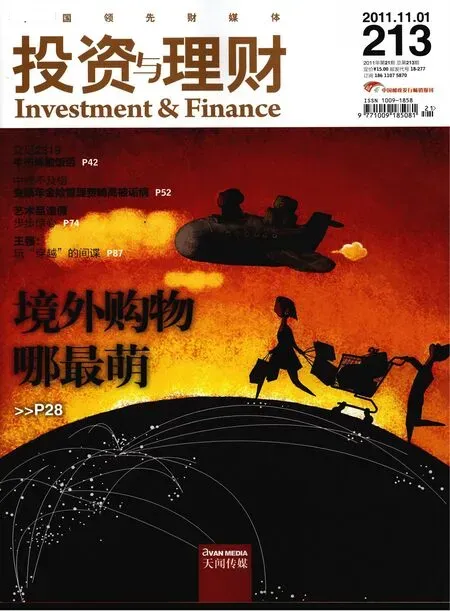李嘉儒:筆墨越過思想禁忌
趙子龍

幽浮香NO.3 80×40cm 紙本設(shè)色2015

幽浮香NO.2 80×40cm 紙本設(shè)色 2015
一直以來,李嘉儒都致力于用工筆水墨的方式營(yíng)造一種曖昧、朦朧、冷艷的女性場(chǎng)景,許多第一眼見到李嘉儒作品的人都會(huì)因?yàn)檫@種唯美、輕盈的情調(diào)和精致的筆墨而心生喜歡。然而,大多數(shù)人止于這種表面的審美愉悅感便已滿足,從而將他規(guī)定為一個(gè)傳統(tǒng)工筆畫家。實(shí)際上,并不是所有的工筆都是“傳統(tǒng)”,正如并不是所有的寫實(shí)繪畫都是“古典”一樣;工筆只是一種大家熟悉的技術(shù)手段,用這種傳統(tǒng)的技術(shù),照樣可以做“不傳統(tǒng)”的事情。李嘉儒就是這樣一個(gè)有意思的案例,他畫的是工筆的樣子,但想的卻不僅僅是工筆的事情。許多人能夠看出他的不同,但即便將其稱為“新工筆”以區(qū)別他與畫院那些根正苗紅的工筆畫,仍然不能體現(xiàn)出關(guān)鍵之處。
即使在工筆的價(jià)值范疇內(nèi),李嘉儒仍然做得很好。生長(zhǎng)于山西的李嘉儒雖然個(gè)性活躍,但可以看出內(nèi)心樸實(shí)、穩(wěn)重,而且有中國(guó)人熟悉的自我約束和道德規(guī)范,這些品質(zhì)在他為人處事上可見一斑。具體到繪畫中,他從不借傳統(tǒng)文化的名義將自己引向玄虛和神化,不刻意追求觀念化,而是始終落實(shí)到繪畫技術(shù)上。他曾在創(chuàng)作的過程中讓我看他對(duì)人物頭發(fā)的描繪,的確精工細(xì)筆,一絲不茍,不以平涂草草了事。由此可見,他并未忽略、回避工筆繪畫中獨(dú)有的價(jià)值:在時(shí)間中最大限度將自身體驗(yàn)注入繪畫語(yǔ)言——這是工筆繪畫對(duì)藝術(shù)語(yǔ)言體系的巨大貢獻(xiàn),也是崇尚理性、現(xiàn)代性的西方世界一直偏愛中國(guó)古典思想的重要原因。在這個(gè)時(shí)代的語(yǔ)境中,工筆繪畫仍 然有其自身的價(jià)值:修復(fù)中國(guó)因“文革”和歷次思想改造運(yùn)動(dòng)而殘缺的文化傳統(tǒng),進(jìn)而有望在我們生活的時(shí)代激活文化基因,重建局部的文化共識(shí)。今天看來,工筆這種繪畫方式更多與中國(guó)古代工藝思想價(jià)值體系相關(guān),與水墨并不太相關(guān);只不過中國(guó)繪畫史慢慢進(jìn)入以文人主導(dǎo)的歷史后,“工筆”“工匠”被冠以“匠氣”的評(píng)判,慢慢被邊緣化,直到今日還左右著許多人的思維。李嘉儒因?yàn)椤皩?shí)在”,在這個(gè)問題上有著很清醒的認(rèn)識(shí),他對(duì)工筆技術(shù)并無偏見,反而極其重視。誠(chéng)然,工筆 是實(shí),水墨是虛,文人看待歷史,過于避實(shí)就虛,從而使得中國(guó)古典思想帶有一定的偏頗性,也多少阻礙了中國(guó)理性思維的建立,在這個(gè)意義上,李嘉儒重視具體技術(shù)的思維對(duì)我們這個(gè)時(shí)代的藝術(shù)有啟發(fā)意義。

女人香 NO.2 80×30cm 紙本設(shè)色 2014

幽浮香NO.7 60×40cm 紙本設(shè)色 2015

幽浮香NO.5 60×40cm紙本設(shè)色2015
從另一個(gè)角度看,李嘉儒雖然重視技術(shù),但又并非想極端強(qiáng)調(diào)一種古典工藝價(jià)值觀。因?yàn)闊o論如何,工筆繪畫思想仍然屬于一種過去的知識(shí)體系,它存在于一種古典的知識(shí)權(quán)力系統(tǒng)中,這種權(quán)力系統(tǒng)并不適用于當(dāng)代。中國(guó)古典權(quán)力系統(tǒng)對(duì)人性的壓制,主要基于兩個(gè)方面:制度上不斷強(qiáng)化等級(jí)意識(shí),思想上不斷強(qiáng)化道德訓(xùn)誡;所以中國(guó)歷來的變革就是針對(duì)兩個(gè)方面,一是文化改革,一是制度改革。在制度變革方面,主要發(fā)力的是政治改革和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改革,90年代以來的中國(guó)前衛(wèi)藝術(shù)也局部參與了制度改革;在文化改革方面,則由80年代以來詩(shī)歌、文學(xué)、音樂、繪畫等偏現(xiàn)代主義、理想主義的藝術(shù)開啟。在這變革進(jìn)程中,原先那些基于古典思想的水墨繪畫也出現(xiàn)分化,一部分人仍然陷入對(duì)古典知識(shí)的迷戀中,以拒絕新事物和新知識(shí)為代價(jià);而另一部分人意識(shí)到滯后的危險(xiǎn),開始主動(dòng)促 成水墨的進(jìn)化——于是有了新水墨、新文人畫、新工筆。這種進(jìn)化存在著各種局限性,尤其在近期中國(guó)區(qū)域藝術(shù)市場(chǎng)對(duì)水墨的狂熱中,水墨的變革更是成為一種表態(tài),或者局限于材料和視覺上的差異,而缺少實(shí)質(zhì)進(jìn)展,許多宣稱完成水墨當(dāng)代轉(zhuǎn)化的人們,實(shí)際上仍然生活在古典的知識(shí)體系之中。
李嘉儒所做的,是在保留工筆技術(shù)和水墨氣質(zhì)基礎(chǔ)上,尋求一些其他的變化。他選擇了一種充滿情調(diào)的、極富感官體驗(yàn)的女性形象和色彩,以及精致的筆墨線條,第一時(shí)間吸引觀者的進(jìn)入,不像許多拋棄視覺而追求觀念的水墨那樣始終與觀者有著天然的距離,必須靠額外的語(yǔ)言文字來彌補(bǔ)。然而,他的工筆繪畫并不止于提供一種大眾熟悉的繪畫形象,不是以繪畫的方式復(fù)述古人的思想,而是試圖穿越古典思想中設(shè)置的禁忌,這是李嘉儒的真正意圖。中國(guó)古典權(quán)力體系中以道德名義設(shè)置的思想禁區(qū)中,以情色最為明顯——這是因?yàn)椋谇樯@種天然欲望中所獲得愉悅、快樂,最不容易彰顯等級(jí)特權(quán),這是一種連最卑微的百姓都能享受的快樂,這是唯一能夠憑借生命超越權(quán)力的力量,所以歷代統(tǒng)治階級(jí)在這一點(diǎn)上極為森嚴(yán),以 至于產(chǎn)生太監(jiān)制度。古典觀念之所以過分強(qiáng)調(diào)羞恥意識(shí), 正是這種權(quán)力在文化中的體現(xiàn)。李嘉儒描繪的一系列香艷、嫵媚、大膽的女性,顛覆了道德體系中的女性形象,揭示了女性作為生命體在古典思想中被遮蔽的氣質(zhì),使得水墨這種充滿道德色彩的藝術(shù)材質(zhì)可以直面人的真實(shí)欲望,這在以往以教化和清欲為主的水墨繪畫中是不曾有過的涵義。同時(shí),他并沒有以犧牲工筆、筆墨來?yè)Q取這種突破,反而盡最大可能保持了這些作品在視覺上與傳統(tǒng)的連貫性,讓這種穿越禁忌的意圖更加清晰。這也讓李嘉儒的繪畫有了多元性,觀者可以欣賞其工筆技法本身的價(jià)值,也不妨可以滿足視覺和心理愉悅,作為時(shí)尚用途也未嘗不可——同時(shí)其突破道德禁忌、指向人性真實(shí)的觀念不曾流失。所以,我覺得李嘉儒的繪畫盡管看起來很傳統(tǒng),但它們與那些致力于強(qiáng)化傳統(tǒng)道德的水墨恰恰是兩條不同的路:那些沉湎于傳統(tǒng)趣味中的水墨在走回頭路,而李嘉儒卻以看似傳統(tǒng)的手段向著當(dāng)代思想行走。
更讓我欣賞的是,李嘉儒在表達(dá)這種人性解放的觀念時(shí),并沒有以傳統(tǒng)水墨那種教化的口吻出現(xiàn),而是以一種近似幽默的智慧表達(dá):當(dāng)我們一方面滿足于那種香艷的心理愉悅感,一方面卻習(xí)慣于推崇傳統(tǒng)繪畫中那種強(qiáng)調(diào)清心寡欲的意境時(shí),我們會(huì)發(fā)覺自己已經(jīng)陷入一個(gè)小小的悖論——這正是李嘉儒善意的設(shè)計(jì)。這種設(shè)計(jì)提醒我們穿越文化帶來的禁忌,直面自己真實(shí)的人性,卻又并不讓人反感,這本身就是一種符合人性的言說方式。
- 投資與理財(cái)?shù)钠渌恼?/dt>
- 作為收藏家的乾隆皇帝
- 消失于自己時(shí)代的李青萍
- 碧璽為何稱霸彩寶界
- 秋拍觀察:價(jià)格壓力無處不在
- 雅致與精致
- 薰衣草之外的普羅旺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