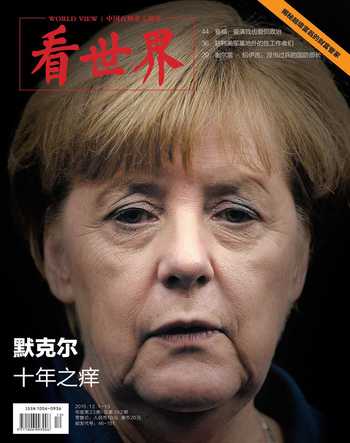揭秘超級富翁的財富管家
布魯克·哈靈頓

莎士比亞說世界就是個大舞臺,社會學家爾文·戈夫曼則在此基礎上說“最有趣的部分通常都發生在舞臺背后”。財富管理行業總的來說就是舞臺背后不為人知的那點兒事。
盡管很多人對這個行業本身并不熟知,但大家不陌生的是各國政府對超級富豪們的那點小心思——除了在他們身上征收可觀的稅賦以外,還尋求對他們增加法律上的監管。這就使得這些高凈值人士開始想方設法地躲開權力機構的“魔爪”。
目前,全球范圍內大約有10.3萬名超高凈值人士,即擁有3000萬美元或更多的可投資資產。普通大眾難以接觸到這些超高凈值人士背后的財富管理行業,一方面是因為從業人員真的很少(全球大約不到兩萬名);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他們的保密條例不僅要求嚴守客戶的秘密,還需要盡可能地保持低調。
比如在2012年的美國總統選舉中,共和黨提名候選人米特·羅姆尼就被媒體爆料稱已經將個人約2.5億美元的財產轉移到了離岸信托和銀行賬戶里。這一做法可以合法地將其收入稅率降低至約15%。在這背后,財富管理公司功不可沒。
與此同時,公益機構樂施會則預計到2016年,全球約1%的人口將會掌握全人類超過50%的財富總量。需要指出的是,這種情況的形成并非什么市場經濟的自發結果,它甚至不應歸結到那些“貪得無厭”的大資本家身上——他們只顧每天用鈔票消遣即可,避稅、訴訟以及逃離監管什么的,有的是專業人士來操心。
為了更深入地了解這個行業,我決定來一次視角獨特的專業調查——以一個財富管理人的身份去觀察這個行業本身。
在我“假扮”成財富管家之前,有關的基礎訓練必不可少。為此,我在瑞士和列支敦士登的多個地方閉關數周學習了公司法、金融投資以及會計管理。最終,一個由行業相關機構頒給我的“信托及房產管理員資格證”終于讓我不至于在各位行業大牛和超級富豪面前露出馬腳。
此外,我并沒有刻意地隱藏自己的真實身份。無論是參加專業課程還是業內社交活動,我一直都佩戴著寫有我真實姓名的牌子。這些與會人員們可以輕易地通過網絡搜索引擎找出我的工作單位——他們都一致認為我是參與學術調研的學者。
最終,我設法前往18個國家采訪,并進行了65次相關訪問,從傳統的財富管理中心瑞士和英國到散落在印度洋中心的塞舌爾群島。盡管這次調研在外人看來就像是一場公費的度假旅行,但有時候也暗藏著令人多次從噩夢中驚醒的那類無法預知的危險。
比如在庫克群島,我就被當地劫匪搶去了身上所有的財物。當地的一位土著毛利人漁民告訴我說,自從金融服務行業在庫克群島落地以來,這里的犯罪率開始飆升。“現在我們的綽號叫‘詐騙群島’”,這位漁民說。
然而財富管理行業對世界的影響不止于此。我所學習到的最深刻一課就是,這個行業不僅僅加劇了正在快速增長中的全球收入不平等現象,還讓超級富豪們得到了一種遠遠不止于逃避稅務和監管的權力錯覺——財富幾乎可以讓他們輕松擺平所有的障礙。
遭遇一場昂貴的離婚官司?這簡直就不是問題。一位有經驗的財富管理專家會幫你將所有的資產轉移到離岸的信托賬戶里。這意味著這些資產從法律上來說已經不再屬于你的名下,因此你那惱人的配偶也別想分到一杯羹。俄羅斯超級富豪迪米特里·雷波洛列夫就因此受益匪淺——按照一家瑞士法庭的初審判決,他本來需要向他的前妻愛蓮娜支付高達90億美元的“分手費”,但上訴法庭最終駁回了這個判決,原因就是雷波洛列夫的財產全都被放在了信托賬戶里。
這種情況同樣適用于來自政府的起訴。比如著名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就把他們的財產放在了庫克群島——目前為止,沒有任何一起公訴人能設法成功動用庫克群島的那些數不清的神秘信托賬戶,其中包括美國政府。
當然還有最著名的避稅大法。對想要逃避巨額稅務的超級富豪們而言,他們的財富管家們一般會建議他們轉換國籍。記得放棄了美國國籍并申領了新加坡護照的埃德華多·薩瓦林嗎?這位Facebook的聯合創始人之一并不是唯一一位選擇放棄美國公民身份的人——目前走這條路子來避稅的案例正在逐年增加。
接受我采訪的一些財富管家認為這個行業被媒體妖魔化了。他們宣稱自己的工作幫助了那些年老的客戶免受貪婪的繼承人的騷擾。“有很多有錢的父母擔心自己的財富被無所事事的孩子敗光,因此選擇了建立信托賬戶。”一位從業人員說。
一些財富管家說他們和客戶之間建立了相當深厚的友誼,和他們一起去度假,參加這些客戶家里的紅白喜事;另一些卻相當詭異,在這些客戶身上賺錢之余不忘占據道德高地,譴責富豪們過于貪婪。
我采訪過的一位美國籍財富管家就對他的客戶頗有成見。他用“注定要毀滅地球的暴君”來形容他們。他透露說這些人已經花錢花到無法滿足欲望的地步,因此只好通過和彼此老婆上床的方式來打發無聊的時間。“我跟我的同事說過,要是有朝一日我變成了類似的人,你們就直接一槍斃掉我好了。”他說。
另外一位擁有劍橋大學歷史學碩士學位的從業人員則告訴我說,他每天都飽受來自內心良知的道德拷問。他認為是自己一手造成了世界貧困,并多次通過建議客戶捐錢給慈善機構的方式來完成某種意義上的“贖罪”。
一位此前在綠色和平組織工作的年輕女士在她男朋友的引薦下來到了瑞士的財富管理機構任職——這家公司的老板就是其未來公公。在這家公司的客戶名單上,一些超級富豪的富裕程度甚至可以輕松超過一些國家的全國財富。“這些人是凌駕于任何一國的國籍和法律之上的。”她說。
“有一次我需要到歐洲以外的地方和一位大公司的CEO見面。當時我因為換了手提包而把護照落在了家里。當我在蘇黎世機場要求回家取護照時,客戶一方來接待我的工作人員卻表示一切都沒有問題。”她回憶到,當她在機場過海關的時候,果真沒有工作人員要求她出示任何身份證明。“那個時候我才意識到這些人享有的特權是多么地一手遮天。”
這個故事讓人想起了紀實作家瓊·狄迪恩的那句名言:財富和權力之間的秘密關系并不在于金錢可以購買權力,而在于金錢換來的之于個人的完全的自由——無論是遷徙自由還是隱私自由。在這層自由背后,財富管家毫無疑問是最大的操盤手。他們通過建立財富信托基金和離岸公司的方式為超級富豪們躲債、避稅,制定完美的財富繼承計劃以確保巨額財富始終固定在家族的核心圈子里。
或許最重要的是,這些財富管理專家讓客戶的隱私得到最大限度的保護。他們讓媒體和監管機構盡可能少地掌握到客戶的資產清單。為此,他們本人也要盡可能地低調處世,越少人知道他們的真實職業身份越有利于他們客戶的資產安全。
就我所見,大部分的財富管理公司都將外部形象保持在干凈和整潔的程度,這和那些裝潢華麗的投資銀行相去甚遠。在離岸小島的辦事處里,一些財富管家的辦公室簡陋得讓你想起薩默賽特·毛姆的短篇小說,那些堆滿了文件和塵埃的辦公桌很難讓人聯想到巨額財富和絕對權力。而在歐洲或北美的在岸總部里,財富管家們清一色地都用藏在大衣里的懷表而非外露的腕表——外行人絕對會忽視掉這些細節,但真正的超級富豪卻不會看走眼。
以此造成的假象就是,這些手中“分分鐘百萬上下”的財富管家從外表上來看完全就是個普通的白領職員。而這又恰好是超級富豪們最想要的:當大眾輿論樂此不疲地繼續討論著“階層固化”和“仇富心理”時,很少會有人將注意力從富豪本人身上轉移到為他們打理財富的管理專家身上來——這恰恰好是所有問題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