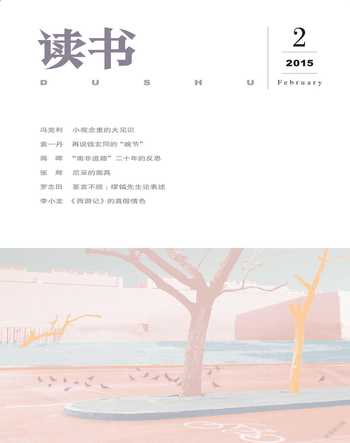再說錢玄同的“晚節(jié)”
袁一丹
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后,在選擇蟄居北平的文人學(xué)者中,錢玄同并不那么引人注目。與他的老朋友周作人相比,錢氏雖也有留日背景,但始終沒有成為外界輿論關(guān)注的焦點,直至一九三九年初,其因突發(fā)腦溢血去世。關(guān)于北平淪陷時期錢玄同的表現(xiàn),即所謂“晚節(jié)”問題,一直沒有太多爭議。因為錢氏去世不久,同年七月國民政府便發(fā)布褒揚令,表彰其學(xué)行:
國立北平師范大學(xué)教授錢玄同,品行高潔,學(xué)識湛深。抗戰(zhàn)軍興,適以宿病不良于行,未即離平。歷時既久,環(huán)境益堅,仍能潛修國學(xué),永保清操。卒因蟄居抑郁,切齒仇讎,病體日頹,赍志長逝。溯其生平致力教育事業(yè),歷二十馀載,所為文字,見重一時,不僅貽惠士林,實亦有功黨國,應(yīng)予明令褒揚,以彰幽潛,而昭激勸。
這一褒揚令帶有蓋棺論定的性質(zhì),再加之抗戰(zhàn)勝利后,錢玄同的門生故友如魏建功、徐炳昶等人在回憶文章中提供的種種細節(jié),似足以證明錢玄同之“晚節(jié)”不成問題。
然而一九九八年《魯迅研究月刊》上登載了謝村人的一篇文章,題為《“書齋生活及其危險”》,從錢玄同的一封佚信談起,認為從“五四”到三十年代,錢氏由新文化陣營中的一位“猛士”,蛻變?yōu)楣淌貢S的“隱士”,北平淪陷后,甚至倒退到“貳臣”的懸崖邊上,要不是死神向他伸出“援手”,極可能有墮入深淵的危險。謝氏文末再次強調(diào)錢玄同“死得其時”—“雖然已被污水弄臟了鞋襪,但未遭滅頂之災(zāi);否則在日寇的威脅利誘之下,未必不會成為第二個周作人!”
謝村人這篇“判決書似的文字”立即引發(fā)爭議,《魯迅研究月刊》上隨后登出兩篇與之“商榷”的文章,大段征引徐炳昶、魏建功等人的回憶文章及國民政府的褒揚令,捍衛(wèi)錢玄同之“晚節(jié)”。但這兩篇商榷文章,并未直接回應(yīng)謝村人指出的一個“污點”:據(jù)《周作人年譜》,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錢玄同接受“親日分子”何克之的邀請,出席了有“日本右翼分子”山崎宇佐和文化漢奸參加的宴會。這次“灰色”的宴會,是謝村人斷定錢玄同有可能淪為“周作人第二”的唯一證據(jù)。不對這一宴會的性質(zhì)加以考察,盡管有官方的褒揚令做護符,僅憑親友的回憶,也難以完全洗清錢玄同的“污名”。要弄清此次宴會的性質(zhì)及出席者的身份,不能僅針對事件本身,尚需大致了解北平淪陷后錢玄同的日常生活。
關(guān)于這次“灰色”的宴會,謝村人依據(jù)的是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周作人日記所載:“午往玉華臺,赴中國大學(xué)校長何其鞏之招宴,同座有山崎宇佐、羅文仲、孫蜀丞、方宗鰲、夏明家、錢玄同、沈兼士。”為支持自己的論斷,謝氏對這條日記略做改編,先給招集者何其鞏貼上“親日分子”的標簽,又在“山崎宇佐”這個日本名字前冠以“右翼分子”的頭銜,其余赴宴者則一律歸為“文化漢奸”。這種貼標簽的辦法似乎太隨意了,謝村人并未逐一考察出席者的真實身份,便急于為此次宴會定性。
問題在于謝村人依據(jù)的其實是《周作人年譜》之轉(zhuǎn)述,而非日記原文。山崎宇佐的身份背景雖尚待查明,但極有可能是兩個人!周作人日記中涉及日本人的,如是相交甚淺或不甚知名者,往往用姓氏表述,而“山崎”、“宇佐”都是日本較常見的姓(日記原文無標點,“宇”字是補寫的)。并且《年譜》轉(zhuǎn)述此事時,只列出赴宴者的名單,竟略去了日記原文中極緊要的半行字:“略談及孔德華北訟事。”這句話實已點出何其鞏招集此次宴會的緣由,容后詳考。
事實上,時任中國大學(xué)校長的何其鞏在政軍兩界有著極復(fù)雜的社會關(guān)系,淪陷時期其在北平文教界扮演的角色,絕非“親日分子”這一標簽所能概括。在招集此次宴會前不久,何其鞏曾以“前華北大學(xué)校長”的身份,應(yīng)邀出席了一九三八年二月九日日本大阪每日新聞社組織的“更生中國文化建設(shè)座談會”。而周作人正是因為在這個座談會上露面,遂被判定為“文化漢奸”,收到武漢文化界發(fā)出的驅(qū)逐令及十八位作家聯(lián)名簽署的公開信。
需要追問的是,在被占領(lǐng)的非常事態(tài)下,出席日方組織的文化活動或有日本人在場的宴會,對周作人、何其鞏等人而言,是否意在表明某種“合作”的政治姿態(tài),或者說是否構(gòu)成某種心理障礙?其實就在出席所謂“更生中國文化建設(shè)座談會”的前一天,據(jù)周作人日記所載,其“應(yīng)山室之招”,同座有錢稻孫、蘇民生、洪炎秋、新見、西川、佐藤、木村、富田、菊池等共十人。又如同年七月七日下午周氏往北京飯店,應(yīng)日本改造社社長山本實彥之招,“來者尚有山崎、村上共四人”。由此可見事變后,周作人并未杜門用晦,斷絕與日本文化人的往來。相較之下,在錢玄同日記中,北平淪陷后出席有日本人在座的宴會,僅此一例。
除了考察赴宴者的身份背景,更重要的是何其鞏以什么名義,或借什么由頭招集三月二十九日這次宴會。無巧不巧的是,錢玄同日記只記到三月二十八日,此后有近一個月沒有寫日記。這種間斷在他的日記中很常見,或是因為身體不適,或就是因為一個“懶”字,不能持之以恒。但淪陷時期錢玄同日記中的空白,比事變前又多了一層闡釋空間。如“七七事變”后,從七月十九日到八月末,他有四十來天沒有記日記。直至九月一日續(xù)寫時,錢玄同聲稱:“這四十日之中,應(yīng)與《春秋》桓四、桓七不書秋冬同例也(以后也還如此)。”所謂“《春秋》桓四、桓七不書秋冬”有何寓意?按宋儒的說法:
問:“桓四年無秋冬,如何?”曰:“圣人作經(jīng)備四時也。如桓不道,背逆天理,故不書秋冬。《春秋》只有兩處如此,皆言其無天理也。”(《河南程氏遺書》卷二十二下,伊川先生語)
故“不書秋冬”乃春秋筆法。錢玄同日記中的這段空白,非一般意義上的間斷,實有意為之。從七月十九日到八月末,正值北平“籠城”前后,其間有兩個關(guān)鍵的時間點:七月二十九日駐守北平的二十九軍撤退,八月八日日軍進駐北平。錢氏日記的此次間斷,是以春秋筆法—“不書”,“言其無天理也”。
問題在于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錢玄同赴宴當(dāng)天及其后一個月沒寫日記,是有意識地“不書”,還是單純“未記”?錢氏對此未做交代,故只能從此前此后的日記中尋找與這次宴會相關(guān)的線索。有研究者從三月二十三日的錢玄同日記中發(fā)現(xiàn)似與此次宴會相關(guān)的信息:當(dāng)天周作人與錢玄同商量“同訪何其鞏,為孔德事也,在何家見”(邱巍:《境遇中的民族主義—從錢玄同的晚節(jié)說起》)。遂斷言三月二十九日的宴會應(yīng)當(dāng)正是“在何家見”的最終結(jié)果。這一發(fā)現(xiàn)雖利用了一手材料,但斷句有誤,當(dāng)日周、錢二人已拜訪何其鞏,并“在何家見姚惜抱致陳碩士信手跡”。故三月二十九日何其鞏招宴,確與孔德事相關(guān),但并非“在何家見”的最終結(jié)果。
三月二十三日周作人、錢玄同“同訪何其鞏”,為孔德何事?除了設(shè)宴者何其鞏,值得注意的是,三月二十九日赴宴者中,孫蜀丞的名字也在這一時期的錢玄同日記里頻頻出現(xiàn),且與“孔德事”相關(guān)。如五月八日“訪孫蜀丞,為孔德訟事”;五月十日至輔仁大學(xué),“因前日約定周(作人)、錢(玄同)、沈(兼士)、孫(蜀丞)在今日上午會于該校,為孔德和解事也”;五月十一日“為孔德事,乘汽車訪豈(周作人)、訪孫(蜀丞)”;五月十三日“得孫(蜀丞)電話,知一切手續(xù)均辦妥,專候孔德付錢矣”;五月十四日“至孔德,取五百五十元,至知老(周作人)處,孫(蜀丞)亦來”;五月十五日“至孫蜀丞處,孔德與華北事畢矣”。五月十六日錢玄同日記稱:
孔德訟事已了。今晚中人何其鞏因調(diào)停此事已畢,約雙方人在其家吃飯。我因傷不能往,電話約知堂來家,請其轉(zhuǎn)達。
可見這一時期錢玄同、周作人屢屢造訪何其鞏、孫蜀丞,都是為“孔德與華北事”。五月二十六日“孔、華訟事,今日已開調(diào)解庭,完矣”。
所謂“孔、華訟事”緣何而起?錢玄同、周作人、何其鞏、孫蜀丞在此案中各自飾演何種角色?錢玄同日記對此事語焉不詳。所幸河北檔案館存有一份涉及北平孔德學(xué)校與華北學(xué)院房產(chǎn)糾紛的和解筆錄。據(jù)已公開發(fā)表的檔案記載,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六日,時任孔德學(xué)校校長的周作人和華北學(xué)院法定代理人何其鞏,因房屋借用權(quán)的民事糾紛,最終達成和解。和解內(nèi)容為:“被上訴人(華北學(xué)院)對于宗人府房屋借用權(quán),情愿永遠讓與孔德學(xué)校。”
何其鞏時任中國大學(xué)校長,為何在“孔、華訟事”中充當(dāng)中間人,且作為華北學(xué)院的法定代理人出庭?因一九三七年八月底,華北學(xué)院被迫遷至城南湖廣會館,其在京校舍由中國大學(xué)代管。而孫蜀丞在“七七事變”后接任中國大學(xué)國文系主任,故亦與此案有關(guān)。一九三八年六月三日周作人“為孔德了結(jié)華北案”設(shè)宴于承華園,回請何其鞏、孫蜀丞諸人。由此可見三月二十九日何其鞏招宴,不過是為調(diào)停孔德學(xué)院與華北學(xué)院的房產(chǎn)糾紛。謝村人據(jù)此質(zhì)疑錢玄同之“晚節(jié)”,無疑不太了解淪陷時期的生活常態(tài)及文教界錯綜復(fù)雜的人事背景。
盡管錢玄同聲稱仿效春秋筆法,“不書秋冬”,但在一些特殊的時間點上,仍瞥見到“淪陷”在北平城中投下的陰影。如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九日為舊歷中秋節(jié),錢玄同在日記中寫道:“‘ ’特令全市商店掛燈結(jié)彩以志慶祝,借紀念東方文化之佳節(jié)也。”引號中的空白,即秉持“不書秋冬”的原則。同日,中山公園改名為“北平公園”,東廠胡同改稱“東昌胡同”。九月二十四日云“今日道路又掛紅燈”,其自孔德歸家時,行經(jīng)東安市場前,見高懸白布匾,文曰:“慶祝陷落保定府”。十一月八日街上張貼“慶祝太原陷落”之布文。十二月七日錢氏路經(jīng)北大一院,見門首有“皇軍”站崗。
這些淪陷的陰影在錢玄同日記中一閃而過,往往是干癟的一行文字,紀實性的,不加評論,不帶情感色彩,有時略含反諷。其著墨較多的場景,是南京陷落前后及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成立。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錢玄同從報上得知南京陷落的消息,“九時警察署大放鞭炮慶祝”,“入晚每家門首至少須懸方形紅燈一盞”,次日中午各校學(xué)生須至中央公園舉行游行慶祝。第二天又聽說南京尚未陷落,“故今日游行及提燈之慶祝均不舉行”。錢玄同至中央公園散步,“見甚清靜,空氣甚佳”。十二月十三日至孔德,與同事談話間,警察忽來傳話,命學(xué)校準備五色旗。翌日“晨起,出胡同口一看,見滿街都掛五色旗”,午后途經(jīng)中南海門前,見已掛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招牌。十二月十五日天安門開慶祝大會,學(xué)校放假,警察送來太陽與五色交叉之旗,令各家貼于門首。
但淪陷這種軍事占領(lǐng)的非常狀態(tài),久而久之會成為一種波瀾不驚的生活常態(tài)。從淪陷時期的錢玄同日記中,我們看到更多的是一個宿病纏身的讀書人在占領(lǐng)區(qū)的日常生活:每日奔走于家、宿舍、學(xué)校、醫(yī)院之間;順道拜訪老友,一談就談三四個小時;身體不適或遇大風(fēng)、雨雪天,便在室內(nèi)清理書籍雜物,倦時倚在床上亂翻書;偶爾去東安市場購物,舊歷正月間照例“巡閱”廠甸東、西兩路。
僅以逛廠甸為例,來看事變對讀書人的日常生活影響到什么程度。一九三八年二月八日錢玄同給周作人寫信說:“嗚呼,計我生之逛廠甸書攤也,今歲蓋第廿五次矣”,“前廿四次總算努力,而今年則七日之中僅逛三次,每次只逛一路,噫,何其頹唐也!”據(jù)錢玄同之子錢秉雄回憶,自一九一三年錢玄同北上進京后,一住就是二十來年,沒有去過比天津更遠的地方,北京成了他的第二故鄉(xiāng)。除了喜歡北方的氣候及在此地結(jié)識的諸多好友,更吸引錢玄同的是北京的書肆,尤其是每年春節(jié)的廠甸。因酷愛逛廠甸,錢玄同被戲封為“廠甸巡閱使”。而一九三八年廠甸書市之光景與事變前有何不同?據(jù)錢玄同考察:“今年有些熟書攤均未擺,而擺者我有許多多不相識,故您過年好哇,要什么好書啦,今年還是第一次來吧,種種應(yīng)酬話很少聽見,此與往年不同者也。”
一九三八年二月一日,即陰歷正月二號,“廠甸巡閱使”錢玄同向周作人匯報:“今天冒了寒風(fēng),為首次之巡閱,居然有所得,不亦快哉!”興奮之情溢于言表。其首次“巡閱”所得,系黃遵憲《日本雜事詩》改定本。二月五日錢玄同逛廠甸東路及土地祠,購書七種,最得意的是新鐫《康南海先生傳》,萬木草堂刊本。此日錢氏從下午一時逛到六時半回家,足足逛了五個半小時,體力驚人,并于廠甸晤唐蘭、劉文典。次日十二時半又至廠甸,巡閱西路,購得《陳石遺年譜》及戊戌至己亥年《清議報》原本。二月八日專程去買《清議報》全編殘本。十日下午三時逛廠甸東路,略及土地祠,毫無所得。十二日下午略瀏覽西路,購得日本田口卯吉之《中國文明小史》(廣智書局譯本)及《昌言報》、《東亞時報》各一期,遇劉盼遂。二月十三日午飯后,頭漲胸悶,仍至廠甸東路一巡。二月十五日本是廠甸書市結(jié)束之期,錢玄同得知今年延長十天,至二月二十四日方散。二月二十二日為其該年最末一次巡視,土地祠中已無人擺攤,道旁的書攤大約比元宵節(jié)以前減半。照錢玄同日記統(tǒng)計,一九三八年正月二十五日間,其分別“巡閱”廠甸東西兩路及土地祠,共計十次,較事變前何嘗有“頹唐”之象!唯有從書信日記中體會知識階層的生活實感—或許有悖于局外人對淪陷北平的想象,才能更真切地理解事變后讀書人的出處選擇及倫理境遇。
在表彰錢玄同的“晚節(jié)”時,一般會舉魏建功回憶文章中的一個細節(jié):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其動身離平前,錢玄同要他刻一方圖章,就刻“錢夏玄同”四個字,借以表明恢復(fù)自己的舊名。對于這方印的寓意,魏建功以為,“錢夏”是錢玄同從事排滿革命時期的名字,自從一九三七年八月八日日軍進駐北平,“他又再拿來表示一個新的民族分野”。至于“夏”字之來歷,周作人在《餅齋的名號》中解釋得更清楚:錢玄同赴日本留學(xué),受種族革命之熏陶,另取光復(fù)派之號曰“漢一”;及從章太炎求學(xué),乃知古人名字相應(yīng),又由“漢一”而想到“夏”字。可見以“夏”為名,在錢玄同這里,帶有“漢一”即“排滿”的胎記。北平淪陷后恢復(fù)這一舊名,則是在事變刺激下,晚清經(jīng)驗的某種復(fù)活。
淪陷時期錢玄同最重要的學(xué)術(shù)工作是編輯《劉申叔遺書》。一九三四年其與鄭裕孚(負責(zé)校對《遺書》者)通信商量是否刊行劉師培的《攘?xí)窌r,稱《攘?xí)分×x于“攘夷”:
夫泛言攘夷,此在任何時代,皆不失其價值。即以今日而論,抗日非攘夷乎?打倒帝國主義非攘夷乎?
在錢玄同看來,劉師培之《攘?xí)凡粌H有其學(xué)術(shù)價值,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抗日戰(zhàn)爭的語境中,更有其現(xiàn)實意義。“攘夷”的內(nèi)涵,遠超出晚清狹隘的種族主義;在世界大同之日降臨以前,幾乎可與同以國家為邊界的民族主義畫上等號。《攘?xí)纷鳛閯熍嘣缒暌詫W(xué)術(shù)鼓吹革命的業(yè)績,在錢玄同眼里,不同于空洞淺薄的宣傳標語,其發(fā)揮“攘夷”之義,“類皆原本學(xué)術(shù),根柢遙深”,乃“純?nèi)粚W(xué)者之言”,而非革命家的一句口號。
一九三六年章太炎去世后,錢玄同所擬的挽聯(lián)中,亦將“排滿”與“抗日”并舉,著力表彰其師之“攘夷”思想:“先師尊重歷史,志切攘夷,早年排滿,晚年抗日,有功于中華民族甚大。”而此思想得力于《春秋》。一九三七年事變前夕,錢玄同重溫三十多年前看過的鄒容《革命軍》,感嘆晚清“雖持極端排滿論者,亦不至于今日之富于保守性”。他認為辛亥以前抱“一民”(民族)主義者,雖不及孫中山之“三民主義”,至少是“二民主義”,兼有民族、民權(quán)二義。章、劉、鄒等人標舉的排滿革命,均非單純的種族革命。即便《國粹學(xué)報》之鄧實、黃節(jié)“亦尚略有新思想”。專以反清復(fù)明為宗旨者,唯有南社諸詩翁及各地會黨勢力而已。錢玄同對“攘夷”二字的重新界定,無疑是針對三十年代過于“保守”的民族主義。
在力主刊行《攘?xí)返哪欠庑胖校X玄同談及劉師培的“晚節(jié)”問題,他推測反對刊行者之用心,“實因申叔晚節(jié)之有虧,恐人見其早年之鼓吹革命而譏其后之變節(jié)耳”。至于如何評判劉師培之“變節(jié)”,據(jù)錢玄同總結(jié),大約有三派。甲派謂劉氏為群小及艷妻(何震)所累,以致陷入泥潭,無法自拔,并非他個人之罪責(zé)。甲派之代表是蔡元培,其對劉師培始終如一,持諒解態(tài)度。丙派則始終敵視,而乙派的態(tài)度有個變化的過程,“始惡之而終諒之”:
當(dāng)時聞其變節(jié)而頗致詆毀,逮革命既成,往事已成陳跡,而敬其學(xué)問之博深,諒其環(huán)境之惡劣,更念及舊之交誼,釋怨復(fù)交,仍如曩昔。
錢玄同坦言自己是乙派中人,“昔年曾與之割席”,表明其政治立場。而“終諒”之前提,首先是時移境遷,“革命既成”,劉師培的“變節(jié)”已成歷史上之陳跡。其次,錢玄同再三強調(diào)學(xué)問與政治、思想與行事的區(qū)別,以為“行事之善惡,時過境遷,即歸消滅,而學(xué)問則亙古常新也”。既然劉師培之行事已成陳跡,無損于其學(xué)術(shù)文章的價值。
錢玄同及章、劉一輩皆是過渡時代中人,出入于政、學(xué)之間,其前后之主張、行動之宗旨難免隨一時一地之思想、感情,尤其是外在環(huán)境之劇變而更易。始激進而后保守,始革命而后不革命,乃至反革命者,絕非劉師培一人。即便是此輩人中腳力最好,緊攆著時代往前跑的梁啟超,“始而保皇,繼而立憲,與革命黨大打筆墨官司,而民國以來乃擁護共和”,善變?nèi)绱恕A簡⒊;省熍嘀児?jié),在民國初年,“因時代較近,故詆毀者甚眾”;二十年后,對于二人清季之所作所為,已知者甚少,“即真知之亦甚隔膜,即不隔膜而怨恨之念亦不復(fù)萌生,但見其學(xué)問之淵深而敬之矣”。
對于劉師培的“變節(jié)”,錢玄同所以能“釋怨復(fù)交”,還涉及公誼與私情之取舍。假如錢玄同目睹周作人之“落水”,他會持何種立場?按照錢玄同對知堂學(xué)問文章之欣賞,對其環(huán)境包括所謂家累及輿論壓力之同情,更考慮到二人數(shù)十年之交誼,很可能“始惡之而終諒之”。不過諒解恐怕要等到抗戰(zhàn)勝利,甚或是新中國成立后。但抗日畢竟不同于排滿,“攘夷”與民族主義無法真的畫上等號,故周作人之“落水”也難以與劉師培的“變節(jié)”等量視之。中日間的那場戰(zhàn)爭,可以說到目前為止尚未結(jié)束,因為引發(fā)戰(zhàn)爭的那些導(dǎo)火索還在。時過“境未遷”,周作人之“落水”還沒有成為陳跡,錢玄同的“晚節(jié)”仍招致非議,盡管后來者對他們在淪陷下的處境與心境更為隔膜。
(《錢玄同日記》影印本,北京魯迅博物館編,福建教育出版社二零零二年版;《錢玄同日記》整理本,楊天石主編,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二零一四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