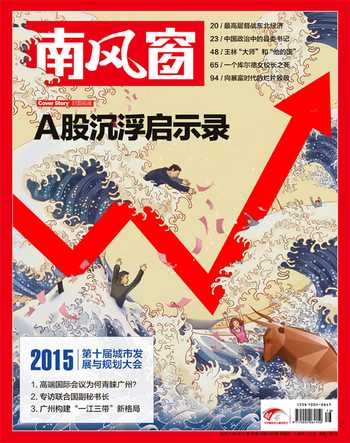這是第一次真正的危機
張墨寧

從2015年6月中旬開始,中國股市從高峰跌入低谷。隨后,政府部門使出了史無前例的強力救市“組合拳”,A股又開始了緩慢而艱難的“修復”。
這次危機充分暴露了中國資本市場的多重問題:除了金融機構毫無顧忌地為市場加杠桿,而投資者也無限制地追求暴利之外,金融監管的漠然和不力也是股市巨震的重要因素。
在瞬息萬變的資本市場,當市場出現風險征兆、遇到重大危機時,“政府之手”究竟以何種方式介入,不僅能使關系短期穩定,更將影響中國金融改革的走向。
因此,分析此次危機的政策因素以及后期救市手段的運用,對未來中國證券市場新的制度構建,特別是IPO注冊制的推進將有著積極的意義。為此,本刊記者專訪中國證券理論研究的開拓者、證監會前發審委委員、著名經濟學家吳曉求教授。
《南風窗》:現在回過頭看這次“股災”,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對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會帶來什么影響?
吳曉求:這輪震蕩應該說是中國資本市場第一次遇到了真正的危機。在此之前,即使2007年、2008年股指從6000多點跌到1000多點,都談不上危機。因為那個時候市場的規模比較小,股權分置改革剛剛完成,市值不過十幾萬億,也沒有杠桿,而且下跌的速度非常緩慢,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對整個社會和實體經濟的影響都是有限的。
這次危機是在各方面綜合因素的影響下形成的,歸結為五個方面,首先是估值泡沫化,特別是創業板、中小板最突出,創業板的平均靜態市盈率差不多接近200倍。這樣一個建立在過高杠桿基礎上的估值顯而易見不可能持續下去。
第二是過度的杠桿化或者杠桿的暴利化,場外各種形態的配資、場內的兩融、股權質押都疊加在一起形成很高的市場杠桿率;第三是監管的淡漠和不敏感,一些部門被“改革牛”、“國家牛”這些似是而非的說法迷惑,牛不牛是由市場、公司價值和宏觀經濟基本面決定的,不是人為地去造一個“牛市”;第四就是投資人的風險意識太差,很多年輕人、新的投資者認為股市就是ATM機,早上一來,晚上把錢取走,完全忽視了風險;第五就是一些主流媒體的誤導,說什么4000點僅僅是“國家牛”的開始,這是完全沒有邏輯基礎的。這些因素綜合,最終形成了最嚴重的一次危機。
其中,監管是一個重要的環節,它沒有及時地隨著市場指數的變化、風險的增大,動態地調整一些工具、制度和杠桿,反而變本加厲地共同來吹大泡沫。這次下跌首先是市場本身出了問題,其次是監管沒有跟上,這兩條是至關重要的。
《南風窗》:監管部門對此也缺乏思想準備,至少沒有想到結果會這么慘烈,未來應該如何重塑監管呢?
吳曉求:我認為,監管首先是缺乏一個平衡概念,主觀色彩太濃。要讓它漲,就單方面使用工具,要讓它跌,也是單方面使用工具,不尊重市場的內在規則。所以,我們要重塑監管的理念,不要以為市場一定跟著監管走,不要以為監管部門的意志可以控制一切,而是應該按照市場化的理念、市場化的機制,利用市場化的工具,保證正常運行。指數或價格也許在一個短期內會偏離所謂的特定目標,但那也是一種市場行為,不要過度寄希望于市場會跟著人們的主觀意志走。政府應該離市場遠一點,讓市場發揮自身的作用。只在發生違規違法行為的時候政府和監管部門可以查處。
《南風窗》:政府綜合運用財政、貨幣和公安這樣的強力手段救市,基本取得了預期效果,但外界也有質疑,認為以這樣的方式緊急救市存在合法性的問題。
吳曉求:政府遠離市場并不是任由市場脫韁,一旦出現重大危機或者出現了明顯泡沫化的時候,政府可以間接手段去影響市場,防止大面積風險的出現。比如,可以適當提高利率,或者不斷降低杠桿率。
風險在哪里?舉個例子,指數高了,可以抵押的資產的風險也就變大了,那么風險的折扣率顯而易見就要大幅度降低。資產10塊錢的時候可以抵押8塊錢出來,但漲到30塊錢的時候,不能再用8折抵押24塊錢了,可能就得降到4折。杠桿率隨著風險增大是要調整的,這樣才能夠防止市場脆弱性的出現,讓市場有一個緩沖和預警。
但調整的過程必須要循序漸進,不能從10塊錢到30塊錢什么動作都沒有,不聞不管,一到30塊錢監管部門就出嚴厲的手段,這是不行的。
從國家層面來看,為了保證金融體系穩定去救是未可厚非的,但是用什么手段去救,這要認真思考。做任何事情必須在法律的框架內,不能損害市場健康的基礎。比如,2008年的四萬億投資,固然避免了經濟增長的斷崖式下降,但帶來的成本卻需要很長時間去消化。資本市場的救市也一樣。
《南風窗》:7月份以來,股市出現了上千家公司以模糊理由紛紛停牌,等到7月9日大盤開始好轉又火速復牌的罕見現象,這是對市場精神的破壞嗎?如何看待這次救市的時間和策略選擇?
吳曉求:總的來說,我認為這次救市是不得已,但不得已之中,也存在方法過猛的問題。有一些辦法違背了市場的基本精神,比如大面積隨意停牌和莫名其妙的復牌,編造停牌的理由,這都是嚴重違規違法的行為,破壞了投資者的預期。特別是國際投資者,他們會看不懂這個市場。要建設國際金融中心,這些手段不可以用。
這次救市有一些方法是很好的,但也有欠缺。7月7日之前,采取的是“總量救市”的辦法。主要是救指數,資金集中去買中石油、中石化、工商銀行這些藍籌股,它們的市場份額比較大。結果是指數可能翻紅,但仍然有大面積跌停的股票。這就有點像和期指打仗,在期指上打仗不是不可以,期指不是主戰場。
早期從5000多點跌到4000多點,雖然下跌得快了一點,我認為這是正常的。高額配資的人損害了市場,如果他們還在市場,破壞率太大。有時候,大幅度波動在客觀上能起到清理隊伍的作用,把那些追求高杠桿的人、有暴利想法的人清理出去。在這期間,我不認為應該救市。場外的1∶3、1∶5甚至更高的杠桿配資只能出去,這些人不出去,市場會出大問題。到了4000點以下,場內1∶2的配資消失了也正常。但再往下走,就會有問題。
融資分三個層級,第三個層級就是股權質押融資,大股東拿股權質押,這是我國資本市場一個常見的行為。如果觸及了這類股權質押融資的風險,就會給股市帶來災難性后果。所以,等到第三層次出現風險,那就誰也救不了,因為市值太大了,應該在此前救市。
所以說,當時采取總量救市的辦法是低效率的,問題的關鍵不是跟期指斗爭,而是要穩定市場,不要波及第三個層次的風險即可。
之后,救市方法有所改變。我們從“總量救市”過渡到了“結構性救市”。放棄了中石油、中石化這些藍籌,開始針對小股票救市。7月8日我就說了,我們出現的是結構性金融危機,不是總量危機,所以要用結構性手段,對那些跌了七八個甚至十多個跌停板的小股票采取及時有效的辦法,因為那個時候靠市場力量恢復已經不可能了。
在我看來,市場有一個基本的交易規則,維護基本的交易規則、維護基本的契約精神也是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一個基礎元素。總結來說,這次救市從“總量救市”變成“結構性救市”我是贊成的,但具體手段還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南風窗》:救市方向的調整是基于什么樣的市場變化?你認為早期把救市的側重點放在股指期貨上的原因是什么?
吳曉求:從6月7日前后到7月7日這一個月的時間,市場有一種喧囂、誤導和猜測。情緒太多,“陰謀論”也出來了。明顯就是估值高了,而維護高估值只會帶來更大的危機。交易量也明顯增大了,最高的時候交易量一天接近2.5萬億元,在差不多三四個月的時間里,中國資本市場交易的換手率都超過3%。
美國市場每天的換手率只有0.2%~0.25%,我們的市場最高峰的時候只有美國40%的市值,但是換手率卻超過它10倍。你能說這個市場是正常的嗎?
所以,首先是市場本身出現了嚴重的問題。而且,不應該把股指期貨產生危機的作用夸大了。如果我是一個投資客,在那個時候也會做空,因為市場已經明顯偏離了正常的價值判斷,做多必死無疑。所謂做空,其實就是讓價格回到理性狀態。做空不是有意跟誰過不去。我們要把正常的做空和唱衰中國區分開來,不要把它過度地政治化。
《南風窗》:從這次震蕩是不是可以看出監管部門在市場監管,特別是管理股指期貨等金融衍生品上還缺乏經驗。你認為未來市場監管的重點是什么?
吳曉求:這次危機對于中國金融來說也許是個好事,因為我們還沒有完全開放,還沒有完全國際化,在即將開放的前夜,有一場大的演習,雖然成本有點高,但讓我們了解了什么是金融市場的風險,有一個心理上的準備。
當然,我們不希望未來出現這么大的事情,這就需要從制度層面全方位的完善。最重要的是確立資本市場的基本理念,解決問題的思路應該遵從市場的基本規則和基本精神。不要臆斷、猜測、情緒化。同時還需要學習美國、英國成熟資本市場怎么應對危機。就是說,今天的救市手段,不要影響未來的信心。維護一個全球投資者都有信心的市場,這比什么都重要。
當務之急是股市的控制杠桿。中國市場的杠桿率非常高,特別是2013年以后,已經大幅度超過全球主要經濟體資本市場,這加大了泡沫化和脆弱性。漲的時候很快,下跌的時候是雪崩一樣的速度,因為杠桿越高,強制平倉的概率越大。
對場外的杠桿,必須從技術和制度層面,把場外的口子通通切斷,不能使場外配資成為一個系統性的普遍現象。借錢炒股是私人的事,但是批量的場外融資迅速進入市場就有問題了。場內的配資也要規范,場內配資按道理也不可以超過1∶1。
還有就是規范上市公司的行為,特別是信息披露問題。這一輪上漲過快、下跌過快和概念股有不小的關系。比如,某家企業只是收購一個網站,就搖身變成“互聯網金融”,馬上就有七八個漲停,這是不正常的現象。
所以,規范上市公司的這種并購重組行為,加大對它信息披露的監管。在這方面,證監會要有敏感性,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統統都是假的,證監會為什么不去核查,對它停牌?出現七八個漲停,這是什么概念,這個公司發生了脫胎換骨式的變化嗎?
人的貪婪與恐懼、夢想與現實,在股市中演繹的淋漓盡致。每個股民都有一段刻骨銘心的故事,尤其在這個頹狂的6月和難以捉摸的7月。
很多新股發行竟出現了20個漲停板,從發行價3塊多錢漲到了70多塊,這種現象會使存量股票的價格跟著它走,最后只能被打回原形。那么,對新股發行制度我們是否應該反思?對發行后莫名其妙的無限制上漲,監管部門是否應該警覺和監管?
《南風窗》:IPO注冊制改革提出已經近兩年了,為何一拖再拖,難點是什么?暫緩,會不會使短期內二級市場供大于求的狀況更加突出?
吳曉求:注冊制的改革是不能扭轉的,證監會的發審核準制維持不了多久,效力也差。股票新發要交給市場去做,交給中介機構,出了事它們負全部責任,必須把責權匹配起來。
推行注冊制的主要條件應該說已經具備了,基本的法律體系也有了,市場也成熟了。經過了這些年的發展,市場各方面對信息披露的理解也越來越強,越來越少的人有意地去搞虛假的信息披露,至少明目張膽的人還是減少了很多。投資銀行、保薦人、律師、會計師等中介機構以及執行評估機構的專業能力還是在提高,投資者對這些機構的識別能力也在增強。
現在,推進的難點在于《證券法》的修改問題,目前,它的修改本身存在很多爭議。包括注冊制執行會不會使供求失衡,怎么處罰違規違法行為,集團訴訟怎么引入、從業人員能不能買股票等等,這些問題還需要細化。所以,推行注冊制還需要不斷消除現行法律上的約束和障礙。
其次,市場對注冊制的認識還沒有到位,很多人認為注冊制改革后,這個市場就沒有約束了,什么企業都可以注冊,注冊了就可以上市。不是說注冊制執行后,上市的企業就無限多了,一定要有一個相配套的退市機制。
《南風窗》:證監會前主席郭樹清曾痛斥A股市場“炒新、炒小、炒差”,這輪暴漲暴跌中,很多公司都由ST改組,在牛市中融到不少錢,暴跌后市值大幅縮水,投資者損失嚴重。退市制度常態化之后,炒作垃圾股的投資理念得到斧正嗎?
吳曉求:退市機制和退市標準最近幾年也在進一步完善和細化,但真正退市的上市公司并不多,因為快到退市的時候,上市公司背后的地方政府、大股東通常會想辦法。不能說想辦法是錯的,有人愿意收購它,有人把優質資產注進去,那也未嘗不可,但實際情況不全是這樣。
有些企業沒有任何業績起色,還能茍延殘喘,這樣的現象是不正常的。其實規則已經很嚴了,連續幾年虧損、資產是負的、交易價格低于面值等都在退市的標準里,但真正的退市上市公司就是沒幾家。注冊制要讓市場形成吐陳納新的良性機制,因此退市制度的嚴格執行必然是未來A股制度構建的重點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