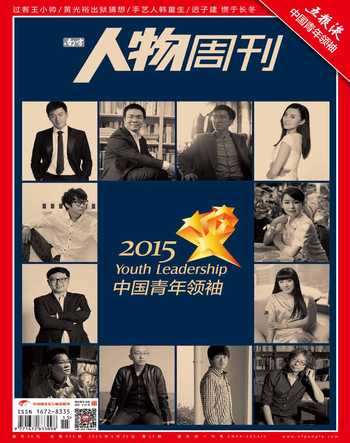李霄峰 我不打算成為完美的人
人物周刊:你對自己的現狀滿意嗎?
李霄峰:當我的第一部電影《少女哪吒》剛拍完時,我覺得很滿意了。但現在這滿意早已過去回到原點,因為下一部電影就要開始了。
人物周刊:對你父母和他們的成長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們嗎?
李霄峰:父親經常回憶他小時候游泳的池塘,說那時的水清澈、自由。母親則有一次跟我說家里3個兄弟姐妹,只有她從沒下地干過活,看上去她的童年和少年過得無憂無慮。后來他們來到省會城市拼搏,在各自的領域都做得不錯,在我看來是移民的一代、拼搏的一代。我反倒成了第一個出生在城市里的人。我對上一個時代并沒有多少感同身受,無論是建國后的饑荒,還是“文革”。因為我是改革開放之后出生,存在決定意識。我的記憶里或許留下了不少屬于上一個時代的烙印,比如大學里那些前蘇聯式的建筑,棱角分明簡潔明了的審美主張;還有從80年代的自由主義思潮到90年代的理想消亡與現實主義抬頭的交響、社會道德的禮崩樂壞。我的電影里已經開始有這些思考的雛形,但是我暫時沒找到一條路超越自己所處的環境和時代去理解別人。
我希望每一代人能從自己的身上找到意義,從而理解別的代際的人,因為人生的意義無論哪一代都是相通的。
人物周刊:對自己的下一代,你有什么期待?
李霄峰:說實話沒什么期待,希望他能比我更簡單快樂?但他將有屬于自己的體會,這似乎跟我一點兒關系也沒有,真掃興啊。
人物周刊:對你所從事領域的前景怎么看?
李霄峰:電影正在經歷一個黃金10年,這10年一定會比我入行的頭10年(2003-2013)更瘋狂也更有意思。我們肯定會遇到比過去更愚蠢更貪婪的資本,但也有在作品上更璀璨的可能。作為導演要思考的問題更多。事實上導演這個職位已經被拉下神壇,打上“某某作品”的做法更像是衣服流水線上的貼牌行為,正在變得無趣。我當然心醉于所謂“作者電影”的時代,導演的作者性毋庸置疑。但在我看來,他更應該是一個創作上的統領者,美學上的調度者,而不是一個所謂的表達者。我的劇組最多曾達到一百多人,他們每一個都是創造力很強的行動者,我不能夸張地說這些人的腦袋都在按照我的意志行事,說這是我一個人的作品。
人物周刊:同齡人中,你最欣賞哪些人?為什么?

李霄峰:我在電影《少女哪吒》里描述了一個叫李丹陽的年輕軍人。他的理想只有一個,就是保家衛國,為了這個理想,他必須放棄兒女情長——聽上去有點主旋律對不對?是的,我更欣賞那些有奉獻精神的人。10年前我在《可可西里》劇組,在海拔五千多米的五道梁兵營住了15天,我知道那些軍人的狀態還有情感故事。我曾經問過一個問題:村上春樹說在雞蛋和墻之間,他選擇站在雞蛋的那一邊,那么墻里面的雞蛋就不是雞蛋了嗎?生命并不是虛無的概念,而是實實在在的一個一個人。我經歷過個人至上的年代,也經歷過學校與社會甚至是權威對年輕人個性的壓迫,但是我欣賞那些能超越個人主義的人,為自己所在的領域奉獻力量并在所不惜的人。我有很多的同齡人都是這樣的人,警察、老師、工人、農民、電影導演,我在生活中真實地感受過他們對事業的追求遠遠高于對個人幸福的追求,對事業的需要遠遠高于對功名的需要。回到倫理的領域,我欣賞丈夫和妻子,我見過照顧家庭的妻子,也見過照顧家庭的丈夫,他們在日常生活中身體力行地維護家庭的觀念不讓外面的風浪沖散,這或許是一種更加普通也更加了不起的奉獻。
人物周刊:責任、權利和個人自由,你最看重哪個?
李霄峰:責任。
人物周刊:對你影響最大的一本書,或者一部電影。
李霄峰:從我25到30歲左右,一直在看《包法利夫人》,那是一本近乎完美的小說,福樓拜完全是從零角度在觀察和描述人和事物,他在審美上給了我很大的啟發與沖擊。后來我接觸了托爾斯泰的幾篇小說,托爾斯泰比福樓拜偉大。他們之間只差那么一點點,但就是這么一點點決定了托爾斯泰的高度,就是他在描述同樣的人和事物時帶著精神的痛苦,帶著毫不妥協的價值判斷。我能聽見他不停地在問為什么,試圖接近他心中的上帝,他不僅認為自己筆下的人物有罪,也認為自己有罪,這不能完全歸結于他有宗教信仰,這是精神世界的問題。
電影則是《飛越瘋人院》,我是在26歲時看的它,看完之后久久不能動彈。
人物周刊:較為珍視的自己的一個品質是?最想改進的一個缺點是?
李霄峰:說實話我覺得自己渾身都是缺點。我并不打算成為一個完美的人,所以我沒什么可珍視也沒什么想改進,現在這樣正正常常的挺好。跟我的電影一樣,好的品質與缺點都在其中,不可分割。
人物周刊:最不愿意把時間浪費在哪方面?又最愿意將之花在哪方面?
李霄峰:最不愿意把時間花在吃飯和聊閑天上。最愿意將時間浪費在睡覺上。
人物周刊:現在的你,還有哪些不安和擔憂?
李霄峰:挺多的,主要是關于下一部電影,還在尋找契機去開始。我希望自己依然能像第一次一樣去拍第二部,但毫無疑問我比從前稍微謹慎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