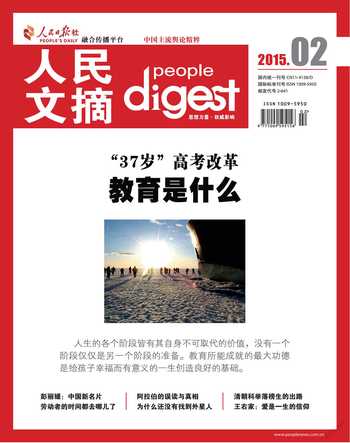美國的窮人福利
布拉德福德·德隆
自1979年以來,美國醫療計劃的擴張,使得合理計量的實際窮人福利增長,其增速并不比真實人均GDP慢多少。但1979年美國的醫療覆蓋面和融資差距意味著,其不平等程度遠比收入分配數據顯示的嚴重。
故事是這樣的:1979年,羅納德·里根就任總統前的最后一個商業周期達到頂峰,自那以來,美國經濟增長一直為富人獨享。
美國窮人和中產階級家庭的真實(經通脹調整的)工資、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升微乎其微。盡管真實人均GDP平均每年增長了72%,從2.9萬美元增加到5萬美元(以2009年的物價衡量),但該增長幾乎全都流向了美國收入最高的人群。
這些都是真事,但需要做一些重要提醒。其中之一見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2013年發布的《家庭收入和聯邦稅負分布報告》(The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Income and Federal Taxes)。
2010年,美國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家庭真實稅后收入比1979年高了49%,平均每年增長了1.3%。同期,中間五分之三家庭稅后收入增加了40%,相當于平均每年增長1.1%。
收入在81~99百分位的家庭稅后收入提高了64%,而收入前1%的家庭稅后收入提高了201%,平均年增長率為3.6%,漲幅比其他收入群體都要高。而如今的經濟復蘇也主要集中在富人群體,收入前1%的美國人自1979年以來的累計收入增長可能將接近300%。
但是,中等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的真實收入增長每年也分別有1.3%和1.1%,也不算太糟。與人均GDP的平均年增長率(1.6%)的差距似乎也不大。
對此,樂觀者(或辯護者)會說,自1979年以來,盡管市場收入變得日益不平等,收入分配下半段的人群的真實收入占比節節敗退,稅收的累進性也日益減弱,但福利國家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緩和了不平等性的加劇。
看看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的統計,最底層五分之一人群真實稅后收入1.3%的年增長率,其中0.9個百分點的增長來自醫療保險、醫療補助和各州兒童醫療保險計劃的增加。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將這些計劃的增加全部計為美國窮人家庭真實稅后收入的增長。但是,美國窮人無法消費這筆錢,因此在計算時應該進行相應的下調。
此外,這些支出中只有一半能成為這些計劃受益人所獲得的醫療服務的增加;另一半流入了美國醫藥費融資系統,用于覆蓋此前沒有償付的醫藥費。
美國醫藥費融資系統以效率低下聞名:其他經合組織國家單位支出獲得的健康和醫療服務比美國多出1倍有余。因此,美國公共醫保計劃擴張對美國窮人實際福利的貢獻,也許每年只有0.2個百分點。
2010年3月患者保護和平價醫療法案(又稱“奧巴馬醫改”)等強制性個人醫療保險十分必要,否則就得咬牙采用單一付款人醫療融資系統了。無論如何,美國巨大的醫療支出需要產生與其他經合組織國家相當的價值。
坦白地說,對于政府醫療融資計劃的擴張與不平等性之間的關系,我的看法有點互相矛盾。
一方面,我的基本觀點是,1979年以來,美國窮人實際福利年增長率為0.5%,而美國富人為4%,超級富豪更是高達6%。這是因為擴張的大部分并未給美國窮人收入帶來相應的增加,也因為美國醫療融資的價值相對低下。
但是,另一方面,我的基本觀點與此大不相同。1979年,美國窮人在健康和醫療方面與普通經合組織社會民主國家差距巨大,即使每增加1美元支出只產生了0.25美元的實際醫療服務,對窮人來說這0.25美元的價值約為1美元。
照此看來,自1979年以來,美國醫療計劃的擴張,使得合理計量的實際窮人福利增長,其增速并不比真實人均GDP慢多少。但1979年美國的醫療覆蓋面和融資差距意味著,其不平等程度遠比收入分配數據顯示的嚴重。
(作者為美國財政部前助理副部長,現為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教授、國家經濟研究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