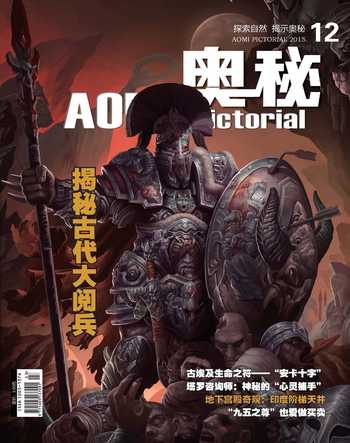掙多少錢由你的姓氏決定?
潤語
熱播美劇《冰與火之歌》里攀爬事業最成功的應該是太監瓦里斯。他曾經是個奴隸,受盡了欺辱,后來靠著自己的努力和聰敏的頭腦成為了權勢熏天的情報大臣,掌握無數人的生死。像這樣的人物奮斗故事在影視、書籍等作品中隨處可見,他們完美地符合我們從小就被灌輸的觀念——自身的努力奮斗是成功的最關鍵因素。然而美國著名經濟學教授高利·克拉克卻斬釘截鐵地告訴你:決定你未來的財富、事業和社會地位的是你的姓氏。
父親的階層對子代影響大
克拉克教授是在他的新書《子孫照樣發達》一書中得出這個結論的,盡管這個結論有些驚世駭俗,但無論是經濟學家、經濟史學家還是精通此類研究的學者教授們卻都很難對該書的數據模型、方法詮釋提出質疑,因為克拉克調用了大量歷史舊檔并征集了歷史的實證數據,集中考察了多個社會,包括英國、日本、印度、韓國、中國、美國、瑞典、智利、丹麥等國家,以及猶太人、吉普賽人等群體的長期演化,實證數據的跨度長達幾個世紀,英國的數據更長達九百余年。然后運用統計學和經濟量學海量分析,力圖使結論跳出小概率、小地域以及狹窄時間段的影響,使之更客觀和正確。
他的研究從中世紀英國開始,在此之前英國人是僅有名,沒有姓的。研究人員追蹤了與工匠職業相關的姓氏,比如史密斯(Smith)意指鐵匠、貝克(Baker)意指面包師、卡彭特(Carpenter)意指木匠等,這些姓氏在十二世紀左右出現,局限在這些有一定技術、地位高于普通勞工的人群中。為了追蹤這些人的社會階層流動性,克拉克教授查閱了自十二世紀以來牛津和劍橋大學的學生名單、受到認證的遺囑等,發現自十三世紀以來,雖然英國經歷了科學革命、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但這一群體的階層流動性仍十分緩慢,代與代之間財富和社會地位變化不大。與此同時,追溯英國貴族罕見姓氏的工作也在進行,上層社會人士,即那些姓氏和他們擁有的土地相關的人群,雖然社會地位和財富在幾百年內逐漸降低,但他們仍然居于所處社會的富裕階層,甚至更高。
克拉克教授把這種人類社會的高粘滯現象稱之為“社會執著度”,并根據數據模型計算出子代受到父親階層的影響為75%左右,孫輩和祖父輩的相關性為56.25%,第四代受祖輩的影響則為42.19%…… 直到第十代,祖上持續的影響仍有可觀的7.5%。克拉克認為“社會執著度”是不變的常數,與文化、制度安排等無關。
那么在那些當代國家中一般被認為社會階層流動性最高的國家,比如瑞典、日本等國家情況如何呢?
中國13個姓氏的名門望族從未衰落
與英美相比,這些國家對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做得比較認真,高低級職位間的工資差別相對較低、累進稅制比較嚴格、醫療教育服務等對全民免費,使得不同階層都享有相近的社會福利。但是克拉克等人采用姓氏研究對瑞典貴族院成員進行了分析,發現從十九世紀初到今天,在社會地位和財富狀況上,上流社會家族的后代依然勝過普通人。例如,貴族的名字出現在瑞典律師協會律師名冊上是一般公眾出現的頻率的6倍,帶有貴族姓氏的人群收入比姓“窮人姓”的人高8.9倍,并且這些國家的“社會執著度”與英美的幾乎持平,父與子之間的影響仍然保持在70%-80%左右。
那么克拉克的姓氏經濟研究是不是也適用中國呢?要知道中國人使用的姓氏非常少,13億人口大概只使用100多個姓。克拉克和他的中國學生郝煜從《明清進士題名錄》中找到了研究的切入點,他們從名冊中找出了13個罕見姓:諸、竺、茅、濮、裘、巢、惲、端木、鈕、忻、薩、笪、宓。根據1820年至1905年的科考數據顯示,這些姓的人比王、李、張這“全國三大姓”獲得進士的比例高8.6倍。因為在《明清進士題名錄》中,這13個姓集中在江南一帶,所以除了“全國三大姓”外,作者還選擇了顧、沈、錢這“江南三大姓”作為另一組對照,“精英十三姓氏”獲得進士的比例是“江南三大姓”的4.7倍。
為了分析不同時代不同群體中這些姓氏的分布,克拉克等人還選擇了1912-1949年間國民黨政府高級官員、2012年中國排名前十的大學教授、2006年資產超過150萬美元的公司董事長、2010年中央政府官員這四個精英群體。結果發現在這四個群體中,13個“貴族姓”的相對比例都遠遠高于“全國三大姓”。即使拿“江南三大姓”做對照,相對比例依然偏高,這說明盡管中國十九世紀末到現今,盡管社會體制發生過翻天覆地的劇烈變革,明清時代的“精英”群體,到了21世紀還是社會精英。
想要孩子成功,先找個好配偶?
為什么這樣的結論與人們對社會流動性速率的印象如此不同?克拉克的解釋是,人們意識的重心是短期的,他們關注的焦點在代際變化,只是兩代人之間發生的變動,這時隨機因素(比如各種運氣,包括好的運氣或壞的運氣)起了很大的作用,從而掩蓋了真實的訊號。
還有部分來自誤算。人們以物質收入的影響替代了社會流動性。其實,競爭社會地位、獲取資源的能力是綜合性的,除了財富,還有教育、職業、社會聯系、健康狀況、是否長壽等,都是構成“社會成功”的元素。
那么我們能做的是不是就僅剩下一點了——若想孩子成功,替自己找個好配偶?當然這是個好建議,但也要注意,配偶的“好”,不在于他(她)是否有錢或生于有錢的家庭,也不在于其面貌是否很好,而在于其生父母的財富、教育、職崗、社會網絡、健康長壽等因素的綜合考量;其次更主要的是,要考察其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曾祖父母以及更上代人是否也成功。從長計議,才能確實把握他們的成功是否有堅實的根基。
當然,克拉克教授也強調了個體后天努力的重要性,他認為雖然個體有社會階層的差異,但這并不等于說社會階層流動性就不存在了(即使緩慢,但仍然存在),或是不需要個人的后天努力了,或是社會平等沒必要了。他指出,即使生來就有較強的競爭力,但要實現成功的人生還是必須通過后天努力;在每個人的人生道路上還是有許多不確定的因素。如果一個社會能夠將資源最大程度的向底層傾斜,還是能夠大大地改善整個社會的健康和教育水平,提高每個人的個人能力和綜合生活質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