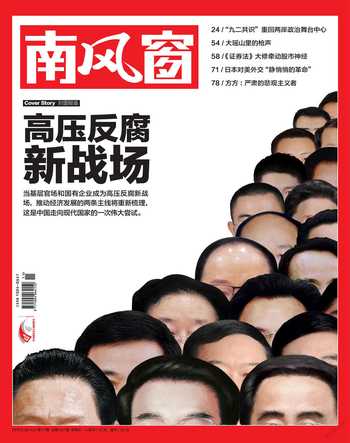凝視世界,凝視自我
夏循祥
曾經,我們翻譯西方名著,學習西方理論,以西方的視角為中國定位。然而,以西方之眼來凝視中國,總給人以仰視者或者追趕者的姿態,缺少自我,也缺少參照。
超越意識形態,在文化多元的世界與悠久的人類史中重新定義并定位中國,是新世紀學術人被賦予的歷史使命。我們不能幻想傳統中國的文明體系不證自明,不用變化就可以幫助我們在當代立足。我們只能在一個更為艱難也可能更為漫長的進程中去構筑屬于當代中國的文明體系及其視角。我們迫切需要建立在平等、相互、自由基礎之上的學術知識,也就是“用中國人自己的眼睛”去重新看待西方,認知世界,認識中國。
社會科學知識的繁榮昌盛,既是國家地位、文明聲譽、文化認同的前提,也是其后果。我不知道有多少美國學者在研究中國,不知道有多少研究中國的美國學者來過中國,但我相信,他們獲得的第一手資料以及研究的態度、方法、發現和結論,都普遍超越研究美國的中國學者。這些年來卷帙浩繁的海外漢學研究,當是明證。當代中國的社會科學發展與積累還遠遠不夠。中國的海外研究長期以來也多側重政治、經濟、外交等層面,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國別文化的多層次和多維度。荒廢的時光和曲折的道路,需要全體學術界的共同努力。而人類學將是中國知識界的“眼珠子”和“腳板子”,肩負著這一重任的啟航。
近年來,中國的海外民族志研究逐步興起。中國的民族志工作者開始深入他者社會,用當地的語言在當地進行為期一年左右的參與觀察,真實、具體地展現他們的生活性文化,并以當地人的觀點來理解他們。這種“用中國人自己的眼睛”的觀看實踐,既豐富了中國人類學現有研究方向,又推動世界人類學的跨文化實踐,對于當代中國文明體系的建立更具有重要意義。如果有一天,每一個國家或者地區,都有中國人在做經驗研究;研究的成果不僅能夠為中國所用,也能夠為當地人所用,為世界學術體系所認可,我們才可以說,開眼看世界的任務基本完成。
“中國人自己的眼睛”,意味著要摒棄歷史虛無主義,不能忽視中國文明曾經的偉大,以及1840年之后中國人的多種努力,從傳統文化中發掘人類共同的價值觀來與世界對接。“中國人自己的眼睛”,意味著要摒棄民族中心主義,不僅要重新審視曾經高高在上的西方,也需要平等看待同在發展的其他國家和地區,更要學會以自信、自尊、自強的態度在世界版圖中重新審視自己。“中國人自己的眼睛”,意味著要在世界性社會科學的范疇內努力發展原創性理論,在多重現代性中尋找“中國性”。
當今中國在與世界的相互凝視中,發現彼此原來如此不同,也如此相同。平心靜氣地凝視世界,也是為了更好地凝視自我,更好地理解中國,看待我們眾多的民族,豐富的族群與地域文化,細致而曲折的歷史變遷與融合,甚至在世界性社會里發現那些被忽視或丟失的“原味中國”。
為中國展示世界,向世界展示中國,是中國學術在新世紀的使命。到海外去,是一條充滿艱辛的道路,也需要一個過程。從著眼國內到著眼國外,背后有政治關懷,也有經濟支持、觀念方面的因素。盡管還有一些制度、資源方面的限制,但是“走出去”已經成為政府到民間的基本共識,并有所切實發展。總有一天,中國學術也會如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一樣,被世界關注,被世界欣賞,被世界珍視,成為世界學術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