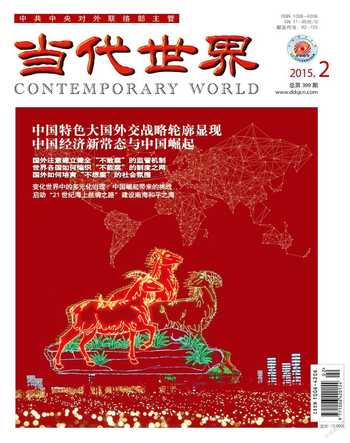國外注意建立健全“不敢腐”的監管機制
石曉虎

當前,世界各國雖重視腐敗監管工作,構建了不同形式、各具特色的監管機制,形成了一道道無形的“高壓線”,但是監管不力、腐敗丑聞迭出的問題始終揮之不去。深入研究國外加強腐敗監管機制的做法及其不足對中國構建嚴密、有效的腐敗監管機制不無參考意義。
一、基于政治制度安排,建立健全制度性腐敗監管機制,遏制腐敗尋租空間
越老古等共產黨執政國家多將反腐確定為國家戰略,堅持黨對反腐工作的領導,形成黨、政府、司法、軍隊等相結合的一體化腐敗監管機制。越共設立由總書記任主任、中央政治局直接領導的中央防治腐敗指導委員會,成員包括九名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及七名中央委員;重建越共中央內政部,負責內部政治和反腐工作,以強化腐敗監管力度和查處重大腐敗案件。2013年越南政府監察總署共查處45起重大貪腐案,涉及99人,涉案資金達到1670萬美元。老撾2012年l2月通過《到2020年反貪污腐敗戰略》,明確反腐的重要性、目標、具體措施和辦法;2013年6月通過《關于干部財產和收入申報制度的規定》,明確黨對財產申報工作的領導以及各級政府監察機關的主體地位,詳細規定申報對象及申報內容、分類和時限,明確對申報材料的管理和使用以及對不實申報的懲處。古共視反腐為關系到黨和國家命運的斗爭、保衛革命成果的斗爭,高度重視腐敗預防工作,頒布《國家干部道德法規》,對黨員干部提出高標準的道德要求;在中央、省、市設立三級監督和監察委員會、申訴委員會,強化黨內監管;重視黨外舉報,設立由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員領導的全國群眾舉報委員會;設立對全國人大和國務委員會負責的共和國總審計署,強化腐敗監管力度。古共中央在懲治腐敗問題上態度堅決,在特殊時期規定領導干部貪污受賄金額在300比索(約12美元)以上者不論職務高低一律免職,情節嚴重者移交司法部門處理。l992年以來,古共先后有兩位中央政治局委員因與不法商人有牽連或以權謀私被免職、判刑。
資本主義國家在腐敗監管設計上多強調制衡原則,監管機構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約。在形式上,既有傳統的議會監督、行政監督、司法監督,也有獨立機構監督,如反貪委、獨立檢察官、廉政官、審計署等,形成相對規范的權力運行和監督機制。美國沒有全國統一的最高反腐敗協調與執法機構,聯邦與州、州與州之間的情況不盡相同,調查公共部門腐敗的權力分散到政府各部門的監察長辦公室、司法部刑事局、聯邦調查局、聯邦稅務局犯罪調查辦公室等幾十個聯邦執法機構。巴西國會參眾兩院可單獨或聯合監督、調查大案要案,聯邦警察局負責調查包括腐敗、洗錢在內的刑事案件,聯邦監察總署設有預防腐敗、透明建設、監察專員等機構,聯邦檢察院可獨立調查違反公共利益的案件。巴西總統羅塞芙上任十個月,政府24個部門中就有五位部長因涉嫌腐敗被司法機關指控而去職。新加坡總理公署貪污調查局獨立行使國家肅貪職能,由總統任命、向總理負責,可以行使刑事訴訟法賦予的一切與調查相關的特別權力,無需逮捕證即可先行逮捕任何涉嫌貪污受賄的人。該局內控機制也非常有效,近期,前助理司長楊少雄因挪用176萬新元公款被判刑十年,局長陳宗憲連帶被撤。加拿大審計署負責對腐敗的監管、打擊,由議會設立并向議會負責,其領導人一般由反對黨代表擔任。腐敗監管機構除預防、懲治腐敗外,有時還被賦予一定的人事任命監督權,如近期印尼反貪委確認新總統佐科提交的43位部長候選人中有八人未通過清廉審查,必須重新提名。
二、完善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健全黨內腐敗監管機制
一些政黨認為黨員干部屬于公民,已受國法約束,無需再在黨內制定設立反腐機制,大多將《政黨法》、《選舉法》、《政治獻金法》等國家法律法規對政黨的要求轉化為對黨員及黨員干部的要求。如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在道德、舉止行為等方面對黨員進行強力約束,但是黨內未建立相應紀律檢查制度,而是更多訴諸國法監管腐敗行為。
而有些政黨則認為,腐敗是危害黨的肌體的毒瘤,不僅破壞黨的形象和戰斗力,而且危及黨的生存,因而注意建立嚴格的黨內規章制度,嚴明紀律,懲治腐敗。一是完善黨內監管機制,對黨員干部財產申報、利益沖突等問題進行全程監管。德國社民黨、法國社會黨分別在不同層級設有監察委員會、協調委員會,其與同級黨組織處于平行地位,參與同級黨組織活動、跟進監督,防止可能產生的黨內腐敗行為。前幾年,法國社會黨因腐敗或紀律問題,先后將前總理法比尤斯、外交部長庫什內、預算部長卡于扎克開除出黨。有些政黨的黨紀要嚴于國法,對不是公務員的黨員也做出財產申報規定。如,丹麥自由黨規定,每個黨員的財產都要對外公布,黨員的財產、土地、住房都要經過注冊,對違規行為予以嚴懲。還有不少政黨注意完善黨內述職、質詢等機制,嚴格考核黨員干部,使得干部受到更多經常性監管。二是規范黨內財務管理制度,防止黨產、黨費的濫用。墨西哥革命制度黨成立“透明小組”,定期開展內部審計并公布黨的經費來源和使用情況。這改變了以往革命制度黨黨內經費使用混亂的局面,遏制了腐敗的空間。三是對黨員干部候選人提出嚴格要求,防止帶病提拔。土耳其正發黨規定,要避免使政治淪為奸商的工具,黨籍公職候選人必須以公開、透明的方式接受黨員群眾的檢查,凡官商勾結、涉貪的人均喪失被提名權。馬來西亞總統規定,涉貪干部一律不予推薦參選公職,近年來取消了多位涉貪高官的參選資格。
三、強化社會輿論的腐敗監管機制建設,自下而上遏制腐敗
國外新聞輿論、公民社會更多介入社會政治事務,成為對官方腐敗監管機制的重要補充。
一是新聞輿論特別是互聯網利用自身優勢,深入揭露腐敗黑幕,對政府權力形成經常性的外部監督。如,德國、英國媒體利用政府對媒體知情權的認可,聚焦政府要員和公務員等熱門群體,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進行日常性追蹤,乃至出高價收購小道消息或內幕消息,并進行廣泛報道。2009年,英國媒體熱炒國會數百名議員虛報冒領國家補貼、以權謀私的丑聞,導致議會下院議長辭職、多名政府高官下野、執政黨工黨遭受重創。新加坡主流媒體實行“輿論專政”,將政府官員腐敗、作風問題大尺度、全方位曝光,讓貪腐官員名譽受損,很難在人群聯系網絡較小的新加坡社會繼續立足和發展。一些新興媒體還通過設立腐敗舉報網站、傳播涉貪信息等方式,對腐敗問題進行曝光,擴大社會關注度,推進查處進程。
二是非政府組織通過專業知識培訓、專業分析以及與官方腐敗監管機構合作等方式,協助監管、打擊腐敗。如,加拿大“問責制促進會”負責對民眾進行反腐培訓,指導民眾依法舉報;“納稅人聯盟”創立“泰迪政府浪費獎”,鼓勵民眾檢舉不同層級政府的貪污浪費情況,激發了民眾舉報腐敗的意愿。巴西民間組織成立“公開賬戶”機構,通過分析公共資金流向,揭露一系列丑聞并使腐敗分子得到應有的懲處。韓國全國3000多個社會團體開展對各類公職人員的監督,形成相互連通的數據庫,及時對發現的問題進行舉報,使得腐敗監管更為嚴密。
三是公民發揮監督主體作用,更多參與腐敗監督,形成全民反腐氛圍。一方面,一些國家尊重公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等,鼓勵公民更多參與對官方工作的監督并不斷探索利用民眾反腐的方式方法。如,巴西官方招募一批出租車司機作為“線人”,通過其掌握乘客透露的涉腐信息并在查實后予以處理。另一方面,公民利用言論、結社等權利,以集會、請愿乃至抗議等方式,要求政府在反腐問題上做出回應。如2011年6月,印度兩名“海歸”設立名為“我行賄了”的網站,方便民眾將生活中被索賄的故事揭露出來,推動政府改進辦事流程并遏制腐敗高發態勢,在印度社會產生很大震動,一批濫用職權和以權謀私的官吏受到懲處;8月,印度反腐斗士阿納·赫扎雷聯合其他反腐人員,以絕食方式要求政府加大反腐力度,最終迫使印度政府做出妥協。
四、加強跨國腐敗監管機制建設,提升國際反腐合力
各國政府高度重視經濟全球化、區域一體化快速發展以及跨國經濟活動日益增多背景下的跨國腐敗問題,大力推進跨國腐敗監管機制建設,深化國際反腐合作。
一是主動擴大腐敗監管法律的覆蓋范圍,監管更加有力。繼美國之后,英國通過《反賄賂法》,宣布英國公民或根據英國法律注冊設立但在英國以外國家或領土上發生的賄賂行為都受該法約束。巴西也通過《誠信公司法》,規定涉及國內和海外賄賂行為的巴西公司承擔嚴格的民事和行政責任。在巴西設有下屬公司的跨國企業,如在巴境內進行賄賂,亦受該法管轄。跨國企業的運營受到母國以及所在國更大程度的監管,以賄賂等不法手段經營面臨更多風險和懲治。
二是加強對腐敗分子、資金外逃的截、堵工作,對腐敗分子形成強大震懾。如,馬來西亞建立腐敗人物數據庫,外國駐馬使館可據此拒發簽證,有效防止了相關腐敗分子出逃。部分國家還要求特定國家嚴格審查入境的外國人特別是移民,把腐敗分子、資金堵在國門外。
三是加強國際反腐合作,密切跟蹤、追查腐敗分子和資金。部分國家對“避稅天堂”提出警告,促其加強自我管理和有效開展國際合作。如法國每年公布一份“避稅天堂”名單,要求其與法國稅務機關密切合作,取消銀行信息保密制度,以便法國了解、打擊跨境資產隱匿和洗錢行為。有些國家簽署雙邊引渡、司法合作的協議,直接開展反腐合作,如西班牙和安道爾等國簽署司法互助協議,在信息共享、互派調查小組方面開展合作,以切斷跨國腐敗資金流動。有些國家雖未簽署雙邊反腐合作協議,但也利用《聯合國反腐敗公約》、《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禁止在國際商業交易中賄賂外國公職人員公約》等有關條約中的國際合作條款,以及借助國際刑事警察組織等開展國際合作,引渡腐敗分子、追繳流失資產等。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研究室)
(責任編輯:劉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