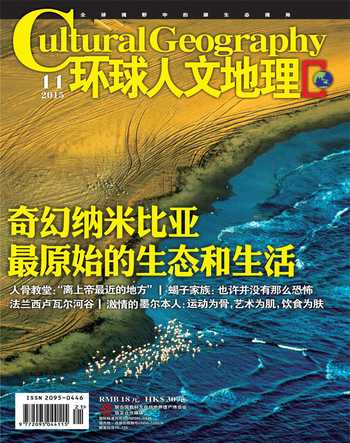食貨志中的嘉州風(fēng)物
龔靜染

詩人、作家。1967 年冬生,四川樂山人,現(xiàn)居成都。著有詩集《影子》、歷史隨筆集《小城之遠(yuǎn)》《橋灘記》、長(中)篇小說《浮華如鹽》《民國少年》《光陰交錯》等,主編有《中國第四代詩人詩選》。
同一種物產(chǎn),因為時代的不同而身價殊異。如麩金,也就是如麥麩一樣細(xì)小的金屑,在宋代是樂山的貢品,但到了清嘉慶時期就不再稀罕了……清末民初,樂山風(fēng)物逐漸變得豐富,“山水清華,農(nóng)商繁庶,文物衣冠之盛遠(yuǎn)邁往時矣”……反觀蠶桑之興,則是一些風(fēng)物的衰落,對比不同年代的《嘉定府志》就能看到巨大變遷,為我們呈現(xiàn)了另一番事實(shí)。
說到四川樂山的物產(chǎn),在《益部方物略》中有句話,叫“嘉產(chǎn),爛如也”。樂山地處中亞熱帶,在四川盆地與橫斷山脈之交,自然條件復(fù)雜,土地沃美,植物繁多,這是大地理;清嘉慶《嘉定府志》又說:“蓋郡當(dāng)三水之會,大峨之英,散而為華,凝而為實(shí),醴泉芝草生為圣時之瑞,亦其宜矣。”這是小地理。大小一合,樂山的方輿形勝就一目了然了。
但這只是攤開的一張地圖,而一方水土并非靜態(tài),其風(fēng)物也隨時間而變遷,如世間生命之此消彼長。在樂山歷代的志書記載中,我們會發(fā)現(xiàn)每一個時期關(guān)于方物的記載都有細(xì)微的差別,細(xì)細(xì)比較會看出經(jīng)濟(jì)、文化、歷史等諸方面的變遷,這都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時代不同的風(fēng)物之異
在樂山的方物中,早期的記載以貢品最為醒目,如“古貢水波綾、烏頭綾、苓根、紅花,今貢麩金、紫葛、巴豆。”(宋·樂史《嘉州龍游縣記》),這句話不僅說出各領(lǐng)風(fēng)騷數(shù)百年的真理,還說出了唐代與宋代的貢品的差異: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需求與崇尚。明朝以后,對方物的記載趨于大宗,但當(dāng)時樂山的風(fēng)物記載還比較單一,如“鹵之水,水之火,乃在南犍;木之綿,綿之縷乃在榮威,刳之才,楮之生乃在夾洪……”(明萬歷《嘉定府志》),這里說的鹵水、綿、楮等分別對應(yīng)的是鹽、布帛和紙,這些東西為昔時之盛,跟人們的生活極為密切。到了一百年后的清朝嘉慶年間,變化就比較大了,“峨眉之茶,沫水之麩金,洪雅、夾江之紙及蟲白蠟,樂山、犍為之鹽及麻、布、絹、綿、石灰,皆民生日用所常需,而地方有產(chǎn)有不產(chǎn)者,流通尤廣”(清嘉慶《嘉定府志》),不同時代一對比就能看出其中的差異。
同一種物產(chǎn),因為時代的不同而身價殊異。如麩金,也就是如麥麩一樣細(xì)小的金屑,它在宋代是樂山的貢品,“日獲不過毫厘”。但到了清嘉慶時期就發(fā)生了變化,“麩金”只被納入“金石之屬”中,跟鐵、硯、土硝、菩薩石、水硫磺等礦物放在了一起,已不再是稀罕之物了。與之形成對比的是一種叫“蟲白蠟”的樹,它們同時記錄在嘉慶年間的《嘉定府志》中,但“蟲白蠟”卻被重重提了一筆,證明在史家的眼里,麩金已不如白蠟。
其實(shí),樂山養(yǎng)“蟲白蠟”之俗并非新鮮事物,但并不廣泛,直到18世紀(jì)末期才大興栽培白蠟樹之風(fēng),此后很長一段時間,這種喜歡陽光的小葉喬木成為了主要經(jīng)濟(jì)作物。以民國的樂山屬縣犍為為例,“縣境歲產(chǎn)蠟約二千擔(dān)左右,值銀二十萬上下”(民國《犍為縣志》);在離樂山20公里的五通橋順河街一帶,白蠟被當(dāng)?shù)厝朔Q為“橋蟲”,可以說是養(yǎng)白蠟之風(fēng)大盛。麩金與白蠟的不同際遇,為學(xué)者們提供了風(fēng)物變遷的證據(jù)。
風(fēng)物之豐的歷史原因
清末民初是樂山風(fēng)物逐漸變得豐富的時期,“山水清華,農(nóng)商繁庶,文物衣冠之盛遠(yuǎn)邁往時矣”(嘉慶《嘉定府志》)。這期間,各類書籍中對樂山的物產(chǎn)記錄也多起來,如光緒二十九年(1903),傅崇矩在《川江游記》中就記錄了樂山“出荔枝、墨魚、絲帕、湖縐、大綢、豆腐、彷紹酒、瓜子、白蠟、鉛、紙”;又如光緒三十二年(1906),日本人中野孤山在他的《游蜀雜俎》一書中也詳細(xì)記錄了樂山的物產(chǎn),如白蠟、蠶絲、土藥、毛茶、葉子煙、大綢、湖縐、燈草、老酒、紹酒、包谷燒酒等。除了記載的日趨詳備外,樂山的風(fēng)物之豐主要有以下兩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物種的引進(jìn),如釀制“紹酒”的紅苕和釀制“包谷燒酒”的玉米,都是在清朝時期由番夷引入栽種。樂山最早種植“玉蜀黍”(玉米)的記載是在嘉慶《嘉定府志》上,列入“谷之屬”中,這個細(xì)微的變化透露了一個信息,即一個新物種在樂山的出現(xiàn)。其實(shí),這也反映了中國農(nóng)作物耕作格局的變遷,說明樂山種植玉米是在康熙以后、嘉慶以前,即17世紀(jì)中后期到18世紀(jì)后期,玉米已經(jīng)在川南土地上生根發(fā)芽了。
紅苕也是蕃物,但在樂山引進(jìn)得更晚,應(yīng)該在咸豐、同治以后,樂山屬縣井研就有相關(guān)記載,“其種賤易植,野人墾掘荒坡、峻坡遍種之,以擔(dān)量,有收至數(shù)百擔(dān),貧戶倚為半歲之糧”(清光緒《井研縣志》)。由于這些后來的農(nóng)作物的種植不斷擴(kuò)大,對樂山的種植歷史有巨大的改變,嘉州有民諺叫“紅苕半年糧”,這句話在清朝前是難以想象的,因為那時當(dāng)?shù)厝诉€沒有見過紅苕是什么樣子。玉米的情況也相似,它一出現(xiàn)很快就在樂山的主要經(jīng)濟(jì)作物中躍居第三位,一改過去粱、麥、黍、稷、粟等為主的種植格局。
另一方面是經(jīng)貿(mào)的促進(jìn)。如蠶絲、大綢、湖縐等,本來是傳統(tǒng)物產(chǎn),但它們的變遷也不小。在康熙以前,除了極少的精品,樂山的棉布“皆欠細(xì)密”,絲則“不多,其養(yǎng)蠶之具及絲織之法皆茍簡不精”(明萬歷《嘉定府志》)。而到了清嘉慶年間,蠶絲是“屬縣俱出,惟樂山最多。其細(xì)者土人謂之擇絲,用以作紬,或販至貴州,轉(zhuǎn)行湖地,亦冒充湖絲;其粗者謂之大夥絲,專行云南轉(zhuǎn)行緬甸諸夷”(清嘉慶《嘉定府志》)。這說明在樂山已經(jīng)廣種桑樹,并養(yǎng)蠶取絲,行銷遠(yuǎn)地。但為什么到了清朝初期才真正興盛起來呢?這是因為不僅要有自然條件,還要有市場,市場決定生產(chǎn),這才是“家家養(yǎng)蠶忙,戶戶織梭聲”的真正原因。
風(fēng)物之變折射人世間的興衰
樂山地區(qū)栽桑養(yǎng)蠶的習(xí)俗很早,除了“水波綾”、“烏頭綾”,還有“絹錦”、“綿紬”等都很有名,但正如前面所說,習(xí)俗并不代表經(jīng)濟(jì)繁榮,而樂山的桑蠶之風(fēng)是到了清朝時期才真正興旺起來。后來,由于水陸運(yùn)輸?shù)耐〞常K稽一帶顯得特別盛,“嘉定大綢”就主要來自這一帶,上賣華西壩,下銷渝滇黔,由于質(zhì)量花色上乘,市民爭相購之。當(dāng)時岷江邊的漢陽壩有“漢陽絲市”,與成都“簇橋絲市”齊名,是西南地區(qū)兩大絲市。
反觀蠶桑之興,則是一些風(fēng)物的衰落。對比不同年代的《嘉定府志》就能看到一個巨大的變遷,也可以說是志書為我們呈現(xiàn)的另一番事實(shí),即古嘉州歷史上曾經(jīng)稱奇的風(fēng)物已幾近消失。如嘉州曾經(jīng)被稱為“海棠香國”,但到清朝時僅僅“唯郡署數(shù)株”而已;又如過去被樂山人津津樂道的荔枝,也只有“郡城會江門有一株,今俱亡”。海棠、荔枝在唐時,能夠出現(xiàn)在樂山可以說都有其不凡的身世,“凡花木名海者,皆從海外來”(《花木記》),雖然名重一時,卻擋不住歲月的無情,所以,《嘉定府志》上也僅僅說“《海棠譜》所稱海棠、海紅,《文選》《圖經(jīng)》所稱荔子、橘柚之屬,抑亦信而有征”。其實(shí),就在幾十里外的嘉州屬縣犍為,荔枝樹卻很常見,在老百姓的眼里并無特別之處,制藤器也好,當(dāng)柴火燒也好,盡生活便利,但人世間的興衰,從風(fēng)物之變中就大可看出些玄機(jī)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