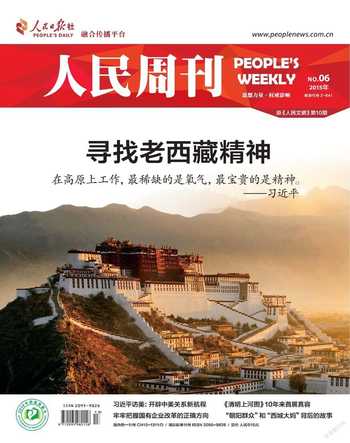新安保法案通過 專家稱應敬畏民意
李海燕 萬冰任鑒


日本當地時間9月19日凌晨2時18分,日本參議院全體會議以執政黨等議員的多數贊成,強行表決了安保法案。這意味著自今年7月以來,安倍政府力推的日本新安保法案正式升級為法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安保法案通過之后,前往靜岡縣小山町為外祖父岸信介掃墓。他向外祖父報告了解禁集體自衛權的安全保障相關法案在國會通過的消息。
日前,日本《朝日新聞》發布的一項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日本全國超過一半選民反對政府安保法案“過關”的計劃。民調顯示,54%的選民反對安保法案,僅29%表示支持;75%的選民認為,圍繞安保法案的討論不夠充分。
9月17日,日本執政黨與在野黨就參院和平安全法制特別委員會上表決安保法一事展開激烈交鋒。會上,委員長佐藤正久遭到在野黨議員的圍堵;會場外,反對安保法案的民眾在國會前集會抗議,要求廢除該法案。但是,執政聯盟仍憑借人數優勢強行將法案通過。從此,日本可以名正言順地行使集體自衛權,成為隨時“可以進行戰爭的國家”。
安保法案解禁集體自衛權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日本經濟專家、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客座研究員劉云認為,安保法案體現了安倍政府極右的傾向,核心內容是把自衛隊海外的行動權力極大地放寬。一是用“重要影響事態”取代“周邊事態”的概念,向美國盟友提供包括軍事資源的軍事支援;二是自衛隊可以在聯合國決議或受到相關國家邀請的情況下,從事海外人員的安全保障;三是可以開展威懾性活動,與國外軍隊共同開展有助于日防衛的活動,在發生核危機、海洋沖突的地區可與美軍及其盟友開展軍演或者進行部署。體現出來的特點是日美要在集體自衛權的相關領域展開合作。在解禁集體自衛權之前,日本不能針對日本以外的國家進行武力攻擊,而在相關法案修改之后則可以在集體自衛權這個領域展開合作,自衛隊還可以對美國的軍事活動進行支援。劉云表示,安保法出臺是以中國威脅論為前提。安倍在7月27日關于安保法案的國會答辯上提到安保法修改是基于亞太和全球力量變化,日本周邊安全環境根本性改變,列舉朝核問題、中國崛起等若干內容,同時提出當從事反導警戒的美艦有受到攻擊的顯著危險時,也屬于“存亡危機事態”,可行使集體自衛權,理由是附近某國有幾百枚可攻擊日本的彈道導彈,美艦遭攻擊會讓日本防衛系統出現漏洞,導致國家存亡受到威脅。這說明美國在周邊受到威脅時,日本無條件與美國進行聯合作戰,等同于把美國的安全作為日本的安全。
安保法案本質“助美制華”?
南開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張玉來認為,安保法案的確有“助美制華”的目的,但又不能簡單地這樣理解。安倍極力推行由11部法案構成的“新安保體系”,真實目的在于為最終修憲鋪路。新安保法案徹底突破了二戰后日本安保政策長期堅持的“專守防衛”方針,即僅行使“個別自衛權”。由此,日本和平憲法第九條也就被徹底事實架空,使和平憲法僅剩一個空架子,這就為安倍修憲鋪平了道路。“助美制華”只不過是安倍贏得美國認可的幌子,安倍從心底里是不愿對美國“俯首帖耳”的,這一點從其“東京審判是勝者的審判”歷史觀就可窺見一斑。他意識到美國實施亞洲再平衡戰略是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現在是讓日本摘下戰后“緊箍咒”的最佳時機。因此,安倍擺出“史無前例”地強化日美同盟的姿態,甚至打出中國威脅論,這些都是實現其目的的手段而已。
張玉來解釋說,新安保法案本質是戰爭法案。它讓日本重新擁有了發動戰爭的權力,盡管暫時還只是部分發動權,也就是行使集體自衛權。但是,這個缺口一旦打開,很可能一發不可收拾。例如,國會辯論中,安倍政權解釋集體自衛權或將用于美國之外的“他國”,這就為日本政府打開了再解釋的窗口。“海外派兵”只是新安保法案獲得的權力之一,而“行使武力”才是重大突破,因為1991年向伊拉克派兵還只能是非戰斗區域。
此外,“地球背面”等無限擴大作戰范圍、營救海外日本人等都是此次新安保法案擴大的權限。所以以行使集體自衛權為目標的新安保法案,本質上就是賦予日本再次發動戰爭的權力,這就實現了安倍政權在事實上徹底架空日本和平憲法的真實目的。
“草根”反安倍浪潮持續醞釀
正如張玉來所說,安倍政權并沒有因為民眾反對就主動放棄安保法案審議,因為這關系到其政治理念與合法性。但是,不能認為只有安倍政權放棄安保法案,才是民意真正發揮了作用。
張玉來指出,草根階層的反安保運動已經發揮了顯著而積極的作用,因為安倍政權已經意識到民意的重要性,并具有了強烈的危機感:其一,安倍史無前例地將通常國會延長了95天。由于三名憲法學者到眾議院作證指出“違憲”,安保法案審議遇阻,民眾開始上街抗議,安倍將會期延長至9月27日,這是安倍為該法案最終通過上了“雙保險”。其二,8月14日發表的“安倍談話”徹底“改口”。安倍曾表示將回避使用“侵略”和“殖民”以及“道歉”等關鍵詞,最終盡管在表達上模糊暖昧,但這些關鍵詞悉數進入“安倍談話”,很顯然,安倍被迫修正了自己的歷史觀,試圖以此來換取民意。其三,執政聯盟宣布不使用“60天原則”,以切實貫徹在參議院的嚴肅審議。自民黨、公明黨會談決定,執政聯盟宣布放棄使用其在眾議院三分之二多數議席優勢通過的原則。其四,在野黨也受到反安保運動鼓舞而醞釀提出內閣不信任案。最大在野黨民主黨代表岡田克表示,將攜手其他在野黨共同起草內閣不信任案和首相問責決議案。
很顯然,正是草根階層所掀起的大規模反安保運動,才讓安倍政權具有了強烈危機感。在眾議院強行通過安保法案之后,引發了大規模民眾上街游行,8月30日甚至出現12萬民眾包圍國會和“全國百萬人大行動”抗議示威活動。這種背景下,在9月9日安倍再次無投票當選自民黨總裁之后,他重新祭出經濟改革的大旗,試圖以推出所謂“安倍經濟學2.0”來繼續“招攬”民意,獲得更多支持率。表面上看,似乎民眾抗議并不能阻止安倍政權的“暴走”,但是民意如山。安倍最為重視的安保法與修憲議題都不得人心,日本民眾的各式抗議集會此起彼伏,致使其支持率也一再下跌。如果安倍政權一味“暴走”,其支持率從當前警戒線的30%繼續跌落至20%的話,那自公聯盟就可能破裂,或者由自民黨內出現的新力量取代安倍。正如中國那句古話,“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安倍必須敬畏民意才能真正實現其“長期政權”的美夢。
在張玉來看來,日本安保法案通過不會直接沖擊當下的中日關系,因為該法案通過與否是日本國內的政治博弈的結果。但是,它將在長期層面影響中日關系,因為它改變了中日關系的基本結構。新安保方案將使日本放棄長期堅持的和平主義道路,擁有了集體自衛權就意味著日本成為了所謂普通國家。包括中國在內的日本周邊國家,將必須面對一個新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的日本,地區安全甚至國際格局都可能因此而發生改變。因此,中國必須調整傳統的對日戰略與方針,依據新的形勢和動向而構筑新的對日策略,這都將帶來雙邊關系基本結構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