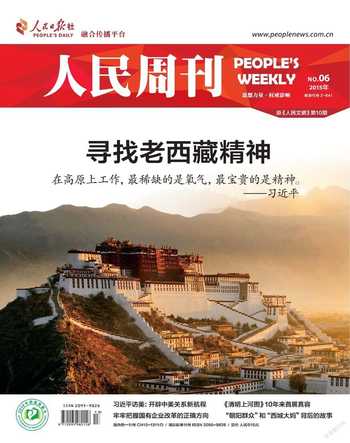論抗戰電影的流變與癥候
史博公

抗戰電影凝結著歷史創傷與現實訴求,也勾連著國際問題和兩岸關系。因此,其流變狀況既顯示了自身美學形態的演化軌跡,也映射著時代風云的變幻過程。
一、民國:吶喊、擔當、傾訴(1931~1949)
民國抗戰電影是華語電影的瑰寶,也是民族文化的榮耀。在國難當頭之際,它以“時代號角”的姿態發揮了警醒國人的作用;在國破家亡的當口,它以“電影抗戰”的實績踐行了激勵軍民的責任;在民族復興的歲月,它更以“秉筆直書”的情懷傾訴了過往的傷痛和現世的苦楚。
1.時代潮頭的吶喊(1931~1937)
在“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和華北事變的硝煙中,誕生了《共赴國難》《風云兒女》《大路》等首批抗戰電影,這批作品不僅在警醒國人方面功不可沒,而且在民國電影“從幼稚走向成熟”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在民族危機的強烈刺激下,民國電影迅速突破了“家長里短、婚戀糾葛、江湖恩怨”的窠臼,開始聚焦于國族存亡問題,這不僅讓電影題材得以大幅拓展,同時也使其文化內涵得到顯著升華。
正是在抗戰電影的帶動下,早期民國電影才轉向對“人與社會、家庭與民族、社群與國家”的思考與表現,這標志著民國電影在思想情感上已初步具備了“本土意識/家國情懷”,并因此步入了社會主流文化范疇。
抗戰電影促進了早期民國電影的美學建構。大量抗戰“新聞紀錄片”的拍攝則為民國電影注入了“紀實美學”的基因。此外,很多作品用隱喻、象征等手法含蓄地表達抗戰主題,也讓民國電影迅速超越了“寫實”的局限,開始步入“寫意”的境界。
2.電影抗戰的擔當(1937~1945)
全面抗戰爆發后,抗戰電影轉而受到政府大力扶持,成為宣傳抗戰的生力軍。此時抗戰電影的“生產主體”也已全部由民營公司變成國營機構。
在這一時期的作品中,“紀實風格”受到高度重視——它能為觀眾提供更加真實感人的視聽體驗,進而使宣傳效果得到顯著增強。如《長空萬里》《東亞之光》等影片在這方面均有出色表現。
為激勵軍民奮勇參戰,也為爭取國際援助,民國政府在此時還十分注重讓“電影下鄉,電影入伍,電影出國”。這使得電影在大江南北得到了空前普及;中國電影也第一次在國際上得到了廣泛傳播。
3、慘勝之后的傾訴(1945~1949)
抗戰勝利后,形成了國營機構與民營企業并存的電影格局。前者熱衷表現廣大軍民的抗戰業績,旨在提倡愛國精神,其內容大多壯懷激烈、積極樂觀,如《忠義之家》;后者重在反映布衣百姓的戰時創傷和戰后痛楚,意在追憶國殤、拷問現實,其格調大都沉郁悲涼、凝重哀婉,如《一江春水向東流》。
二、新中國:策略、訴求、局限(1949~1978)
新中國抗戰電影在“華語抗戰電影史”上享有十分獨特的地位,并擁有驚人的傳播廣度與深度。它影響了幾代人,至今仍被當作教育青少年的“紅色經典”。
1.大眾化的敘事策略
新中國抗戰電影無論在當時還是在后來都擁有大量觀眾,之所以能產生如此驚人的影響力,在很大程度上與其高度吻合了大眾審美傳統有關。
首先,這批作品的主人公均為基層官兵或農民,這使其自然具備了民間情懷,因而對觀眾更富親和力。
其次,《鐵道游擊隊》等眾多作品的劇情都極具傳奇色彩,當這些充溢著血與火、愛與恨的英雄傳奇被統一在“保家衛國”的麾下,被命名為“民族解放”的壯舉時,這些傳奇便有效地升華為黨的光輝歷史與人民的偉大勝利,從而在娛樂民眾的同時也肩負起了教育民眾的使命。
2.狹隘化的歷史觀念
與民國抗戰電影相比,此時最大的變化就是中共領導的“敵后游擊戰”成了唯一的表現對象。就此時的抗戰電影來看,無論講述了怎樣的故事、塑造了何種人物,這批電影出現了嚴重缺陷——遮蔽了“正面戰場”的功績;湮沒了“統一戰線”的格局,所呈現的只是一部片面的“抗戰史”,因而也就無法反映出我國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所作出的巨大貢獻、所付出的偉大犧牲。好在,這些缺陷在改革開放以后均漸次得到了修正。
三、新時期以降:統戰、反思、拓展(1979~2015)
受兩岸格局、中日關系和時代審美趣味嬗變的影響,新時期以來的抗戰電影在創作理念、主題意蘊、美學形態、傳播訴求等方面,都出現了明顯變化。可以說,近36年來的抗戰電影不僅呈現了繁復的歷史況味,也映射了諸多耐人尋味的現實問題。
1.臺海局勢與“國軍抗戰”
抗戰電影在這一時期最顯著的變化,就是表現“國軍抗戰”的作品從無到有、逐步增多。
臺灣問題事關祖國統一大業,也與改革開放所需要的穩定局面休戚相關。自1979年以來,隨著大陸“對臺政策”的調整,先是在20世紀80年代出現了《血戰臺兒莊》等幾部作品;隨后在進入2000年以后,為應對“臺獨勢力”的聒噪,提升國民黨在臺灣的影響力,陸續推出了《喋血孤城》《我的團長我的團》等大批表現國軍抗戰的影視劇。這些作品還原了歷史真相,撥正了長期被誤導的某些歷史觀念。
2.中日關系與“以史鑒今”
抗戰電影與中日關系的起伏密切相關。20世紀80年代雙方因經濟上的彼此需要而進入了“蜜月期”,隨即出現了《一盤沒有下完的棋》等一批旨在教睦中日關系的作品;20世紀90年代雙方因政治隔閡、經濟差異而開始疏遠,于是出現了一批旨在牢記歷史、弘揚愛國主義的“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片,如《七七事變》《國歌》等;2000年以來,因“釣魚島”等問題,中日關系持續交惡,因此揭露日寇侵華暴行的影片開始大批面世,如《棲霞寺1937》等。
顯然,抗戰電影從來就不只是對歷史的緬懷與反思,實際上它同時也是現實政治與國際關系的風向標、睛雨表。
3.多元探索與“藝術成就”
縱觀整個中國抗戰電影史,近36年來無疑是創作視野最開闊、藝術成就最突出的一個時期。
從題材上看,對國共兩黨抗戰功勛的表現已趨均衡;對草莽英雄、國際友人、少數民族、民間苦難,乃至附逆分子亦均有涉及,如:《關東大俠》《柯棣華大夫》《騎士的榮譽》《一九四二》《末代皇后》等;從藝術追求看,既有贏得國際大獎的《紅高梁》、探索影像美學的《一個和八個》,也有吟詠俠骨柔情的《歸心似箭》、調侃抗戰時事的《三毛從軍記》,還有執著于探討人道主義的《晚鐘》、致力于思忖圍殤根源的《鬼子來了》……真可謂既有“高原”也有“高峰”!
當然,大江東去亦難免泥沙俱下。近年來也出現了諸如《追擊阿多丸》《一起打鬼子》等一批以“消費抗戰”為能事的低劣之作,這些影視劇拿“民族創痛”當作牟利工具,已經受到主流輿論的強烈譴責。
在中國電影史上,抗戰電影無疑是其中頗為重要的一個序列,其創作之繁盛足堪欣慰。但我們也應看到,其中真正能躋身“經典”之列者可謂鳳毛麟角,論國際影響力更是微乎其微。這不僅與我國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地位極不相稱,也嚴重制約著我國“國際形象”的塑造和“軟實力”的輸出。從這個意義上說,抗戰電影創作仍可謂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