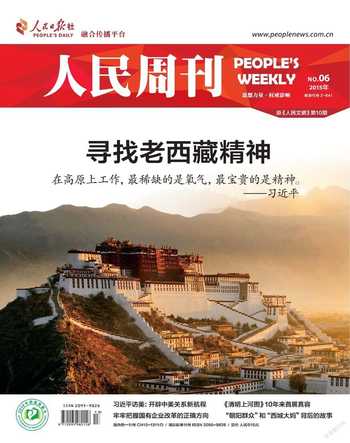十八軍進藏:王貴的歌聲與皮帶
屈一平

1950年5月,西藏昌都,清晨。19歲的十八軍偵查參謀王貴,和戰士們趕往修機場的路上,剛才炊事班老陳特意多盛了一勺代食粉給他,摻和野菜的糊糊在肚子里咕嚕咕嚕作響,這個瘦小的孩子腳下有點發飄。
“咚”——身后一聲巨響,驚動了他,所有人都停下腳步。一個年輕的戰士頭部血漿濺地,倒在身后的山路上,是從山上摔下來的。“就在我們眼前”,半個世紀后的今天,84歲的王貴回憶這一幕,眼淚默默流下來,訴說沒有停止,那是一個軍炮營的戰士,在解放西藏的昌都戰役后,后方供給沒有到位的艱難歲月,為給負載重炮的騾子割草,自己餓著肚子,眼前一黑,從山崖上跌下來。
接受《人民周刊》采訪當天,王貴坐在自己家中回憶往事。茶幾上放著隨軍用品,古舊的“指北針”閃爍著60年的光陰。大多數時候,他認真講述,那些記者聽來唏噓不已的艱難往事,他講來會笑出聲,他執意要送一本當年進藏的歌曲集給記者。“鐵腿班,鐵腿班……這歌,來勁呀,一唱歌,勁頭就來了。出發之前就唱‘不怕那米袋沉……堅定我們信念,鼓起我們的勇氣’。”
19歲的王貴,在進藏部隊里同時兼領唱員的工作,甘孜度糧荒、負重徒步行軍8000里,20座雪山,“歌聲要嘹亮,士氣要高昂”。他現在還唱,北京的建藏援藏工作者協會,每年藏歷年春節等節日,會聚在他家唱這些歌。“也許,50周年慶祝日也會來吧,”他猜測著。桌上的皮帶,是翻越雪山、勒緊褲腰帶的見證,最里面的扣兒被拉開很長一段。他撫摸這些過往,最終沒等來和他一起唱歌的“同志”。
騾子踢破藏民家瓦罐,要賠錢
1950年進入十八軍的王貴,對十八軍的“老西藏精神”認識有一個過程。
回想1950年所在部隊被合并人十八軍偵查科,開赴西藏,源于“進西藏光榮,服從了黨和組織的安排”的理念。而現在,他會告訴年輕的援藏干部:十八軍的“老西藏精神”,一以貫之。十八軍前身是豫皖蘇軍區(1946年冬成立),軍長張國華帶領軍隊,以—萬多人對付敵人十萬人,戰斗最頻繁的時候,是天天打,每天一仗。“獨立作戰能力特別強,特別能吃苦”的十八軍精神,在挺近大別山戰役,豫皖蘇軍區起了很大接應作用。
王貴堅信,“老西藏精神”不僅僅在于特別能戰斗的獨立作戰能力,在進入西藏前面臨選擇時,“特別能奉獻”的精神在當時也初見端倪。“這時候,我們十八軍上下正為駐守川南做準備。多年征戰后大家終于可以享受勝利成果,很多干部都準備結婚、安家。軍政委譚冠三也被調任自貢市市委書記。”1950年1月2日之前的十八軍戰士面前,是一條享受成果的康莊大道。誰也沒想到,此時十八軍領導突然接到劉伯承、鄧小平、賀龍三人聯名簽署的特急電報:速來重慶受領新任務。
“哎呦,王老五,今年已過25,衣服破了沒人補……”對西藏高原荒涼的抵觸、對個人問題的擔憂,十八軍官兵的思想轉化,成了進藏的大問題。出身知識分子家庭的王貴,第一次在十八軍動員進藏的憶苦大會上,聽到從未聽說的舊社會農奴受壓迫的故事。
1950年2月3日,王貴所在的由王其梅副政委、李覺參謀長率領的進藏先遣部隊出發了。張國華把他們送出去很遠,再次提醒部隊要堅決執行毛主席“進軍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
很難憑借過往經驗,來判斷十八軍進入甘孜度糧荒,修機場的那一個月時光。“菩薩兵”——藏胞給十八軍的美譽背后,到底發生了什么?
藏康地區地廣人稀,生產落后,沒多少糧食可以銷售,如果十八軍大量購糧,勢必引起糧價飛漲,部隊命令,不許在當地購糧。在后方糧食無法運來的情況下,3000多人面臨斷糧的威脅。偵查科和北路先遣部隊一樣,一再減少定量。由每天一斤代食粉減少到每天不足四兩,早上多吃點摻和著藿麻頭(對皮膚有毒、煮后可食野菜)、灰灰菜等粉糊,完成修機場的任務下午少吃點,保證睡覺任務。就這樣也不購買當地一兩糧食。
一天,154團戰士彭菊生在路邊拾到一袋糌粑,足夠一個班吃一天的糧食!彭菊生還是忍著饑餓,將糌粑原封不動歸還給藏民。吳忠師長提倡部隊開展“滿缸運動”,就是借住藏胞民房的戰士,要主動給房東挑水,保障水缸常滿。“我都不知道挑了多少缸。”王貴自豪地說,從藏胞家離開當天,部隊都要清理—下,士兵的騾子踢破了藏民的瓦罐,要賠錢。
甚至,他們使用藏民的柴草也要付錢,是白花花的大洋,這也是當年財政部長陳云的指示,不用人民幣,給藏民大洋購買物品。開始哆哆嗦嗦害怕的藏民同胞,大膽地開價:60斤一元,他們中很多人第一次知道,稻草還是可以賣錢的。
特別感動藏胞的是免費醫療,衛生員編了順口溜:“頭疼發燒,阿司匹林三包,看了幾個都好了。”老百姓都感動,藏胞歌唱解放軍的歌就唱起來了’以后都歡迎戰士們。
士兵半饑餓,阿沛享小灶
在人跡罕至的亙古荒原、高寒凍土地帶,十八軍將士硬是用最原始的工具,打通昆侖山、唐古拉、二郎山、雀兒山、達瑪拉、色霽拉等10多座高山,跨越了金沙江、瀾滄江、怒江等天險急流,征服了冰川、沼澤、密林、泥石流等無數障礙。
在昌都戰役中,王貴所在的十八軍穿越了近百公里荒無人煙的巴塘草原,翻雪山,涉冰河,頂風冒雪,奔襲千余里。作為先遣部隊的偵查科,往往是最先嘗試“各種苦果”的。
1950年6月去德格,雀兒山5300米,爬了一天,6個多小時,當時還穿著1949年進軍川西南時發的棉衣。6月登山,“一年的汗水一天灑”,經過一冬一春進軍西南和甘孜長途跋涉,再加上打柴、割草、擔水、修機場等繁重勞動,早已磨破,補衣服就用了一天。
“特別能忍耐”——在十八軍面對俘虜的考驗中,王貴深刻感受到。按照寬待俘虜的指示,十八軍對藏軍士兵和下級官員發放大洋予以遣返,對有家屬者還發一匹馬并多發幾枚大洋,這些都感動著藏軍官兵。
王貴回憶,十八軍請當時昌都總督阿沛·阿旺晉美與隨行官員等仍住在原總管府小樓,而王其梅副政委同志等通知暫時在院內搭帳篷住下’這時我軍嚴重缺糧,指戰員每天每人糧食定量減少至6兩代食粉,在這種饑餓困苦條件下,阿沛小灶待遇。阿沛親眼看到部隊在半饑餓狀態,天天伐木、蓋房子,深受感動。而王其梅多次與阿沛推心置腹交談,絲毫沒以敗軍被俘人員對待,還給他找回丟失的心愛金鞍銀鐙。在事實面前,阿沛承認“西藏方面軍政腐敗無能,解決西藏趨勢不可阻擋”。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自覺遵守政策紀律,自力更生艱苦創業”是王貴在2013年寫下的對“老西藏精神”的回憶和總結。對今天的援藏干部,王貴說,新時代援藏從現在來說,不容易。“那時候我們是集體孔繁森”,王貴每天雷打不動的一件事情,是每天19:30收看西藏衛視新聞,桌上的皮帶,陳舊著孤寂,60年的光景,猶如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