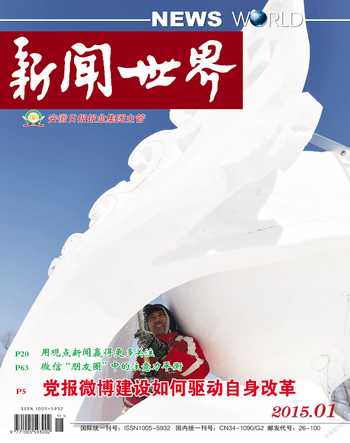試析我國獨立紀錄片對公共領域的建構
呂丹
【摘要】隨著現代化、全球化以及網絡化的發展,我國的公民社會開始出現,我國的公共領域在某種程度上也開始了實質性的建構。而我國獨立紀錄片作為一種獨特的影像方式,以獨立的精神姿態介入到公共/社會話題之中,開掘出了新的公共活動空間和話語空間,影響著公眾的社會認知和自我身份認知。獨立紀錄片的這些特質都極大地促進了我國公共領域的建構。
【關鍵詞】獨立紀錄片公共領域社會建構
隨著現代化、全球化、網絡化的發展,我國的公民社會開始出現,公眾或者說底層的聲音開始要求被聽見,他們對轉型期所涌現出的各種問題和矛盾開始有了強烈的表達意愿,且要求捍衛自身的權利或是價值追求。我國的公共領域在某種程度上開始了實質性的建構。而在當下,我國獨立紀錄片中所呈現的現實圖景、情感體驗與精神樣態,往往顛覆了公眾對現實生活的認知以及想象,讓公眾開始看到、思考和討論之前(或是當下)一直被遮蔽的社會現實和問題,開始了除主流“灌輸”之外的獨立的批判性思考。這時,獨立紀錄片就不再只是一種藝術,而是生命力強大的社會力量,是一種構建社會公共領域的社會工具。
1990年,吳文光拍攝了《流浪北京》,這部片子通常被認作是中國獨立紀錄片的開端。影片主要講述了五位年輕人到北京尋找自由和夢想的故事。片子真實記錄了這五位北漂藝術家在物質嚴重匱乏的現實生活和藝術理想之間不斷糾結、掙扎,又一次次重新自我建構與確認的情感與精神體驗;段錦川拍攝的《八廓南街16號》(1996年),聚焦一個中國最小權力機構——西藏拉薩市八廓南街居委會的日常權利運作狀況,有評論說“當你看完這部片子后,也許你已經忘記了你的浪漫期待,取而代之的是你對另一種東西的理解,那就是政治,以及政治與人的關系。”①。可以說,中國獨立紀錄片以一種體制外的獨立精神打破了中國傳統專題片的創作模式,把鏡頭對準被主流意識形態所忽視或遮蔽了的社會問題和底層人物身上,記錄下這群人在當下社會中的生存境遇、精神體驗或訴求,體現出了對社會的嚴肅思考和對個體生命價值的尊重,帶有深刻的社會責任感和獨立批判意識。
一、開掘出新的公共空間
1、開掘新的公共活動空間
獨立電影人時間于1991年6月組織成立了“結構·青年·電影小組”,即SWYC小組,并于該年12月舉辦了“北京新紀錄片作品研討會”。這是一個具有影響力的開端。而從90年代中期開始,一些城市的民間影像社團也紛紛興起。影響較大的有上海的“101工作室”(1996)、廣州“緣影會”(1998)、成立于2000年的北京“實踐社”、南京的“后窗看電影”、沈陽的“自由電影”、重慶M公社、賈樟柯的“青年電影實驗小組”等等。許多中小城市也逐漸自發成立了類似的組織。起初,活動主要是為了一起觀摩、探討那些前衛、經典的外國影像作品,后來是一些在國內院線或電視臺無法播出的紀錄片。隨著這些社團的影響力的增強,其活動范圍也不僅限于觀影。2001年9月,北京“實踐社”開始嘗試聯合其它城市的影像社團,和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共同舉辦了“第一屆中國獨立影像節”,影展的關鍵詞為“民間·獨立”。隨后,影像放映及作者交流活動開始風行。場地也由隱蔽的私人空間、酒吧開始擴展到一些更正式、更大的空間,例如書店、高校、圖書館等。各個城市的藝術倉庫或美術館也開始開設展廳放映獨立影像作品。“這些影像團體組織各種活動,倡導影像創作,組織巡回演講,開展網上討論,出版內部刊物……這些影像社團通過活動與文化的連接,營造出一種小型的公共空間,成員在其中相互觀摩、彼此切磋,針貶現實,各抒己見。”②由此,新的公共活動空間開始出現,雖然“領地”不大,但影響力卻不容忽視。
2、開掘新的公共話語空間
《老頭》的拍攝者楊天乙并未受過任何專業訓練,只是看到一群每天聚集在小區墻根下的老年人后,對生命有了些許感悟,并將其用影像的方式記錄下來。這部片子樸實真摯,觸碰到了生命的某些真實,獲得了社會的認可。楊天乙通過獨立影像完成了跟自己、跟社會的交流與對話。
獨立紀錄片導演艾曉明曾經用寫作的方式表達自己對社會問題的關注和思考,但后來改用紀錄片的方式。她說:“比如說太石村事件,你可以透過許多文字資料、新聞報道去了解事件成因,但重要的還有看見,看見村民的形象、他們的情感狀態,直接面對人的喜怒哀樂,我們的感情受到激發,這促使我們去理解這些事情背后人們的內心、動機,理解他們的經歷和感受……如果缺乏視覺表達和記憶,我們對歷史、社會的認識會流于概念化,因此也很容易忘記,缺乏感情的沖擊,缺乏對痛苦的感同身受,我們的價值觀也很容易被其他概念所取代,不會特別珍惜一些價值。”③艾曉明用獨立影像的方式將被拍攝者和自己的思考“帶到”了公眾面前。值得注意的是,她同時還將自己的觀點傳達給被拍攝者,這既是對他們的聲援,也將公民權利、平等、正義等概念直接傳達給了被拍攝者(往往是底層民眾),完成了更大范圍的、雙向的對話。
“公民或者民間要參與公共事務,國家不能觸及,首先得把握一個自己的話語權和公共話語空間的建立,由對話(話語)的雙方或者多方達成一致。”④無疑,獨立紀錄片給了公眾以新的話語方式和更廣大的自由的交流空間或渠道,無形中挖掘出一塊新的公共空間。
二、以獨立之精神介入社會議題
獨立紀錄片通常關注被主流話語所遮蔽和漠視的生存空間,“如中國改革進程中的城鎮和城市,農村,工廠,煤礦,發廊等,處在這個空間中心的則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弱勢群體和邊緣群體,如老人,殘疾人,民工,三陪小姐,下崗工人和流浪漢,而正是透過他們,我們得以窺見一部分關于這時代的真相。”⑤其實,諸多的社會問題往往就是底層問題,獨立紀錄片正是直面這些問題或是癥結,揭示它,“觀看”它,獨立地思考它。
徐辛的《克拉瑪依》用六個小時的時間呈現了一個個遇難學生的家庭對那場大火的回憶,和大火后面臨的種種苦楚與生活窘境。克拉瑪依大火一直是模糊的,而徐辛用手中的攝影機將這段被故意隱去的大火重新拉回人們面前,以此對抗遺忘,對抗某種荒誕扭曲;趙亮對北京南站上訪村的關注持續了十二年之久,他的《上訪》便是記錄訪民上訪的一部片子;艾曉明的《我們的娃娃》是關于汶川地震死難學生名單的調查;范立新的《歸途列車》通過追蹤記錄一對來自四川的農民工夫婦外出打工的艱辛經歷,來展現當下中國高速發展背后的小人物的心酸和不易;陳為軍的《好死不如賴活著》拍攝了河南省上蔡縣文樓村因受賣血致富蠱惑而感染艾滋病、面臨生存與死亡困境的馬深義一家,鏡頭展現了這個不幸家庭最平凡、質樸的生活場景,于無形之中迸發出震撼人心的力量,讓人動容。
另一方面,部分獨立紀錄片已不僅僅停留在“觀看”、“諷喻/隱喻”的層面,而是身體力行地介入到社會事件當中,關注社會大環境,并以平民的身份發出自己的評判。這部分創作者親身參與事件進程并以記錄的姿態開啟了中國獨立紀錄片由純粹的觀看者立場,向參與社會運動、建構公民社會者立場的轉變。艾曉明是這類創作者的代表。她的紀錄片主要是一些敏感題材和有爭議的公共話題,片子態度明確,批判力度尖銳。她拍攝的《太石村》跟蹤紀錄了廣東番禺太石村村民罷免村官的經過,為這個事件提供了一個不同于官方說法的真相。
可以說,獨立紀錄片顛覆了主流話語模式中美化、刪改或刻意回避部分社會現實的價值立場,而是以獨立的精神姿態和社會公民的身份力圖還原現實真相,揭開遮蔽的黑幕,發出自己的聲音。這是創作者們對社會的思考和批判,是對社會責任的勇敢承擔。
三、促進社會認知與身份建構
這是一個網絡化和視覺化的時代,而網絡的發展也加速了視覺影像的發展。影像無處不在,“影像是我們想象社區、城市乃至諾大世界的基礎”。⑥斯圖亞特·霍爾曾指出,現代傳播具有一種首要的文化功能,就是選擇建構“社會知識”和社會影像。公眾通過媒介傳播所建構的這類知識和影像來認知世界,認知自己,來體味他們曾經歷過或正在經歷的現實生活,來確認其自身的存在方式和價值。凱斯·桑斯坦曾說過:“民主要求有兩個要件:一是一定程度的共享經驗;二是能接觸到一些未預期的、事先不經過選擇的多元的話題和想法。”⑦
無疑,獨立紀錄片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這兩個條件的實現。獨立紀錄片這種影像方式是一種深入民眾生活、觀察世界、促進相互(人與人之間、不同社區群體之間、主流與非主流之間)的認識與溝通的社會工具。當人們觀看一個影像故事的時候,就意味著他已經走出了私人領域,在體驗和思考著通常是和社會公共生活、大眾民意相關的現象和問題。他開始知道了不一樣的故事和想法,開始了自己的思考。而這里的“他”可以是任何人。在這個紐帶或者“文化社區”中,話語是開放的、多元的、互補的,人們相互溝通、分享、學習,更新社會認知,進行新的自我身份的塑造,實現自我確認。這時,公眾的社會認知就不再局限于主流或官方意志了,公眾對自我身份的認知也不再是主流告訴他“他是誰”或“他應該是誰”。
結語
我國獨立紀錄片將獨立之精神與公民身份結合,積極介入到話語傳播中,切實踐行了對公共領域的構建。但須注意的一點是,影像畢竟只是一種手段,獨立紀錄片的發展本身也面臨著諸多困境,而真正能讓公共領域發展的是人們的共同意識。只有當綜合文明程度達到一定高度時,公眾能夠真正廣泛地參與各類公共事務的討論,能夠更自由地進行理性批判并且形成公共意見時,我們的公共話語才能更有力量,我們的公共領域才能真正成熟。而這,需要政府、媒體、社會以及大眾的共同努力。□
參考文獻
①朱靖江、梅冰:《中國獨立紀錄片檔案》[M].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9
②韓鴻,《影像社區、公共領域與民主參與——中國大眾影像生產的新走向》[J].《新聞大學》,2005(3):75
③王小魯,《我的紀錄片是媒體——談艾曉明和趙亮的影像實踐》,http://wxiaolu999.blog.163.com/blog/static/1353341 4720108263016705/
④寇燕,《當代中國環境類紀錄片對公共領域構建的影響》[D].重慶大學,2012:19
⑤張亞璇,《無限的影像——1990年代末以來的中國獨立電影狀況》[J].《天涯》,2004(2):156
⑥南帆:《雙重視域——當代電子文化分析》[M].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65
⑦凱斯·桑斯坦:《網絡共和國:網絡社會中的民主問題》[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46.
(作者:重慶大學新聞學院研究生)
責編:姚少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