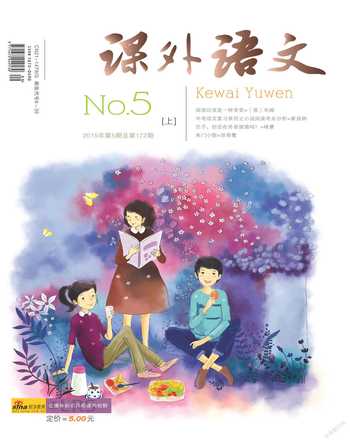不毀滅的背影
沈從文
“其為人也,溫美如玉,外潤而內貞。”
“君子”在這個時代雖稀有難得,也就像是不切現實。唯把這幾句作為佩弦先生身后的題詞,或許比起別的稱贊更恰當具體。佩弦先生人如其文,可敬可愛處即在凡事平易而近人情,拙誠中有嫵媚,外隨和而內耿介,這種人格或性格的混合,在做人方面比做文章還重要。經傳中稱的圣賢,應當是個什么樣子,話很難說。但歷史中所稱許的純粹的君子,佩弦先生為人實已十分相近。
我認識佩弦先生和許多朋友一樣,從讀他的作品而起。先是讀他的抒情長詩《毀滅》,其次讀敘事散文《背影》。在詩歌散文方面,得把他的作品和俞平伯先生的成就并提。作為比較討論,使我明白代表“五四”初期兩個北方作家:平伯先生如代表才華,佩弦先生實代表至性。記得《毀滅》在《小說月報》發表時,一般讀者反映,都覺得是新詩空前的力作,文學研究會同仁也推許備至。唯從現代散文發展看全局,佩弦先生的敘事散文,能守住文學革命原則,文字明朗、樸素、親切,且能把握住當時社會問題的一面,貢獻特別大,影響特別深。在文學運動理論上,近二十年來有不斷的修訂,語不離宗,“普及”和“通俗”目標實屬問題核心,真能理解問題重要性,又能把握題旨,從作品上加以試驗、證實,且得到有持久性成就的,少數作家中,佩弦先生的工作,可算得出類拔萃。求通俗與普及,國語文學文字理想的標準是經濟、準確和明朗,佩弦先生都若在不甚費力情形中運用自如,而得到極佳成果。一個偉大作家最基本的表現力,是用那個經濟、準確、明朗文字敘事。這也就恰是近三十年有創造欲,新作家待培養、待注意、又照例疏忽的一點。正如作家的為人,偉大本與樸素不可分。一個作家的偉大處,“常人品性”比“英雄氣質”實更重要。但是在一般人習慣前,卻常常只注意到那個英雄氣質而忽略了近乎人情的厚重質實品性。提到這一點時,更讓我們想起“佩弦先生的死去,不僅在文學方面損失重大,在文學教育方面損失更為重大”(馮友蘭語),因為馮先生明白“教育”與“文運”同樣實離不開“人”,必以人為本。文運的開辟荒蕪,少不了一二沖鋒陷陣的斗士,扶育生長,即必需一大群有耐心和韌性的人來從事。文學教育則更需要能持久以恒、兼容并包的人主持。佩弦先生偉大得平凡,從教育看遠景,是唯有這種平凡做成一道新舊的橋梁,才能影響深遠的。
一個寫小說的人,對人特別看重性格。外表輪廓線條與人不同處何在,并不重要。最可貴的是品性的本質與心智的愛惡取舍方式。我覺得佩弦先生性格最特別處,是拙誠中的嫵媚。他對事、對人、對文章,都有他自己的意見,凡事和而不同,然而差別可能極小。他也有些小小弱點,即調和折中性,用到文學方面時,比如說用到鑒賞批評方面,便永遠具教學上的見解,少獨具肯定性。用到古典研究方面,便缺少專斷議論,無創見創獲。即用到文學寫作,作風亦不免容易凝固于一定的風格上,三十年少變化,少新意。但這一切又似乎和他三十年主持文學教育有關。在清華、聯大“委員制”習慣下任事太久,對所主持的一部門事務,必調和折中方能進行,因之對個人工作為損失,對公家貢獻就更多。熟人記憶中如尚記得聯大時代常有人因同開一課,各不相下,僵持如擺擂臺,就必然會覺得佩弦先生的折中無我處,如何難能可貴!又良好教師和文學批評家,有個根本不同點:批評家不妨處處有我,良好教師卻要客觀,要承認價值上的相對性、多元性。陳寅恪、劉叔雅先生的專門研究和最新創作上的試驗成就,佩弦先生都同樣尊重,而又出于衷心。一個大學國文系主任,這種認識很顯然是能將新舊連接,文化活用,引導所主持一部門工作到一個更新發展趨勢上的。中國各大學的國文系,若還需要辦下去,佩弦先生的這點精神,這點認識,實值得特別注意,且值得當成一個永久向前的方針。
(選自《不毀滅的背影》,有刪節)
注:佩弦先生即朱自清,中國現代作家。
【閱讀訓練】
1.文章主要從哪兩方面介紹了朱自清先生的成就?請結合文章的內容加以具體說明。
2.作者對朱自清先生的“小小弱點”作了怎樣的評價?這樣寫有什么好處?
3.文末說“佩弦先生的這點精神,這點認識,實值得特別注意”,“這點精神”“這點認識”分別指什么?
4.作者在文中說“一個作家的偉大處,‘常人品性’比‘英雄氣質’實更重要”,你認同這種觀點嗎?說說你的看法。
(王云卿 設計)
(參考答案見3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