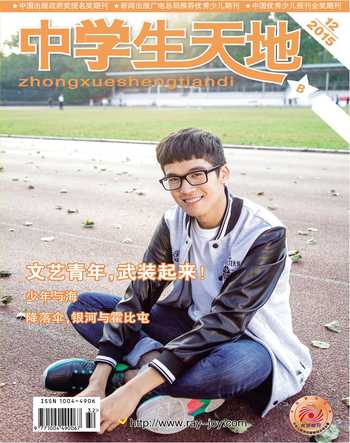反建筑
何真
早些年,我因為工作的關系在北京采訪了“鳥巢”的中方總設計師李興鋼。當時他正處于個人形象備受關注,具體事務飽經煎熬的矛盾旋渦中。一方面,“鳥巢”驚世駭俗的造型使他名聲大噪;另一方面,工期拖延、造價縮減等問題又令他頭疼不已。我提出要找一個能代表“鳥巢”的背景為他拍照時,找來找去,他說工地太亂了還是在沙盤前面吧。此時,模型上的“鳥巢”已看不到一絲光鮮靚麗,北京的沙塵灌入設計室,給它遮上了一層灰黑。
其實,李興鋼承載的關于“鳥巢”的榮譽或爭議,更多的是民眾情緒的投射,大家需要一個中國人的形象來代表“偉大的鳥巢”設計師。瑞士赫爾佐格和德梅隆設計事務所,才是這個“絕妙造型”的點子的真正主人。在諸多競標方案的最后投票環節,“鳥巢”方案可以說是以壓倒性的票數中標。
“鳥巢”為什么能中標呢?以另一套較低調方案參標的北京市建筑設計研究院設計師王兵,事后曾經這樣分析:選擇“鳥巢”方案是當時的“大氣候”決定的。當時我國經濟發展很快,奧運申辦成功讓全國人民歡欣鼓舞,無論政府官員、專家學者還是老百姓,多少都有種“全球矚目”的浮躁情緒。
實際上,彼時的北京已經成為全球建筑設計師的試驗田。除了“鳥巢”,還有“水立方”(國家游泳中心)、“大褲衩”(中央電視臺新樓)……無一不因標新立異的造型、與周遭環境的違和感而受到一定程度的非議。
據說在那幾年,投標中似乎有種不成文的規則,即沒有國外設計單位參與的方案很難中標。因為我們求大崇洋,所以外國設計師就投其所好,很多設計方案固然在安全方面經得起考驗,但感覺在是向自然挑戰,比如中央電視臺新樓,這么高的高度,還要傾斜的造型,帶來的是巨大的資金投入和視覺沖擊。
并不是每一個“外來和尚”都在北京受到追捧。還是拿“大褲衩”來說,我見到過當時日本設計師提交的競標方案。他們主張,中國的國家電視臺不應修建頂天立地的巨型高樓,相反,應該用平面化、躺在地上而錯落有致的低矮建筑群落取而代之。該方案的設計者認為,媒體要避免給市民高高在上的形象,相對于權威感,電視臺的建筑更應體現貼近和親和感,而且,群落式的結構、低矮的姿態,更容易融入北京古城。不過,日本人的觀點最終未能獲得采納。
正因為有了這一點點對日本設計師的認識,伊東豐雄的《反建筑》最近擺上了我的書桌。這并不是一本設計師大講設計思路的理論作品,更不是某個建筑的建造說明書,而是伊東豐雄參與“3·11東日本大地震”重建工作的一些心得體會,以訪談的形式集結出版。
2011年3月11日,東日本地區發生里氏9.0級的地震災害,地震引發海嘯,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還導致福島第一核電站1~4號機組發生核泄漏事故。伊東豐雄作為建筑設計師,義不容辭地投入震后重建工作,他前往距離震中最近、受災最嚴重的仙臺市,為數以萬計離家避難的人群設計居住空間。
伊東豐雄是新銳的當代建筑師,用材大膽,風格鮮明。他的成名作“風之塔”,是日本國鐵橫濱線的北幸地下街通風口,光聽名字就很有霓虹國動漫風。伊東豐雄將通風口設計成透明圓柱狀,夜間照明會依據噪音、風速等數據變化,相當有巧思。“仙臺媒體中心”是伊東豐雄另一個著名作品,有興趣的同學可以找圖片看看,我覺得它就像小孩子搭的積木,僅僅由6塊“板”和13根形狀像搖晃海草的“管柱”,支持起了地下2層、地上7層所有的空間。媒體中心就像一個大公園,人們可以在里面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看書,上網,吃東西,交流……它的外立墻壁全是玻璃,音樂節和祭典時,可打開來進行藝術活動,感覺相當奇幻。
值得一提的是,看似玩具的仙臺媒體中心在3月11日那天巋然不倒,經受住了地震的考驗。如果沒有對建筑發自內心的愛,是無法創造出這種高水準的作品的。大地震引發了伊東豐雄對人類自以為是的生存狀態的思考。脆弱的河岸本來不適合建造高層建筑,好辦,把建筑修得更牢固就好了嘛。人類正是帶著這種盲目的樂觀,開始了修筑居所、改造世界的現代旅程。然而當真正的災難來臨的時候,無論多么牢固的建筑,都不堪一擊。
那么,人類應該抱著怎樣的態度來建造呢?伊東豐雄的解答是,居所是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產物,以互不侵害、互惠互利為前提。套用一個經濟學術語,就是“共贏”。岸邊不適合起高樓,那把它修剪成大片的草地就好;山上有千年古樹,建筑何妨以枝為梁、以葉為瓦,引山泉做生活用水呢?隨著人類科學技術水平的不斷進步,樹林里也不難創造出現代化的生活空間。
有的同學可能要說,這樣的房子,造價可能非常昂貴,可居住的人數又那么有限,多不經濟啊。伊東豐雄的“反建筑”,正是要反對這種大部分人認為理所當然,以經濟和效率優先、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的建造方式。“20世紀的建筑是作為獨立的機能體存在的,就像一部機器,它幾乎與自然脫離,獨立發揮著功能,而不考慮與周圍環境的協調;但到了21世紀,人、建筑都需要與自然環境建立一種連續性,不僅是節能的,還是生態的、能與社會相協調的。”
了解了伊東豐雄對于居所的想法,就可以理解他以往那些“出格”作品的設計思路。“風之塔”是對自然環境產生的噪音,因勢利導改造成音樂;“仙臺媒體中心”是用玻璃材質,將本來就不必隱藏的室內活動,大白于天下。
聯想到國內某些房地產開發商的作派,競得地王之后,大有戰天斗地、愚公移山的勇氣。沒有山頭推不倒,沒有溝渠填不平。氣魄固然可嘉,也的確解決了人多地少的種種難題,創造了所謂的現代化。可惜留給后人的,往往是經不起時間考驗,再生能力幾乎為零的建筑體。直到今天,每當我路過“鳥巢”,看那一處繁華和周邊落寞,總覺得這位降臨人間的“鋼鐵巨人”與北京格格不入,他自己也因為孤獨,早已失去了往昔的榮光和活力。
日本設計師注重人與環境的互動,是有其社會基礎的。像我們很多中國人一生中至少會“買”一次房子一樣,不少日本人一輩子會“造”一次房子。在日本時常能看見掛著售賣標記的小片空地,那是在等待新主人用大半生的積蓄,來這里搭建人生的歸宿。對于許多日本人而言,建筑房屋是籌備幾十年,最后親自規劃,再找人實施的人生大事。有規劃的自由,才有規劃的能力,規劃的格局。
有意思的是,一直以來以“擅長創造人居和諧環境”著稱于世的日本建筑設計師們,今年被日本政府重重打臉。事情緣起于2020年東京奧運會主場館的招標,伊拉克裔英國女建筑師扎哈·哈迪德擊敗眾多日本同行,成功中標。這本來也沒什么,但問題在于扎哈是設計師中有名的“燒錢女魔頭”,其設計方案比“鳥巢”的造價還高得多。自然,以伊東豐雄等人為首的本土設計師們對扎哈展開大規模的口誅筆伐,著實上演了一出“反建筑”的大戲,最終迫使日本政府單方面毀約,以較低的價格重新招標。
看來,只要人類依然擁有征服自然的野心,各種奢侈的建筑還會不斷出現,“反建筑”的爭議也不會終止。我們不乏動力,但也要懂得敬畏,或許這樣,前路才會更加坦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