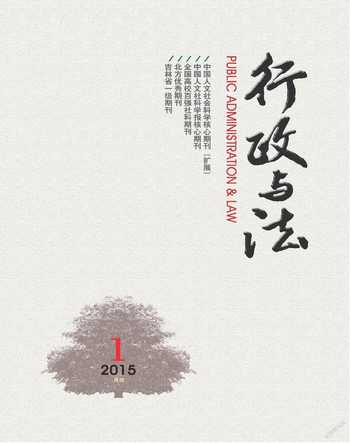論“知假買假”行為的反契約性及其克服
摘 ? ? ?要:對法律實踐中存在的“知假買假”現象,我國長期以來一直處于懲罰性賠償對其是否適用,包括是否賦予“知假買假”者以消費者地位,其打假行為是否具有價值正當性的爭論之中。但是,忽視這種行為的反契約性及其折射出的社會風險,必然怠于反思正當的規制路徑。本文認為,應當以剖析假冒偽劣產品存續的時空條件為基礎,確定政府、“知假買假”者和消費者在制假售假社會防治網絡中的合理地位,以實現社會風險防控和契約精神捍衛的共同目標。
關 ?鍵 ?詞:契約;知假買假;社會風險;協同治理;反契約性
中圖分類號:D923.8 ? ? ? ?文獻標識碼:A ? ? ? ?文章編號:1007-8207(2015)01-0104-08
收稿日期:2014-08-12
作者簡介:肖峰(1983—),男,四川南溪人,湘潭大學法學院講師,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環境法和國際經濟法。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我國農業貿易生態化轉型的法律保障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2BFX143。
我國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下簡稱《消法》)等立法中①規定了懲罰性賠償制度,有力地保護了消費者購買商品和接受服務時的法律權益,但也為知假買假者利用法律規范獲取非消費利益提供了法律空間。自從1998年“王海現象”以來,“知假買假”現象引發了理論界和實務界的激烈討論,但就制假售假問題的解決并未提出有效的規制途徑,產品質量缺陷特別是食品安全問題愈發嚴重,因此,應當對“知假買假”現象給予更加深入的解讀。本文的研究旨趣不在于論述懲罰性賠償是否適用問題,而在于剖析“知假買假”現象背后的社會問題,探求讓知假者無需依靠買假來治假的合理規制路徑。
一、“知假買假”行為的法律解讀與問題提出
顧名思義,“知假買假”就是明知購買對象的質量狀況而加以購買的行為,知假在先、購買在后。目的通常有兩個:一是滿足自身消費需要,如低價購買盜版軟件或仿冒名牌服裝等;二是以懲罰制假售假或牟利為動機,利用《消法》等規范中的懲罰性賠償獲得超過原價數倍的非消費收益。主觀上明知未必會購買,不過一旦實施了購買行為,則會產生消費契約關系上的權利和義務,契約制度所欲實現的法律效果與知假者購買動機之間的錯位是解讀“知假買假”的核心。
“知假買假”以消費合同上的債權作為制度工具,作為一種法律行為,合同具有法定成立要件和生效要件。[1]該種購買行為在形式上具備合同法律關系成立的因素,但該行為的效力瑕疵也顯而易見。在知假條件下做出購買的意思表示能否產生法律效力,雙方意思表示的一致是否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是存疑的。從法律行為的要件構成上分析,合同標的物的虛假情況買賣雙方明確知曉,二者的意思表示也確是購買具有瑕疵商品或服務,雙方均無意思表示障礙且行為意思和目的意思一致。問題在于:交易標的物是有違法律規定的,要么屬于違反國家強制性技術標準的產品(如劣質電工產品、受污染食品等),要么屬于侵權行為結果(如冒牌馳名商標產品等),合同雙方意思表示一致恰是雙方共同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違反公序良俗原則,是典型的無效民事行為。筆者認為:不管是尋求低價劣質的自身消費品還是以非消費性收益獲取為目的,“知假買假”都是濫用合同權利,因而有害于契約精神的行為,在行為性質上應當歸于無效合同,依法雙方應當返還各自所得或者由國家沒收。但這在立法精神上明顯與懲罰性賠償不符,它是違反有效合同而承擔違約責任的一種形式,并以根本性違約為前提 ,“知假買假”行為絕無適用之余地,由于認定買受人“知假”主觀狀態很難,加之社會的打假心切,因而造成了懲罰性賠償的混用。
探討判斷買方消費意圖的標準及其消費者地位,已在我國理論實務界爭議多年,值得深思的是為什么消費契約關系會淪為“知假買假”者打假的法律工具,答案要在假冒偽劣產品存續時空規律中去尋找。這些產品形成后便成為消費者利益的可能危害源,客觀上完全具備侵害消費者的形態,但未被購買則不是合同之標的物,只能被認為是相對于人體健康損害而言的前置性社會風險,經營者也就無須對此擔負懲罰性賠償的責任。防控該種風險轉化為實際損害后果,須明確風險防控主體,即經營者就風險向誰負有法律義務?如能通過法律制度而讓假冒偽劣產品在風險階段即受到否定,則消費者權益保護機制就相當完善。由是觀之,“知假買假”行為折射出的不是真實消費者權益受損后缺乏保護的問題,而是缺乏將制假售假防范于風險階段的制度設計,只能待其轉化為損害后果后才予以法律規制,這才是契約精神被踐踏的深層次原因。
通過解讀“知假買假”現象的法律屬性及效力,筆者不禁要問:知假買假者所要實現的價值目標是否具有社會正當性,如何協調其與契約精神維護的關系;假冒偽劣產品的風險防控義務主體是誰,它與打假者、消費者間處于什么關系之中。這需要法律作出全面解答,對懲罰性賠償適用于“知假買假”行為上尚存爭議,這說明我國相關立法對此問題缺乏合理的規制途徑。
二、懲罰性賠償對“知假買假”可適用性爭議之評析
因自身消費而“知假買假”,其后主張賠償的情形不是典型形態。而以獲得懲罰性賠償為目的的“知假買假”行為,確是學界和實務界廣為爭論的問題,并圍繞知假買假者的消費者地位、消費意圖發覺、社會效應等方面產生了嚴重分歧。
(一)“知假買假”人的消費者身份之爭
從“王海現象”出現開始,知假買假者是否屬于法律上的消費者、其大量購入假冒偽劣產品是否基于滿足消費需要為動機的爭論不絕于耳,司法實踐中對相關案件的處理各地法院做法也不同。[2]一方面,否認“知假買假”者消費者身份的代表性觀點認為,“民法解釋學上有一項重要原則:無論采用何種解釋方法, 其解釋結果都不得違背法律條文可能的文義。毫無疑問,‘買假索賠’超出了‘生活消費的需要’這一用語可能的文義范圍, 因此應肯定‘買假索賠’案不在《消法》第49條的適用范圍之內。”[3]因為《消法》保護的是為消費需要而購買商品和服務的自然人,客觀上以一般經驗所指示的消費量和消費種類為依據,購買超過一般經驗認為的合理數量假冒偽劣產品肯定不屬于供消費之需,因而不是《消法》上保護的消費者。另一方面,許多學者從法律解釋學和保護消費者弱勢地位的角度肯定“知假買假”者的消費者地位。目前這一派觀點占據上風,其中又分為完全承認和有限承認兩種類型:第一,完全承認的觀點認為,“在人性的假設上,法律并不禁止個人基于‘利己心’而采取的投機主義行為,消費者從來就不是以一個‘利他主義者’形象被設計的”。[4]“無論是什么樣的人, 無論是知假也好,不知假也好,凡是確認所購買的產品是假冒偽劣產品,所提供的服務是欺詐性服務,就應當適用《消法》第49條,就應當適用懲罰性賠償金制度,給予受害人以雙倍賠償”。[5]這是強調懲罰性賠償的形式正義,但凡與經營者交易并買到假冒偽劣者均認定為“消費者”。第二,有限承認的觀點又分為排除認定和推定認定兩種類型,前者認為,“在市場中,所謂消費者是指非以盈利為目的的購買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人”,[6]“任何人只要其購買商品和接受服務不是為了將商品或者服務再次轉手,不是為了專門從事商品交易活動,他(她)便是消費者”。[7]認為“知假買假”者符合《消法》的立法目的,即是將買受人分為自行消費與轉手盈利兩種,排除盈利目的則可認定為消費者。后者認為,“由于舉證困難,購買商品不是用于生產經營,應該推定用于消費”,[8]因為如果經營者證明買受人是以“知假買假”為盈利手段則合同無效,但“這種舉證責任是擺在持否認知假買假者是消費者觀點的人面前的一個很難逾越的障礙,知假買假者仍然是消費者,而且是打假式的消費者”。[9]
可見,消費者身份的爭點在于:是以經營者為參照,只要與其發生產品交易關系的買受人就是消費者;還是以日常消費需要為依據,對比一般性生活經驗與購買行為來判斷買受人是否具有消費意圖。
(二)“知假買假”行為的制度價值之爭
認可“知假買假”者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贊同其可以對社會建設做貢獻,而法律上是否認可“知假買假”行為的效力,也要在其形成的社會成本與收益孰大孰小的比較中選擇。
否定“知假買假”行為具有價值的觀點認為:“學界普遍認為為牟利而‘知假買假’的行為具有一定社會危害性, 也有違設立懲罰性條款的初衷”。“‘知假買假’的行為在局部上對于抑制偽劣假冒產品的危害有一定的積極作用。然而這種積極作用是以法律的漏洞為基礎、以曲解法律的精神為代價的。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這種行為無疑有巨大的潛在危害。”“假冒產品的經濟價值最終被社會所承認,消費者實際上成為了經營者非法經營的幫兇,這不僅助長了非法經營者的氣焰, 而且也是對法律的嘲弄”。[10]這種看法認為日常消費真實需求的法律權益救濟機制受到了經濟利益的抵牾,是一種道德淪喪的現象,容易引起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誠信危機。
肯定“知假買假”行為的社會正面效應的觀點認為:第一,盡管知假買假者不是典型的消費者,但是對其的保護與真實消費者的保護不可區分,“對知假買假者的法律保護決不僅僅反映了其與經營者之間的單一的利益平衡問題,而是涉及到消費者全體利益的保護問題。對知假買假者的法律保護昭示了懲罰性賠償的制度功能, 從而激勵廣大消費者主動運用該制度維權, 具有良好的社會效果”,[11]有利于發揮法律的引導、預測等方面的功能;第二,其正面效應源于消費者私力救濟和監管權間存在制度“真空”,這給“知假買假”者留下了扮演社會秩序“潤滑劑”角色的空間。“綜合考慮我國目前政府打假能力及公益性程度、假冒偽劣產品的泛濫程度、市場主體誠信行為的比例、消費者受欺詐的嚴重程度等因素以及可能的變化方向及程度,在我國目前賦予知假買假者獲得懲罰性賠償的權利以發揮其打假功能是必要的”;[12]第三,雖然“知假買假”具有一定的負面效應,但兩害相較取其輕,其正面價值大于負面價值,其價值應當得到社會和法律的認可,“即便‘知假買假’,也可‘打假’,因為這種行為對社會并沒有損害,它卻同樣懲罰了知假售假者,而且社會還可從中獲利”。[13]因此,“知假買假的雙倍賠償這種理性的殘缺美是可取的”。[14]
可見,對“知假買假”行為的法律價值之爭在于:該行為是以一種不誠信抑制另一種不誠信的“血態復仇”在現代社會的變種,還是其對當前情勢的利好優位性而認可其積極價值大于消極價值。
(三)爭議評析
從根本上來說,圍繞“知假買假”的爭論是對其制度價值認識的差異,各方是以社會需要為視角確定應給予“知假買假”行為相應的地位,得出懲罰性賠償是否可以適用的判斷,對消費者地位、消費意圖等法律行為構成因子做出狹義或廣義的解釋。應當說,“知假買假”行為在懲罰性賠償條款中的可適用性、適用方法等問題已討論得比較充分,但這種討論都是建立在消費契約關系之上來說明“知假買假”者是否有資格主張懲罰性賠償這種違約責任。似乎消費契約的合法性就不證自明了,鮮于關注實質性社會問題的替代性解決方案。
⒈對懲罰性賠償現有認識遵循以有效消費合同法律關系為基礎、超額賠償部分作為違約責任的思路,制度功能認識紊亂。一方面,違約責任意義上的賠償由有效合同的債權人主張,且遵循誠信原則和促進交易的價值要求。“考慮到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高速發展時期,從鼓勵交易的需要出發,對懲罰性賠償范圍進行適度的限制,即限定在惡意違約或故意違約和幾種特殊的違約情況下才能夠兼顧當前各方面的利益,較好地發揮懲罰性違約損害賠償的積極作用”。[15]但當前對“知假買假”行為的論爭,更注重照顧社會效應與民眾法律情感,忽略了消費契約關系的價值與效力規定性,而“知假買假”行為恰是典型的無效合同。另一方面,之所以脫離契約精神來談“知假買假”,是因為“買假”是客觀事實而“知假”卻是主觀狀態,買假者做出締結合同意思表示時內心真實狀態(即目的意思和效果意思)難以為相對人獲知,只能以其表示行為的一般意義為據,實踐中“知假買假”與普通消費者難以甄別,將它們置于合同法律關系中注定是一個無解的難題。但困境的造成不在于合同法乏力,而在于“知假買假”行為目的本身就不是捍衛契約精神,而是反擊風險行為,本就不為實際消費而是以合同作為抑制制假售假的工具。“知假買假”不在合同法的調整范圍內,合同被濫用為“知假買假”解決社會問題的“面具”,這會破壞質樸的契約精神和交易秩序。筆者認為,“知假買假”法律規制的既有認識存在前提性錯誤,解決之道存乎于私人契約關系之外,似在社會治理框架下考量更為合理。
⒉在契約關系上評判“知假買假”的價值存在悖論,肯定其價值有違誠信原則,否定又有不利于關心整體利益、關心他人福祉的公民精神的養成。非此即彼選擇的原因在于:“知假買假”行為的價值判斷被異化為消費合同效力判斷。從法律價值上看,誠信原則主要在已然建立法律關系意義上指導主體履行權利義務,適用于法律關系建立后,規則內容從法定應然狀態轉化為實然狀態。公民精神則體現為主體關注所在社會團體(國家是典型形態)共同福利,秉承利他主義來參與社會關系,超越既有法律關系而探求要建立哪些法律關系、怎樣建立法律關系等更高層次問題,認識到價值位階差異后二者應當并行不悖。筆者認為,理清“知假買假”內在價值與契約精神關系,必須脫離契約語境的束縛,尋找到更優的替代性制度資源,否則會發生“知假買假”公益目標與契約誠信的抵牾,給借打擊制假售假為名來獲取非消費性利益留下制度真空。如果我們仍對“知假買假”的價值認識與甄別消費領域、消費者復雜構成混為一談,與過度消費、投資性購買消費品(如炒房)等消費合同本身的相關問題相提并論,必然會引發價值的混亂。
⒊對“知假買假”者社會角色的認識尚不清晰,未追溯其以合同為工具打擊制假售假的本源問題。即立法上忽視解讀已產生而未進入消費的假冒偽劣產品的法律性質,未在合適法律關系環境中賦予“知假買假”者應有角色。經營者(含生產者與銷售者等)處于產品生命周期上游,其組織原料、設備、人員和技術資源等獲得產品,通過交易實現價值。產品到達消費者前,政府基于公民人身、財產安全保護考慮,對產品屬性進行干預,制定技術標準、標簽與地理標志規則等。經營者必須在產品成為消費標的前達到國家要求,否則即違反了其在公法上的義務,未到達消費者的假冒偽劣產品是可能產生損害的“風險”,對其加以防控的義務乃歸于政府。從這個意義上說,“知假買假”者發揮了政府風險防控的部分作用,考慮它與政府的關系比置于消費契約中更合理。因此,現有“知假買假”爭論所得到的認識基于一個錯誤的語境(即消費合同法律關系),科學認識“知假買假”者社會角色和法律地位必須突破這一囹圄。
三、“知假買假”者地位的理性復歸與法制回應
既要發揮知假者參與打擊制假售假行為的積極性,又要避免其以“買假”這種反契約性的方法作為途徑,在我國相關法律制度設計時須打破“知假”與“買假”間的關聯,為真實消費者維權與知假者打假提供不同的制度工具,以保障知假者能與消費者、政府的權利(力)機制形成制度合力。
(一)對“知假買假”行為性質的再認識
⒈“知假買假”者抑制的是制假售假行為,彌補了政府監管資源和能力的不足,對制衡經營者盈利意圖肆意擴張具有積極意義。一方面,面對制假售假行為形成的危害風險,“將社會多元主體,尤其是不同代表的利益相關者、不同的立場和觀點納入到風險治理的過程中來”,[16]形成經營利益、消費利益和監管權的平衡,有利于保障公眾人身財產權益。“知假買假”在目的上與此契合,也是減少威脅健康的產品進入消費環節,維護了公眾享有的消費自由,法律制度應當認可其在保護消費者權益、形構良性市場秩序中的價值。另一方面,“知假買假”者通常具備較普通公眾更強的辨識能力,對生產、銷售中消費品的物理屬性、生產工藝、衛生安全狀況、標簽標識使用等情況認知水平較高,打擊制假售假精確度較高。其知識經驗累積能反映市場中產品質量真實狀況,有利于探索有效對策和方法,為法的創制活動提供素材。其行為也能引領以法律武器維權的社會風尚,改變消費者權益受損時怠于行權的心態,他們也可以接受消費者委托代為維權,在向消費者普及識假拒假知識、提高安全消費能力等方面提供生動的實踐知識。在價值目標和制度效果上,“知假買假”者能對社會風氣激濁揚清作出重要貢獻,法律制度應當承認其正當性。
⒉“知假買假”者在假冒偽劣產品的風險存續規律中處于關鍵位置,賦予了其發揮獨特功能的廣闊空間。“知假買假”針對未進入消費環節的在生產和待售產品,以消費者為參照體,“知假買假”行為處于損害的風險預防關系中。經營行為使假冒偽劣產品威脅著不特定主體的人身、財產利益,在社會中形成彌散性風險,經營者違反了向不特定公眾負有的對世義務。但與其對應的法律關系主體類型多樣,政府作為公眾利益保護人是職能性打假人,消費者為自身利益免受損害也是可以采取預防措施的適格主體,是自然性打假人。“市場對資源的配置起著基礎性的作用,市場經濟形式下的政府也只能為有限政府”,[17]政府作用是有限的,加之消費者的分散性,與經濟利益惡性擴張不匹配。“知假買假”者作為政府、消費者主體資格的補充,彌補了預防假冒偽劣產品進入消費環節的系統漏洞。雖然“知假買假”行為具有反契約性,但其控制危害于經營環節的預防性指向是合理的,即抑制經營者故意(如摻假食假)造成的作為性風險,引導經營者預防由過失(經營者設備落后)、意外引起的各種致害風險,這能與政府的職能行為和消費者的維權行為形成合力。當前,我國多數產品危害產生于經營環節中,處于價值鏈下游的消費者由于信息不對稱、維權能力弱、維權成本高等原因,難以有效反擊經營者的風險行為,由政府與“知假買假”者在價值鏈中游形成風險防控網絡最為合適。
⒊在行為效果上“知假買假”者以消滅自身為目的,依法發揮其積極功能不會破壞市場經濟秩序。由于他與制假售假行為處于對立統一中,打假效果越明顯則制假售假行為越少,對“知假買假”的繼續性需求越會降低。其法律地位可由法律直接規定,與經營者建立直接的法律關系,也可設計為政府、消費者的代理人。我國現行立法中沒有賦予“知假買假”者以獨立地位,而是將其與普通消費者一并置于消費契約的債權人地位。實踐中,普通消費者在獲知假冒偽劣訊息后,要么不購買,要么故意購買來滿足自己低價低質消費需求,受欺詐后傾向于保持沉默。而“知假買假”者更愿意借消費者的權利軀殼行事,以懲罰性賠償為工具打擊制假售假行為。因此,“知假買假”者正當法律價值的發揮,有賴于賦予其合理的獨立法律地位或代理人地位,使其能與經營者建立直接的風險預防法律關系。
(二)協同治理模式——風險規制的法制路徑所在
在保護“知假買假”行為功能的同時,要改變其反契約的性質,必然要求我國法律制度加以創新,在風險預防和損害救濟的共同目標下,除了形成經營者自律、消費者自救的模式外,更要注重政府與“知假買假”者等協力形成風險防控體系。從目前看來,制假售假等市場亂象已經對經濟社會秩序造成了破壞,我國立法賦予經營者、政府和消費者的風險規制手段存在“失靈”的情況,因此,以合理的方式將“知假買假”者嵌入風險防控體系中是必然選擇。對此,“我們可以把協同學引入對我國公共危機管理的研究之中,進而創建新的更適合現代社會發展需要的公共危機管理模式”,[18]這就要求在制度上鞏固權利(力)共同體,加強對違法行為的抑制,以建構公私合作、多元參與的協同治理模式。
⒈積極規制——完善風險防控體系的系統化構建。“知假買假”者彌補我國產品風險防控體系的漏項,就是以法律制度為手段,形構職能打假人(政府)、自然打假人(消費者)、職業打假人(知假買假者)組成社會積極效應,維護共同體。換言之,就是在當前政府監管和消費者維權的基礎上,將“知假買假”者轉化為與政府、消費者平行的風險規制主體,并提高其與監管權運行的協同性及對消費者維權意愿的激勵作用,在規制產品風險領域最終形成主體功能互補、利益均衡的法律機制。
一方面,增強政府、消費者運用風險規制工具的實質有效性,破除不利于二者主體功能發揮的法制障礙。第一,通過優化制度設計,逐步降低消費者的維權成本。這就要求在既有的懲罰性賠償力度之外,適當擴大民事法律、消法中的賠償范圍和額度,借鑒我國《合同法》中關于合同保全相關費用償付規定,將消費者維權中合理的交通費、法務服務支出等列入。在具體案件中,加大對消費者主張懲罰性賠償、精神損害賠償的支持力度,提高個體消費者維權成功的幾率。積極發揮指導性案例在保障法律的準確適用方面的作用,并與司法解釋結合起來。[19]對《民事訴訟法》第55條規定的公益訴訟制度給予實在化,形成便于消費者組織化維權的法律機制。第二,構筑系統協調、層次分明的防控權力配置模式。調整政府監管權配置,構筑分階段、分部門的協同性風險監管防控體系,形成科學建議權、決策權和執行權相對獨立的監管權行使模式。將各部門的技術力量整合為獨立于行政執法權的科學咨詢機構,專司于風險評估、溝通和管理的專業化力量,形成風險客觀存在與否與應對措施制定的客觀性、科學化結論,直接對各級人民政府負責。各級人民政府或協調性機構(如食品安全委員會)根據科咨機構對客觀形勢的研判,向各相關部門發出執行指令,在保持行政部門分工的前提下形成規制制假售假行為的權力合力。
另一方面,賦予“知假買假”者獨立的法律地位,并完善相應的利益保障機制。作為與經營者相對應的風險規制主體,“知假買假”者獨立于消費者的法律地位必須得到確認,當然其主體作用的發揮可采取政府委托、征集消費者的維權主張和自行公益性打假等方式進行,但要賦予其請求一定比例的打假收益作為勞動回報的權利。第一,實現“知假買假”者社會公益角色法律化和規范化。建立“知假買假”機構審批和“知假買假”個人備案制度,使其與經營者之間形成直接的法律關系,“知假買假”者能以自己的名義及行為而無需冒充消費者,采取公益訴訟制度等手段打擊制假售假。第二,建立有償舉報制度,為“知假買假”者向政府讓渡制假售假信息提供基礎。當前,我國的公益訴訟制度還存在訴訟主體錯位、公益效果不明顯等諸多困境,[20]因此,設立“知假買假”者呈報監管機構的制度通道非常必要。以行政機關對經營者的處罰額度為基數,給予一定比例的獎勵,既能彌補“知假買假”者相應的支出和合理的勞務報酬,又能使“知假買假”者具有與政府監管部門形成協同配合的動力。第三,建立“知假買假”者與消費者維權的配合機制。允許“知假買假”者向消費者公開征集小額索賠主張,以委托代理等方式將消費者零星訴求化零為整,并與消費者達成類似于風險訴訟中的懲罰性賠償金分配約定,但以不超過法定比例或額度上線為限,并相應地完善民事訴訟法中代表人訴訟與訴訟合并審理制度。
⒉消極規制——強化經營者、政府風險防控法律責任。除采取各種措施增強社會積極正面力量外,還需采取有效措施抑制造成、擴大風險的消極負面力量,強化經營者肆意妄為和政府失察的風險防控法律責任。嚴格規制其違反風險防控的作為與不作為,明確相關行為應受到的否定性法律評價,引導經營者放棄、減少制假售假行為,降低行為的風險程度,引導政府機構及其工作人員克服懈怠行權模式。
一方面,我國現行立法中經營者責任設定與風險存續規律不匹配,采用假冒產品經濟價值而非風險程度作為責任計算基準值,“企業違法成本過低,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刺激下企業明知故犯,鋌而走險”。[21]改善之道在于:第一,細化確立風險程度的技術性規則,為追究風險法律責任提供歸責方法。模仿稅務機關核定應稅金額的方法,通過調研來確定特定區域內公眾消費假冒產品同類產品中的位值,同時根據查獲的假冒偽劣產品數量和質量低劣程度,結合人均攝入量或該產品日均使用量,測定其損害程度和影響面,以此標準來確立處罰額度。對未進入消費環節即被查獲的產品可按一定比例折算,對風險已釋放給消費者的還應追究民事、行政責任,消費者損害部分按民事侵權處理,已售出但未召回、未承擔民事賠償的則承擔風險責任,根據交易數量扣除民事侵權已賠償部分來確定處罰標準。第二,建立以風險等級差異為基礎的結構性罰則。借鑒美國食品安全法的分級處理方法,如《聯邦食品藥品和化妝品法案》第301、第303部分的規定:對任何食品安全的違法行為都采取1年以下或1000美元以下處罰或二者同時適用,對嚴重違法則納入刑事違法中的罰則。[22]再如2011年4月美國《食品安全責任法案》(S.216)規定:故意或對生命和生命損害風險的忽視則按照美國法典第18部分實行經濟處罰或處以10年以下徒刑,或二者同時適用。[23]我國在《國家食品安全事故應急預案》等規范中已將產品質量事故作出了等級劃分,可以借鑒美國的違法懲處機制,采取分級定量處理的方法對違法主體進行懲處。第三,必要時可采取加重懲處的責任追究手段。在上述方法中選定一基本懲處依據,但對主體的故意行為和惡意不執行處罰的行為,在基礎處理依據上加倍執行,這也是美國《聯邦食品藥品和化妝品法案》第303部分和2007年《食品藥品管理修正案》第902部分中管理藥品的重要措施。[24]
另一方面,由于假冒偽劣產品釋放風險過程的時間跨度大,而我國的監管權力階段性、部門劃分同時存在,致使監管機構間的風險預防義務較模糊,特別是經營信息和政府信息透明度不高,[25]追究法律責任難度較大。因此,必須化解風險信息義務、責任在監管權體系內歸屬混亂的問題,提高信息溝通的多方參與水平,促進風險信息公開中政府與相關利益方的多元互動。一是建立政府接受公眾監督義務的法定機制。應完善監管機構應答社會主體對產品風險信息、監管信息等訴求的程序(歐盟要求對消費者投訴按標準格式統一分類,并使用標準化的投訴管理信息平臺),[26]將政府的監管義務細化到具體機構,在明確義務主體的前提下才能理清責任。二是強化監管機構在風險防控中的公共服務提供職能。既要提高產品質量標簽、標識、說明書等風險信息的完整性和普識性(歐盟專門編撰了標簽識別手冊[27]作為消費者辨識標簽的輔助資料),也要保障監管權運行信息通過官方文件、聲明、公告等途徑讓公眾知曉,將監管權啟動、行使依據、處理后果、程序過程等公之于眾,通過提高政府信息的透明度,將形式的共治提升到實質的共治。
總而言之,“知假買假”行為目的的正當性與方式的反契約性,折射出我國現行立法對社會主體參與風險預防的法制供給不足。因此,必須在法律地位、行為模式設置等方面將“知假買假”者納入法律制度譜系,在實定法層面上既能滿足直接向制假售假行為出擊,并與政府、消費者法律功能相協調,又能在法律文化功能方面培育公民精神。隨著市場秩序逐步回歸理性,“知假買假”行為必將隨著制假售假現象的減少而逐漸退出法制的視野。
【參考文獻】
[1]趙旭東.論合同的法律約束力與效力及合同的成立與生效[J].中國法學,2000,(01):80-85.
[2]王衛國.中國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與懲罰性賠償[J].法學.1998,(03):22-28.
[3]梁慧星.知假買假不受消法保護[N].南方周末,2002-07-05.
[4]謝曉堯.消費者:人的法律形塑與制度價值[J].中國法學.2003,(03):23.
[5]楊立新.“王海現象”的民法思考——論消費者權益保護中的懲罰性賠償金[J].河北法學.1997,(01):5.
[6]王利明.消費者的概念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調整范圍[J].政治與法律,2002,(02):4.
[7]王利明.關于消費者的概念[J].中國工商管理研究,2003,(03):39.
[8]李振宇,李學迎.知假買假行為適用懲罰性賠償評析[J].政法論叢.2006,(01):55.
[9][14]周倫文,王建平.對知假買假是否適用雙倍賠償的再思考[J].新疆社科論壇,2005,(02):40.
[10]覃有土,晏宇橋.論消費者之義務[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04,(02):95-97.
[11]董文軍.論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的懲罰性賠償[J].當代法學,2006,(02):72.
[12]應飛虎.知假買假行為適用懲罰性賠償的思考——基于法經濟學和法社會學的視角[J].中國法學,2004,(06).
[13]沈幼倫,黃偉豐.也談知假買假索賠的“王海現象”[J].法學.2002,(08):32.
[15]于彥麗.論懲罰性違約損害賠償的必要性及其適用條件[J].青島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2003,(04):83.
[16]張成福,陳占鋒,謝一帆.風險社會與風險治理[J].教學與研究.2009,(05):5-11.
[17]吳傳毅.有限政府:民主政府的時代內涵[J].四川行政學院學報,2005,(03):5-8.
[18]張立榮,冷向明.協同學語境下的公共危機管理模式創新探討[J].中國行政管理,2007,(10):100-102.
[19]王利明.我國案例指導制度若干問題研究[J].法學.2012,(01):71-80.
[20]許清清,文勇.我國公益訴訟的困境與出路——以36例公益訴訟案件為分析樣本[J].經濟法論叢,2012,(01):1-29.
[21]王小龍.論我國食品安全法中風險管理制度的完善[J].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02):32-38.
[22]FDA.Federal Food,Drug,and Cosmetic Act (FD&C Act)[EB-OL].http://www.fda.gov/RegulatoryInformation/Legislation/FederalFoodDrugandCosmeticActFDCAct/default.htm.2013-08-05.
[23]House of Representatives.S.216(112TH Congress 1ST Session)[EB-OL].http://www.gpo.gov/ fdsys/pkg/BILLS-112s216rfh/pdf/BILLS-112s216rfh.pdf.2013-08-05.
[24]FDA.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Amendments Act(FDAAA) of 2007[EB-OL].http://www.fda.gov/RegulatoryInformation/Legislation/FederalFoodDrugandCosmeticActFDCAct/SignificantAmendmentstotheFDCAct/FoodandDrugAdministrationAmendmentsActof2007/default.htm.2013-08-06.
[25]湯萬金,楊躍翔.關于建設我國國家質量監管體系的思考[J].世界標準化與質量管理.2008,(06):4-8.
[26]曾文革,肖峰.歐盟食品安全社會監督立法的“便利性”特征及對我國的啟示[J].大連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03):83-87.
[27]irectorate-General for Health and Consumers European Commission. how to read a label[EB/OL].http://ec.europa.eu/dgs/health_consumer/index_en.htm.2011-10-10.
(責任編輯:王秀艷)
On the Anti-Contract and Overcoming of the Behavior of Buying Fake
Xiao Feng
Abstract:Our country has been in consistent discussions of the applicability of punitive compensation or not to it in the practice of “buying fake” phenomenon for a long time, including whether to give “buying fake” people the status of consumers,and whether the cracking down fake behavior has the legitimacy of value.However,to ignore the anti-contract and the social risks reflected by the behavior is the inevitable slack to the due reflection of regulation path.This paper holds that it is right to take the analysis of the conditions of time and space of fake and shoddy products as the basis,to determine the reasonable positions of the government,“fake buyers” and consumers in social control network of making and selling fake good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common goal of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social risks and the defense of the spirits of contract.
Key words:contract;buying fake;social risk;collaborative gover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