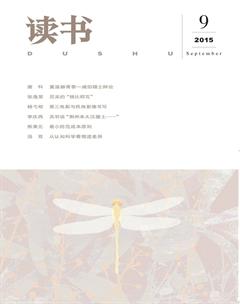第三電影與民族影像書寫
楊弋樞
二○一五年春,洛杉磯紅貓當代藝術中心放映了菲律賓導演基拉·塔西米克的影片《甜蜜的夢魘》,一部近四十年前的以反思西方文化滲透及批判后殖民為基點的菲律賓獨立電影,在洛杉磯觀眾中引起陣陣笑聲和經久的掌聲,這情景頗有意味。在映后交流時間,基拉穿著菲律賓土著民族伊格洛特族服裝,在臺上表演了一個自編的舞臺短劇,他扮成好萊塢大學的博士畢業生回去向母親呈上自己的學位證書,卻遭到母親的批評,他由此驚醒,丟棄了好萊塢大學的學位證書并回到遺忘的自己的傳統。顯然在這個幽默的寓言故事里,子虛烏有的“好萊塢大學”是一個戲謔的喻指,基拉在這個舞臺表演里精準地概括了他的文化處境。
《甜蜜的夢魘》喚醒一個特定的電影時期,那就是上世紀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第三電影在第三世界國家彼此呼應的年代。彼時拉丁美洲各國新電影運動興起,巴西導演多斯桑托斯的《貧瘠的生活》以其對底層人民的人道關懷和對社會問題的尖銳呈現,拉開了巴西新電影運動的序幕。格勞貝爾·羅加拍攝了《黑色上帝白色惡魔》、《恍惚的土地》、《職業殺手安東尼奧》等多部影片,直面巴西腐敗的政治面貌、無情的斗爭局面、媒體的丑陋、人性的扭曲,他的電影呈現了被卷入其中的個體在這一處境下的恍惚感受和覺醒,在形式上又將現代主義與巴西傳統民族風格結合為一體。在軍事政變頻繁、人民生活困苦的玻利維亞,導演荷西·桑吉內斯拍攝了《它就是如此》、《禿鷲之血》、《圣胡安的夜》等影片,記錄社會矛盾、印第安民族對帝國侵略的反抗、軍政府對底層礦工殘酷的大屠殺,他堅持左翼革命立場,堅持個體獨立電影制作方式,被稱為“第三世界的革命電影詩人”。阿根廷導演費爾南多·索拉納斯和奧克塔維奧·赫迪諾的紀錄片《燃火的時刻》是一部宏大而豐富的影片,影片梳理阿根廷的苦難歷史和當下癥結,批判地反思阿根廷的新殖民狀況、軍事鎮壓與阿根廷的暴力現實、自由運動、財閥與外國利益集團的勾結、貧民的生存現實等等。在非洲,由法國返回故土的導演烏斯曼·塞姆班完成了非洲電影史上的第一部長片《黑女孩》,他最有影響力的影片是《夏拉》,該片呈現了獨立后的非洲國家的荒謬處境:獨立后的被殖民國與前宗主國的新的依賴關系、新經濟模式和舊權力關系、傳統生活方式混合成新非洲生活,被施以寓言般的“夏拉”詛咒。
這些影片風格各異,但它們都一致將攝影機對準本民族現實,面對殖民歷史與當代新殖民主義給本國帶來的創傷,關切政治和社會動蕩狀況之下平民的苦痛,展現民族傳統的豐富性。與當時涌動于第三世界國家內部的革命激流相映襯的,是電影自身的革命。第三電影作為自覺的電影實踐,使革命的電影和電影的革命成為這一時期的主題。阿根廷導演費爾南多·索拉納斯和奧克塔維奧·赫迪諾的那篇著名的《邁向第三電影》一文中稱(他們的主張得到弗朗茨·法農、切·格瓦納和胡志明的支持):“第三世界人民反帝國主義,以及在帝國主義內部爭取平等的斗爭,是今天世界革命的軸心。”文學、科學、藝術都被階級所定義,是新殖民關系里的不可缺少的部分,第三電影需要和這個巨大的文化再生產體系作戰,它需要面對自身的歷史和現實,它的觀眾不是資本主義發行體系里的大眾以及古典趣味培育的藝術愛好者,而是需要被喚醒的本國人民。在索拉納斯和赫迪諾看來,就連巴西新電影也不盡是他們認定的第三電影,他們將第三電影嚴格從第三世界電影中劃別出來。第三電影,是那種不能為電影體制吸收、與體制的需求完全相異的電影,或是直接而明確地向體制宣戰的電影。第三電影首先當然區別于以好萊塢電影為標準的封閉于資產階級內部維護資產階級再生產的商品電影(第一電影),它也區別于歐洲等國家的作者電影、表現主義電影、新浪潮電影(第二電影),第二電影已是在電影系統內部反抗的極限,但,敵意、不墨守成規、破壞秩序、宣泄不滿等,依然是資產階級的一部分,反體制的藝術最終都被體制吸收了,成為其一部分,只是為資本主義市場增加了更多的以“不同”面目出現的消費品—資本主義文化本性里還有“每天來一劑震驚”的嗜好。因此,只有第三電影才是電影革命的唯一可能所在,它必須是每秒二十四幀的槍,第三電影的目標,就是“建構自由品格,使每個人都以反殖民作為起點”。
第三世界電影面對各自的具體歷史,殖民和政治無序都是現實存在,第三世界知識分子所面對的,是西方帝國主義在本國的代理或已滲透于日常生活的文化無意識。第三電影的命運還取決于它的對立面,因此各國電影軌跡各異,有電影制作者被本國政府禁止、監禁、驅逐,比如玻利維亞的桑吉內斯,另一些電影制作者則和革命潮流合拍共振,比如索拉納斯,南美第三電影之激烈的革命狀態,與南美社會內部無法化解的深刻的社會矛盾以及矛盾隨時面臨爆發這樣一個歷史現實是直接相關的。七十年代后期開始制作電影的基拉·塔西米克就沒有索拉納斯和赫迪諾那么激進和絕對,他甚至是機智俏皮幽默的,這和菲律賓社會相對平和不無關系,但在自覺反新殖民書寫這一立場上,亞洲導演與拉美、非洲導演完全一致。基拉半自傳敘事電影《甜蜜的夢魘》是一個豐富的第三世界文本,觸及第三世界知識分子和藝術家關切的很多重要問題,如文化身份認同、西方意味著什么、全球化與文化傳統的關系、后殖民處境下知識分子何為以及如何抵抗美國通俗文化與好萊塢電影在世界范圍內所行銷的意識形態等等。而這一切問題的起點,是怎樣認識菲律賓,如何認識自身。影片在基拉的畫外獨白里開始:“這是通往我們村子的橋,它是進入巴里昂(村名)的唯一途徑,也是唯一的出口。它是我們的生活之橋。西班牙士兵拆除我祖父修建的竹橋之后建了現在這座橋,美國軍隊曾經想拓寬這座橋,但因為周圍的山很堅固,他們沒有成功……”基拉扮演自己各個年齡拉著玩具卡車通過橋的情景,詼諧地由一座橋概括了近代菲律賓的殖民歷史:其先后被西班牙和美國侵占殖民的歷史。基拉出生于日本軍國主義侵占菲律賓的太平洋戰爭時期,在他的童年時代,美國宣布菲律賓獨立,但仍然保持在這個歷史上的正式殖民地的經濟、政治和軍事特權,“二戰”后到七十年代,菲律賓在經濟上依靠美國,其新殖民結構不斷鞏固,基拉的電影從這里開始,基拉本人扮演的吉普車司機迷戀美國的一切,從選美小姐到太空計劃,從電影到每天必聽的“美國之聲”,對西方現代化生活的向往使他對村莊的落后景象越發感到失望。一個美國商人恰好需要一名司機,將他帶往巴黎。以一座又一座比他家鄉的橋高大現代多姿多樣的橋,基拉“以小見大”地描畫了一個初到西方發達國家的青年大開眼界的欣喜,他夢寐以求的一切都在眼前,這一切和他的家鄉有著巨大落差。然而對作為奇觀世界的西方的新奇感過去后,當基拉試圖和這個社會有更深入的交流和友誼時,他唯一的朋友、一個個體零售商因為超級市場興起受擠壓而無法生存最終自殺,基拉的西方夢在此破碎了,他開始重新認識自己的家鄉。影片里西方和家鄉作為對比呈現:欠發達地區鄉野和西方現代都會、民俗傳統與流行文化、手工制造與跨國企業、承載著全部生活的橋和作為建筑和工業景觀的橋、溫情的民間社會和冷淡疏遠的現代人際關系、情感和疏離……影片記錄了一個年輕人的覺醒,他從迷戀“美國制造”到認識資本主義擴張的本質,到對自身文化殖民處境的清醒意識,再到返回自身文化傳統的歷程。簡言之,基拉用幽默自嘲而充滿創造性的影像講述了一個出走、返家、尋根的后殖民故事。
基拉本人當年在美國念完經濟學學位,之后去法國一家國際金融機構工作,這頗能代表第三世界部分知識精英的軌跡。但幾年后基拉辭職回到菲律賓,從事獨立電影制作,并在菲律賓展開一系列行動。在紛紛趨向歐美的全球性移民潮里,他的返家是逆向而行,或也是一個戰風車的行動,因此《甜蜜的夢魘》還是一個第三世界知識分子(藝術家)的心靈史:他的覺醒、文化危機感和精神焦慮。夢魘,是對無法逃脫的現實的描述,政治和經濟的后殖民有跡可循,文化滲透卻是無形的,多民族融合和特殊的殖民歷史,使菲律賓文化天然帶有混合性特征,就連菲律賓的外來宗教,也是融合了本土習俗,西班牙文化、美國文化已融進菲律賓的日常生活,這種歷史語境下,什么又是菲律賓傳統呢?返回菲律賓的基拉,一面用影像尋找菲律賓歷史,一面投身于行動,建立藝術區域,甚至走上街頭表達政治關切,這委實是一個重建的過程,《誰發明了悠悠球?誰發明了月球探險車?》、《過度發展的記憶》、《為何彩虹中間是黃色的》、《世界之巔!聯合起來!》等等影片就是這個重建過程的記錄,基拉追尋菲律賓歷史,行走于菲律賓山區,和原住民一起居住,他投身于烏托邦般的藝術社區建設,他也在城市的街頭做行為藝術來吶喊呼吁,他不是把自己只當作一個導演,他以知識分子的清醒,用全部作品和行動重新定義菲律賓,介入菲律賓的現實政治。詹姆遜在那篇著名的《處于跨國資本主義時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學》一文中說,第三世界的文化都不能被看作人類學所稱的獨立或自主的文化,這些文化在許多顯著的地方處于同第一世界文化帝國主義進行的生死搏斗之中。伴隨跨國經濟,社會和文化已被現代性滲透的當下,搏斗與搏斗之難,成了基拉這樣艱難尋找自我文化身份的知識分子的困境。
第三電影存在于相對性中,存在于它與其所搏斗或對抗的對象的關系中。制作時間前后跨度三十余年的《過度發展的記憶》是返家后的基拉的漫長求索的記錄,記錄了他尋找菲律賓傳統、尋找自由之途的努力。基拉轉向菲律賓伊格洛特族部落尋求傳統資源,伊格洛特是一個高山上的部落,崇尚自然質樸的生活哲學,外部世界數度變遷,他們依然完整保留著自己的文化傳統。基拉深入部落毗鄰而居,和原住民一起制作手工木雕,甚至穿上了伊格洛特人的服裝。此后,每當他出現在各國電影節、影展或大學演講時,用木雕竹制書寫菲律賓歷史的伊格洛特手工藝術品展示、身穿伊格洛特服裝的舞臺短劇表演成了基拉的保留節目。基拉展覽的藝術品中,竹制的攝影機和木雕好萊塢明星夢露在電影《七年之癢》里被風吹得裙裾飛起的經典造型,諧趣而特別。對于基拉,好萊塢是一個無法繞開的相對物,不僅如此,他的電影既反好萊塢模式化敘事,也區別于歐洲藝術電影由經典藝術形塑的那種講究的藝術趣味,他自成一體,自傳、虛構、社會寫實、政治批判、抒情、菲律賓式幽默、藝術、古今對話等等繁復的內容經過他無與倫比的剪輯而呈現一種獨特的豐富多義性。他也在公開場合一再表述他與好萊塢(以及好萊塢所代表的文化新殖民)的對立立場。在木雕夢露這個反寫的關系里,基拉除了表達傳統與現實的對話,他的竹編和木雕不僅重新書寫民族的歷史,也在用自己的傳統改寫好萊塢與好萊塢代表的大眾文化的內涵—經由木雕,經由多棱的木質質感重塑,好萊塢消費文化中夢露的性感形象變成質樸厚重的東方女神,對于滲入第三世界肌理的流行文化無意識,基拉以寓言的方式予以僭越。
當我在洛杉磯見到基拉時,被稱為菲律賓獨立電影之父的七十多歲的老藝術家依然堅定地反后殖民、反好萊塢,這一立場一生未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