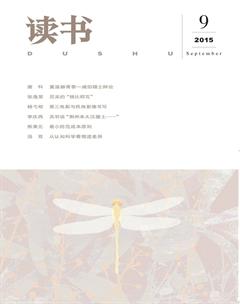關羽說「荊州本大漢疆土……」
李慶西
《三國演義》第二十五回,曹操大軍將關羽圍在下邳城外一座土山上。此時徐州、小沛已失陷,劉備、張飛各自逃命。關羽未便逃跑,是因為甘、糜二夫人尚在下邳,他負有保護之責。曹操派張遼來勸降,關羽提出三個條件:一是降漢不降曹,二是不能為難兩位嫂嫂,三是日后但知劉備去向立即走人。關羽追隨劉備拯援漢室,本來就是漢臣,其以“降漢”申辯名義,有些自欺欺人;打著這種旗號歸附,倒不啻是承認曹操代表漢室的資格。所以曹操并不惱,還笑著說:“吾為漢相,漢即吾也。”這話自然流露剛愎自用的倨傲心態,但此際他只想著收納關羽為己所用,不去糾纏什么說法。彼此各自表述,各取所需,乃以實用主義對付機會主義。雙方都是應機權變,其實誰也不吃虧。
甘、糜二夫人既然成了人質,給予優待不成問題,像是道上的規矩,此前呂布擄獲劉備家眷也是好生侍養。關鍵是關羽提出的第三個條件,頗讓曹操猶豫。既然人家早晚得回到劉備身邊,曹操心想,那還養著他干嗎?張遼舉述戰國刺客豫讓“眾人”、“國士”之論,勸說曹操答應這一條。在張遼看來,若以優于劉備之恩厚對待關羽,想必終能使他回心轉意。
這里涉及“忠誠”的道義基礎,張遼扯出豫讓的例子,是一個有趣的話題。按《史記·刺客列傳》,豫讓的舊主范氏、中行氏讓智伯給滅了,他被收在智伯門下。后來智伯又為趙襄子所滅,幸而逃脫的豫讓決意要替智伯報仇,毀容隱名亡命江湖。他在行刺時被執縛,趙襄子詰問:你早先的主人為智伯所滅,你并未替他們挺身而出,現在怎么倒要為智伯報仇?一問之下,便有豫讓這段經典臺詞:“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眾人(一般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于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豫讓的忠誠動機很簡單—“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
《史記》所述豫讓事略皆出《戰國策·趙策一》,按顧炎武說法,那正是“邦無定交,士無定主”的時代。其實,諸鎮紛爭的三國時期亦大致如此,大家都在道上混,誰也不至于一棵樹上吊死。但這里的問題是,關羽不是豫讓,他在劉備那兒亦非“眾人”一格。所以,盡管曹操待之甚厚,贈袍、贈金、贈馬、贈美女,三日小宴五日大宴,最后還是留不住他。當關羽得知劉備在河北袁紹那兒,便毅然封金掛印,帶著兩位嫂嫂遞遞迢迢奔其而去。千里走單騎,過五關斬六將,可謂歷盡艱難厄阻。書中這些虛構的情節極為精彩,不但是寫關羽之果敢勇猛,更是表現其忠心義膽。
秦漢之前,士者忠誠之道義基礎主要在所謂知遇之恩,但以某些個例而論,不能說沒有其他因素。如《史記·趙世家》記公孫杵臼、程嬰舍命救護趙氏孤兒,是將“立趙氏之后”作為延續宗祀的大事業,顯然不僅為著感恩與報答。司馬遷未及細述趙氏恩厚如何,但從公孫杵臼言辭(“趙氏先君遇子厚”)可以看出,主人對待他倆自有厚薄之分。公孫杵臼帶著假趙氏孤兒赴死,是因為程嬰認為“死易,立孤難耳”—既然程嬰恩遇更厚,由他擔負“立孤”重任自是順理成章。這個故事后來被元人紀君祥編為雜劇《趙氏孤兒》,更是淡化其報恩色彩,大大強化了“立趙氏之后”的家國倫理大義。同樣亦為宋元以后的講史作品,《三國演義》塑造關羽忠勇節義之高大上形象,亦同樣注入這種倫理政治觀念。
關羽之忠誠,《三國志》已有原型,其傳中亦記述解白馬之圍后辭曹操而回歸劉備。關羽早就跟張遼說過:“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當然,這里表達的還是知遇之恩。小說中桃園結義之事,大抵從“誓以共死”一語中敷衍而出。但這“誓以共死”,并非結義時所謂“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字面意思,應該指彼此赴死以求的某種共同事業。小說將這層意思做了明晰闡發,那就是桃園結義誓言中所謂“上報國家,下安黎庶”云云。
小說第六十六回中,諸葛瑾來索討劉備佯許的長沙等三郡,關羽聞言竟勃然大怒,聽著像是完全不給劉備面子—“吾與吾兄桃園結義,誓共匡扶漢室。荊州本大漢疆土,豈得妄以尺寸與人?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這話可謂大義凜然,點明結義乃志在“匡扶漢室”,自有超越私誼的大目標。所謂還荊州一半與東吳,只是諸葛亮導演的一出戲,讓劉備唱紅臉,關羽唱白臉。關羽倒是錚錚有聲,理直氣壯—結拜之義是報效國家,而兄弟私誼不能妨礙國家利益。諸葛亮跟諸葛瑾還是親兄弟,對此倫理大義,亦是各為其主。
史傳未有劉關張結義之事,但三人間親密關系在陳壽筆下有所記述,《蜀書·關羽傳》開頭這段話約略勾勒出一番情形,亦為小說提供描繪他們兄弟情誼的基本素材:
……先主于鄉里合徒眾,而(關)羽與張飛為之御侮。先主為平原相,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寢則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
另,《張飛傳》亦謂:
張飛……少與關羽俱事先主。(關)羽年長數歲,(張)飛兄事之。
“恩若兄弟”不能說是正式結契,此中關系可略作討論。劉備私下里與關、張二人“寢則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卻是另一種情形。古代人倫語境與今不同但當日宗法社會與現代黑社會有著相似的差序結構,長兄與諸弟固以親情(情誼)凝聚為團體,彼此亦是老大與馬仔的關系。關羽與張飛在劉備身邊終日侍立之際,儼然已將這大哥視為人主。在“漢官威儀”成為禮治風氣的年代,這種“恩若兄弟”的關系自然很容易內化為“君君臣臣”的倫理自覺。當然,《三國志》記述劉關張諸事并未明確貫以圣王之道與國家意識。陳壽敘史以曹魏為正統,對于劉備承祧漢室的合法性未予肯定;從《先主傳》看,面對諸鎮紛爭之亂局,劉備糾合徒眾,只是爭一分天下而已。然而,到了《三國演義》里邊,其承祧漢室的使命就一再被強調,關羽的忠誠亦便納入了超越一般人倫層面的政治內涵。
至于曹操,關羽實是頗有感恩之念,人家好吃好喝招呼著(當然,“上馬一提金,下馬一提銀”那些細節都是小說家臆構),怎么說也是一份恩惠。不過說到底,那只是一筆人情債,斬了顏良就算是抵還了人情(小說中又買一送一,多斬一個文丑,以后還有華容道一節),無須終身鞍前馬后替曹操做事。于曹操而言,關羽倒是不折不扣的“持不同政見者”(今人所謂“政見”,古人視為“大節”),不可能成為其黨羽。關羽心里明白,劉備那兒才是他真正的歸屬。劉備不止是兄長和老大,毫無疑問,關羽認準這中山靖王之后、皇N代血脈的劉皇叔才是“國家”。
“士為知己者死”,其言鏜鞳有聲,卻只能說是一種簡單的報恩觀念。猶之革命話語所謂樸素的階級感情,是對救主、人主的感念之言。其實,一說感恩與報答,士者與人主已然有別。張遼舉“國士”之論,之于關羽實在很確切,(《蜀書》關張諸傳評曰:“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并有國士之風。”)但究竟以劉備還是曹操為主公,絕非只是金錢爵祿的計較。張遼忽略了一個重要關節,就是今人所謂思想立場,其中自有是否政治正確之因素。
如果不是遇上劉備,關羽只是游俠刺客一類角色。他在鄉里殺了人,久已流落江湖(《關羽傳》謂之“亡命奔涿郡”),跟從劉備之后才算是上了道。從本質上說,這跟孟嘗君的門客沒有兩樣。司馬遷作《游俠列傳》,敘說朱家、郭解諸事,實著眼于君侯事業,意在讓季次、原憲那樣的獨行君子“效功于當世”,亦即如何使天下閭巷之俠“軌于正義”。其實,人主如何收納天下桀士,君侯怎樣燮定手下一干徒眾,亦是收拾漢末亂局之關鍵。故王夫之有謂,“所謂雄桀者,雖懷不測之情,而固可以名義馭也。明主起而馭之,功業立而其人之大節亦終賴以全”(《讀通鑒論》卷九)。然而,王夫之強調“名義”,與司馬遷僅著眼于“效功”已是大為不同,宋元以后,尤其明清之際,儒者意識形態中已將概而言之的“天下”明確為國家實體;而產生于蒙元入主中原之后的《三國演義》,借“匡扶漢室”大做文章,明顯是召喚漢族士夫之歷史記憶,強調華夏民眾之國家認同。所以,其“名義”之辨,如謂“漢賊不兩立”之類,實是一條重要的敘事原則。
劉備以何種“名義”驅馭關羽、張飛?無非是兩條:一者是作為人主身份的合法性,他是“中山靖王之后”,又是“皇叔”;一者是以整飭郡國天下為目標,所以他一再以“匡扶漢室”為號召。從關羽這方面來說,正是這兩條奠立了他的忠義人格。
《三國演義》的政治情懷分明是宋元以后國家意識的轉錄,而陳壽的敘事基于成王敗寇的歷史消息。所以,《三國志》不可能獨于劉備的訴求賦予某種具有合法性的理想架構。像劉表、劉焉、劉璋那些人都是漢室宗藩,要說奉天承運的合法性,不唯其劉備一人(《蜀書》將劉焉、劉璋二傳列劉備之前,實則以為先主之前之“先主”)。《先主傳》雖然透露劉備有帝王之志,亦謂“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但陳壽并不認為劉備有資格承續大統,甚至都不認為托翼曹操的漢廷還是一種合法性存在。小說里一再鼓吹拯救漢室的光榮與夢想,而《先主傳》里的劉備不曾借由如此申明大義的話語力量。通觀《先主傳》,只是劉備即位漢中王時,上表獻帝的官樣文章里才有“靖匡王室”的字樣。
陳壽記述劉備如何糾合關羽、張飛乃至趙云、馬超數輩,不講什么大道理,只是以“恩若兄弟”為籠絡。當然,陳壽筆下的劉備倒不失仁者風范,如當陽撤退攜民眾十萬,行路艱難亦未肯舍棄;(有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又如入葭萌關即“厚樹恩德,以收眾心”。在小說里,劉備這些仁義之舉自然被大肆張揚,甚至不乏陣前摔阿斗這樣夸張的細節。不過,《三國演義》表現劉備之仁厚,絕非婦人之仁,而是與社稷大義相為表里,自有一套崇高話語。比起史傳中“真實”的劉備,小說家刻畫這個人物明顯突出講政治講大局的觀念,其引領左右的訣竅亦在于此。
譬如,第十一回陶謙二讓徐州,劉備堅執不受,關羽、張飛勸其“何必苦苦推辭”,劉備卻道:“汝等欲陷我于不義耶?”這未必是故作姿態,其救援徐州打著主持正義的旗號,這時候得了徐州難免落下乘人之危的名聲。劉備給曹操寫信勸其退兵,申述黃巾遺孽和董卓余黨之害,亟言“愿明公先朝廷之急而后私仇,撤除徐州之兵,以救國難”。如此奮辭陳義,標格甚高。先朝廷之憂而憂,穩定壓倒一切,這就是政治。再說徐州乃“四戰之地”,劉備本不欲成為眾矢之的—后來陶謙臨終托任,不得已權領徐州事,果然就被袁術、呂布、曹操輪番絞殺。其時劉備實力不濟,尚不足以自領州郡,取舍進退之間自需掂量利弊得失,這亦是舉大事者之大局觀。又如,第二十回許田打圍,曹操迎受群臣山呼萬歲,關羽忍不下這口惡氣,“提刀拍馬便出,要斬曹操”,卻被劉備制住。事后劉備解釋“投鼠忌器”的道理,擔心的是獻帝安危。關羽、張飛之所以跟從劉備,其政治觀、大局觀是不能忽視的重要因素。
古人以仁恩馭士,內中自有付諸某種理想化的倫理邏輯。先秦儒者以為這種“尊尊親親賢賢”的仁愛模式便是建構圣王之道之樞要,借此可將鄉曲之俠、江湖吊絲一并納入禮治軌道。故《禮記·大學》有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其實,僅由上下關系厘正責任與義務,這種倫理構想過于簡單。如果說上者盡施予恩惠,下者必聽命于上,什么事情都不難擺平,天下就應該秩序井然祥和安寧,而儒者這番道理恰與許多實際情形大相徑庭。
《三國演義》虛構的桃園結義倒是一種有效的統馭方案,它為劉備如何糾合徒眾設計了頗有創意的組織形式,也即以匡振大義為宗旨的異姓結契。實際上劉關張之“結義”就是結社或結黨,《水滸傳》中寫到的大小聚義亦大率如此,其核心內涵是將公義與私誼捏合到一起。雖說結契的習俗在中土由來已久,甚至往往被人追溯到《周易·系辭上》的“金蘭”之言,但正史中很少記錄這類事例,尤其是具有明確宗旨的結契活動。秦漢之際,劉邦、項羽短暫的盟約關系可以說是一個少有的例子。太史公記昔楚漢爭霸,對峙廣武之時,項羽捉了劉邦老父欲置俎上活烹,劉邦不為所動,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項羽本紀》)其謂“約為兄弟”,與結契庶幾同義。但劉關張之結義,顯然不同于劉備的祖上與祖上的那位“兄弟”,因為劉邦、項羽各有人馬,只能是對等關系(對等就容易演化為對立乃至互掐),而劉備與關羽、張飛則有上下之分、君臣之別,劉備一開始就是老大。也就是說,盡管都是異姓結契,亦各有宗旨與內涵,但劉邦、項羽“約為兄弟”只是一時的合作,而劉關張的桃園結義作為一種差序結構,反倒更像是關系穩定的黨社組織。
所以,后世的幫會門道與民間異姓結契大抵沿循桃園結義這一模式,中國歷史上所有稱兄道弟的結契沒有比這個虛構事件影響更大的。值得注意的是,《三國演義》用“結義”一詞代替“結契”,分明彰顯仗節死義的意思,其結義之“義”是道義、節義,亦是誓之宗社之大義。這“義”之一詞既可融通上下界限,更使“兄弟”結為“同志”。(《國語·晉語四》:“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在《三國演義》中,這種結義更勝于親情,比人家親兄弟更為齊心。有趣的是,小說里寫到的親兄弟大多反倒不是同心同德。不必說曹丕對曹植“相煎何急”,不必說袁譚、袁熙、袁尚三子兵戎相見,不必說劉琦、劉琮哥倆明爭暗奪,這種兄弟鬩墻或分道揚鑣的事情,實并不限于世族閥閱子弟立嗣之爭—如,張松是暗通劉備欲獻西川,被其兄張肅告發,落得個滿門抄斬。又如,糜竺、糜芳自徐州跟從劉備,一者始終是蜀漢的忠臣,一者卻在呂蒙偷襲荊州時臨陣倒戈使關羽敗走麥城。還有一個更耐人尋味的例子,諸葛亮與其兄諸葛瑾分別是蜀漢與東吳重臣,而且他們還有一個族弟諸葛誕效力于曹魏。毛宗崗特別關注這事情,因有“諸葛兄弟三人,分事三國”之謂(第一百十一回總評)。
上述兄弟歧途之例,并非小說家虛構,均見諸《三國志》和有關史書。只是《三國演義》寫了劉關張結義一事,相應有了對照,可以見得結契義理更勝于同胞親情。奇怪的是,《先主傳》敘劉備起事之初,不提關羽與張飛,卻偏偏扯入兩位贊助商—“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貲累千金,販馬周旋于涿郡,見而異之,乃多與之金財。先主由是得用合徒眾。”陳壽以為劉備“販履織席為業”,家貲不厚,須交代招募部曲之資金來源。其實,團隊、組織、核心骨干,這些才是最重要的,有道是“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因素”。
如果將歷史理解為一個民族的共同“記憶”(抑或包括共同的“想象”),被認為是文學作品的《三國演義》之敘史意義,實在是甚于《三國志》。
當然,不要真以為劉備與關羽、張飛就是“兄弟”。在劉備心里,他倆只是“手足”與“股肱”,有如棋局上的車馬炮(參見拙文《劉備說“妻子如衣服”》)。小說第二十一回,劉備在獻帝衣帶詔上簽名,參與誅曹密謀,如此重要的事情卻未告訴關羽、張飛。當時劉備行韜晦之計,在下處后園種菜以為掩飾,他這兩位兄弟還蒙在鼓里。書中寫道:“關、張二人曰:‘兄不留心天下大事,而學小人之事,何也?’玄德曰:‘此非二弟所知也。’”
劉備明說了,你們不懂。老大與馬仔之間,亦以上智下愚為界限。煮酒論英雄一節過后,劉備為尋脫身之計,以截擊袁術為由率軍出征,星夜收拾軍器鞍馬,匆忙起程。他騙過了曹操,也弄得關羽、張飛一頭霧水—“兄今番出征,何故如此慌速?”這幾乎是倉皇出逃,劉備的算盤還留在自己腦子里,不肯向他倆交底。他是老大,他可以隨便指揮那兩桿槍。
其實,關羽與張飛不同,此公實非粗人,雖說“剛而自矜”,卻是有勇有謀,心思縝密。《三國演義》塑造其人,還添加了讀書人的儒雅形象,書中一再出現關羽夜讀《春秋》的情形,(《關羽傳》裴注引《江表傳》曰:“羽好《左氏傳》,諷誦略皆上口。”)而張遼則當面贊許關羽“兄武藝超群,兼通經史”。如此說來竟是文武全才。不管怎么說,他可比劉備有文化。《先主傳》說劉備“不甚樂讀書”,小說里更不見劉備碰過書卷。以關羽這樣的性格與素養,在這三人幫的兄弟格局中似乎難以自適。
劉備誥封“五虎將”一事,關羽就極為不滿。表面上是沖著黃忠發飆—“黃忠何等人,敢與吾同列?大丈夫終不與老卒為伍。”其實,拿黃忠說事兒很沒有道理。論武藝黃忠幾乎不在他關羽之下,當初戰長沙陣前斗一百合,關羽絲毫沒有占到便宜。“黃忠老將,名不虛傳。”這是他自己的心里話。后來再戰,雙方都手下留情,也算留下一段佳話。再說劉備進軍西川、漢中,黃忠戰功卓著,定軍山斬夏侯淵一幕,完全就是他關羽斬顏良的翻版。關羽這是要抱怨什么呢?書中沒有說。
第七十三回中,東吳欲聯手關羽共破曹操,派諸葛瑾來為孫權之子求婚,關羽竟甩出“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這番狠話。東吳找上門的親事不是第一回,關羽自然不會忘了孫權之妹曾嫁與劉備。罵孫權是“犬”,未必是指桑罵槐,卻拐彎抹角有意無意捎帶上劉備。毛宗崗夾注中一語挑明:“玄德曾配孫夫人矣,是虎兄而配犬妹也;孫夫人為公之嫂矣,是虎叔而有犬嫂也。”這話或有些過度解讀,但關羽拒親至少說明,就眼界、心氣而言,他不自覺中也有些傲視劉備。當然骨子里更是蔑視孫權。
當初諸葛亮入川時,將荊州托付給關羽,留下“北拒曹操,東和孫吳”八個字,而關羽終是未將“東吳群鼠”當回事兒。第六十六回單刀會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魯肅獻計在陸口江亭擺下宴席,請關羽赴會,企圖逼其歸還荊州。這分明是鴻門宴的招數,關平、馬良亟勸關羽切勿赴會,關羽卻滿不在乎,有謂:“昔戰國時趙人藺相如,無縛雞之力,于澠池會上,覷秦國君臣如無物,況吾曾學萬人敵者乎?”他不僅做廉頗,還要做藺相如,是要將國家擔于一身。如此以古人自況,可見一副睥睨千古之傲氣。這單刀會一出,完全成了關羽的個人秀場,從席間談笑自若到手提大刀將魯肅扯到船邊,一身英雄之氣表現得淋漓盡致。
先是身陷曹營,再是千里走單騎,這回又是獨守荊州,關羽的故事多半發生在與劉備、張飛暌隔之際。孤獨中的聚焦凸顯了關羽個人的雄邁豐采,似乎也擺脫了結義三人幫的差序結構。當然,沒有證據表明關羽已對劉備懷有二心,事實上他始終努力維護自己的忠義形象,絕不會逾越君臣界限。不過,事情也許有一些微妙變化。以劉備為效忠對象,自然最終是效忠作為“國家”的漢室;而內心這個終極目標有時會繞開劉備這個“中間物”,直接向他發出召喚。
第七十五回中,關羽水淹七軍,擒于禁,斬龐德,威震華夏,即率軍圍攻樊城。按關羽的計劃,“取了樊城,即當長驅大進,徑到許都,剿滅操賊,以安漢室”。消息傳到許都,曹操大為慌亂,一度想要遷都。當然,這不是劉備、諸葛亮的戰略意圖。倘若關羽長驅奔襲,拿下許都或有可能,但絕不可能給曹軍以毀滅性打擊,反倒在中原深陷重圍。而一旦傾力北上,荊州必然落入東吳之手。由于自己身中毒箭,隨后呂蒙偷取荊州,關羽眼前的戰機便稍縱即逝。書中沒有寫劉備、諸葛亮對關羽“長驅大進”的計劃做何反應,因為關羽沒有向成都匯報自己的意圖。等到荊州的消息傳來,一切都晚了。
孤獨的英雄需要抓住內心的絕對意志。關羽說:“吾與吾兄桃園結義,誓共匡扶漢室。”這是亮出政治底牌,他強調的是一種終極信念。關羽說:“荊州本大漢疆土,豈得妄以尺寸與人?”當著諸葛瑾唱白臉,他說的卻是真話。言談謦欬都是大漢忠臣的范兒,顯然他本人也國家化了。關羽說:“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這也是真話,既然“國家”已經從劉備身上移植到自己信念之中,他當然可以自行裁奪。孤獨的英雄獨往獨來,至少可以在想象中恣意而行。
在陳壽的三國敘事中,關羽不能說是一個被特別關注的人物,《蜀書》是將關羽與張飛、馬超、黃忠、趙云數傳合為一章,其事略竟不如姜維、法正等人詳盡。然而,在《三國演義》中關羽卻被塑造成忠勇節義之集大成者,成為影響最大的正面人物。小說家對關羽的重視自有歷史原因,自北宋末年起,朝廷對關羽的敕封接踵而至,大抵是“國危思良將”的意思。但此中因素很復雜,民眾的尊崇另有原因,也許要從“道”、“義”兩面尋之。
民間對關羽的祭祀應該更早。本文作者無以考證這種祭祀起于何時,以及最初是否屬于“淫祀”之類。然而,自元雜劇三國戲和《三國演義》問世之后,文藝作品塑造的形象顯然又影響了民間祭祀與官方敕封,這種互動關系可以作為一個研究課題。
三國人物中唯獨關羽死后成為神,成為“關圣”與“關帝”。據說,明萬歷二十二年,朝廷從道士張通元所請,關羽晉爵為帝,廟曰“英烈”。四十二年,又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圣帝君”,自是相沿有“關帝”之稱。明清以后各地大興廟祠,關帝崇拜赫然為盛。身前為人臣,死后卻稱帝,這事情確實很有趣。相形之下,當年的老大卻顯得落寞,劉備好歹正式做了皇帝,后世未以“劉帝”見尊,亦鮮有祭拜。
關羽被奉祀似有多種理由,從道德形象到相貌體貌,此公都是國人極喜愛的一路。“丹鳳眼,臥蠶眉,面如重棗,唇若涂脂,且身長九尺,髯長二尺。”這形象在舊時年畫上看著很是威武持重,儀態儒雅又透著幾分嫵媚,甚至青龍刀、赤兔馬、黑周倉那幾件伴當也都洽洽入畫。忠誠者變成了膜拜的對象,這個對象化過程可以說是一種審美選擇,也可以說是國人集體意識之確認。重要的是,關羽不僅有著忠勇節義的完美形象,而且具有“剛而自矜”的個性—不要以為這個民族的性情都湮沒在家國話語的集體意向之中,以評騭歷史人物而論,國人眼里注意的首先倒是某種超凡個性(從伯夷、叔齊到屈原,從“竹林七賢”到“戊戌六君子”)。在皇權、風教和政治倫理的禁錮中,逮著機會放肆一把也是生命亮點,誰說不是?
“神威丕顯”、“大義參天”之類是碑文上的濫詞,返照于國民精神深處也許是另一套話語。譬如,怎樣才是真正的牛范兒,如何將隱忍克制與任性使氣集于一身……諸如此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