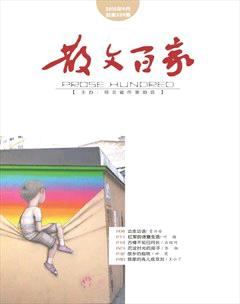風 匣
●王金平
我回老家清理房屋,意外地發現了一只風匣,蜷縮在一個堆滿雜物的角落里。它滿身塵土,底部出風口糊的馬頭紙也已脫落。
它是一只黑色的風匣,人們大都叫它風箱。長方形箱狀,箱體是梧桐木,性軟、不裂、耐磨、輕便。酸棗木拉桿,柔韌堅硬。拉桿一頭在箱體前側,連接一推拉手柄;另一頭立著一塊長方形木板,為了不漏氣,木板四周用牛皮筋箍一圈雞毛。箱體前后兩面,各留一個搭調活門,樣子像小窗口。隨著桿的前后推拉,兩頭的活門一開一合,并發出呱嗒呱嗒美妙的響聲,產生的風通過風道送出。
這只風匣在這里閑置30年了。當初,一只風匣、一座爐灶、一口大鐵鍋,成為農家必備的炊事用具。它們像同胞兄弟,相互不能分開,否則就會使農家的日子變得支離破碎。
那時,爐灶里能燒的柴火有很多種:割回的茅草、耬來的樹葉、砍下的樹枝、刨出的樹根,還有荊柴、土強、圪針和秸稈,光莊稼的秸稈就有好多。麥秸、玉茭秸、高粱秸、芝麻秸、豆秸、稻草、瓜秧、豆角秧,凡是枝枝草草,都能燒。像樹葉、茅草、稻草和麥秸一類,暄,呼隆一下就完了,也留不住底火,用風匣也是輕拉慢推,否則,吹起的灰到處飛揚,或者干脆就不用風匣。好多時候,這些樹葉草秸都用來做引火。那些芝麻秸、豆秸就不同了,風匣一拉,著起來很旺。
燒火拉風匣時,一般都坐個小板床(同小板凳)。往往怕拉錯了位,右手拉的同時,右腳還要抵住風匣。左手朝灶膛里添柴火,時不時用燒火棍捅一捅爐底中間的出風口。夏天怕熱,坐的小板床盡量離灶口遠些;冬天總是面對灶口,火光一照,滿臉通紅,渾身暖和。由于拉風匣是一拉一推,所以身子也就一仰一合加上呱嗒呱嗒的風匣聲、呼呼的風聲,不一會兒,就使火苗一竄一竄、來回跳動。
聽娘說,我家一開始是沒有風匣的,掏2塊錢,租用本家來栓叔的一只,租用了四五年這只風匣光呱嗒呱嗒響,可就是不出風,想必是拉板上的雞毛該換了。印象中,我還拉過這只風匣。后來,我家找木匠打了一只,娘在拉板周圍綁了一圈厚實的雞毛。風倒是不小,可弄得風匣沉重得拉不動。做飯時,娘總喊我們去幫忙。我們雙腳抵住風匣、雙手攥住拉桿,無數次地把自己推拉成一張弓,即使在深冬,也累得滿頭大汗。為了減輕阻力,娘拆開風匣,卸下些雞毛,又在拉桿上打了石蠟。
享盡呵護的風匣,巧妙地掌握著火候,讓我們的一日三餐變得有滋有味。
每年臘月二十五一過,家家的風匣就更忙活了。打豆腐、打年糕、蒸菜包、蒸饅頭……這與平時不大一樣,要用耐燒的柴火,呱嗒呱嗒猛拉一陣,待到大鐵鍋里水開,風匣聲才變得遲緩,可生出的風格外的大。那風匣聲,就像一個人穩健的朗笑,傳出很遠,播送著山里人一年的喜悅。這時,木板鍋蓋上熱氣騰騰,糧食的香味兒四處彌漫,連在街里走的人都能聞到我們那些孩子,嬉笑著圍在一旁烤火,其實是在等待要出鍋的年糕。熟食晾涼后,擱進一個大缸里用撇撇(用高粱秸縫制的蓋子)蓋住,除了走親戚,直吃到正月十五。
這時的風箱涌動著甜美祥和,渲染著濃濃的年味。
拉風匣是有竅門的。在拉風匣時,為了省勁兒,要把風匣桿緊靠風匣圓孔的下方,這樣推拉就有了依靠。如果在圓孔上下咣當著,會很費力。拉風匣講究快慢緩急,一般是快拉慢推,長拉短放。
有經驗的人,能從拉風匣的聲音里,判斷出拉風匣人的脾氣性格和年齡。勻長緩慢的,會是經歷了世態炎涼年事已高的奶奶;均勻有力的,一定是堅韌辛勞的中年主婦;急迫短促的,肯定是毛糙小子。
日出東山坳。當太陽格外清晰地照在參差錯落的石頭房上時,乳白色的炊煙便從煙窗口升起來,氤氳飄悠,一路尋找云彩。一家挨一家,炊煙籠罩了整個山村。走在街道上,呱嗒呱嗒的風匣聲不斷從院落里依稀傳來,更加顯示出深山村莊的清靜。
夕陽西下。波浪似的西山山頂,布滿了彩色晚霞,風匣聲又從朦朧的薄霧中傳來,裊裊炊煙從各家的紅石板房頂上緩緩升騰開來,空氣中便流淌著淡淡的柴草煙味兒,這味道幾乎是一種天然的清香。時而,傳來叫孩子吃飯的呼喚,聲音悠遠而嘹亮。
娘說,一只好風匣能用一輩子。
呱嗒呱嗒,風匣聲動聽而有節奏。一手拉風匣,一手添柴火,還要用燒火棍通透風口,還要照顧鍋里的、鍋脖上的。風匣,把灶間燃燒得紅紅火火。
這一切,都深深刻進了我的腦海,以致現在我依然認為:從前的山村,才是真正的山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