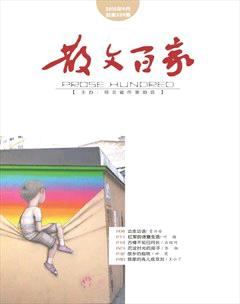夢縈老宅
●吳 筱
路,還是那條路,只是多了水泥的灌注。很小的時候,端坐在三輪卡車里,一路顛簸,在泥濘中行進著。喜歡從三夾板的縫隙里探看出去,一邊是青綠的田地,一邊是裸露巖石的山林。無論是哪種,總歸都沾染著鄉間的氣息。淡然地、肆意地,結下一段永生不隱的緣。
卡車的聲響停息了,我想我該下車,去找尋老宅的蹤跡。不用引導,不用回憶,只需憑著感知,拾級而上。抬頭是青山的環繞,循著云霧的氤氳,好似走向了塵世的結局。沿路,溪澗潺潺,雞鴨成群,還有牛棚里的牛不時發出哞哞的叫聲。近了,近了。為何有種紛亂的心緒在作祟,彌散了先前的欣喜?該是在害怕吧,害怕即將出現的不再是記憶中的模樣。依舊是念念不忘的老宅,只是平添了幾分古意。
三進平房大且深。房前的庭院很大,是最原始古樸的狀態。泥土放肆地裸露著,零碎的是縫隙里的花花草草,頑強固執地生存著。我努力追想自己在這片庭院里的往事,盡力在腦海中進行著速寫。院子左側有一個大水缸,是那種體積很大的容器,瓷的質地透露著厚重與沉淀。描摹出一個孩子的輪廓,蹣跚而來,從屋內拽著棉鞋使勁地丟進水缸,游曳幾圈,再撈出來曬開。是不是不小心驚動了流年里的觸角,就這么沒有預期地鋪成展現?一度以為自己早已隔離在喧囂之外,卻不曾想可以毫不經意就觸碰到唯美的章節,留白須臾間蘇醒。孩子臉上的微笑映襯著冬日里的暖陽,分明是滿足的幸福。想起自己還身處夢境,卻為何景致如此清晰?該是每一次的醞釀都雕刻在時光里,瞬間,細琢成年輪,點點圈圈。天很藍云很低,我坐在藤椅上仰望靜謐。黃昏時分,炊煙裊裊升起,伸出手采摘到一抹布帛的柔軟。其實,可以算是在山間,站在庭院中眺望,是蒼茫的遠海,間或傳來汽笛船鳴。轉身,云霧籠罩著綠樹青山,飄飄渺渺,猶如仙境。不愿去回想,從前的從前,祖父母在這里看盡了多少我們的離去,又留下了多少不舍的嘆息。漸漸釋懷,只留微微的疼痛縈繞心底。
臥室的窗戶很別致,木板加玻璃的組合,可以移動,也可以搖轉。夏季,入夜,打開木板,關上玻璃窗,讓月光灑進屋內,浪漫溫馨。入眼是一張做工精細的雕花木床,吟唱著舊日時光,沾染出熟悉的意味,追隨至今。更多的時候,還是喜歡躺在后面的小床上,只因正上方有一個天窗,透明的玻璃瑩瑩發亮。觀星抑或看雨,聽滴滴答答吹送入夢。我喜歡玻璃窗里的那層木啟,喜歡貼在墻壁上的精美年畫,喜歡木質的舊時被柜,喜歡一根線控制的電燈開關;我喜歡只收得到一兩個頻道的十四寸黑白電視機,喜歡散落在房間各個角落里蒙著灰塵的書籍,喜歡床后米缸里滿滿的大米,喜歡四方桌抽屜中精致的飾品。還有很多很多,可以不用停頓,無需刻意,就這么一股腦兒地悉數出來。原來,一切的一切都已永久地印刻進生命里,一旦剝離,就連呼吸也開始變得急促。
一定要好好走一走老宅的廚房,即便只是在夢中。不是水泥地,有凹凸不平的坑坑洼洼。大水缸在碗柜下方,我還是像小時候那樣期冀著水缸姑娘的突然光臨。房間很暗,風箱呼呼地拉動,點旺灶膛里的火,照亮整間屋子。燒火用的柴多是外祖母采來的松樹枝,松果在烘烤時噼里啪啦作響,好似彈奏一曲歡快的歌謠。剩下來的炭灰大都摻入灶臺邊的瓷缸中,常年焐著一瓦罐,或粥或湯。最喜歡肉粥,那種香無法形容,以后再也未曾喝過那么美味的肉粥,不只是口感,更因為外祖母深深的疼惜。是家的味道,是親情的羈絆,不用經營就立時滿溢。
夢境的時限來臨,我從夢中醒來,悵然若失。獨自經歷風雨、跨越千山萬水的剎那,身處千里之外、滿眼陌生風光的須臾,便會不止一次地想起老宅,想起如水年華里那些永不被侵蝕的感動和思念。若是可以,找一個時間,回去老宅,潛心夢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