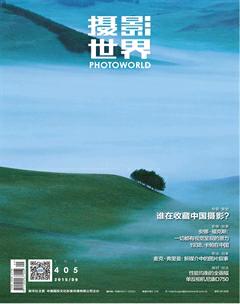這不是一部辭典—任悅談她的《1416攝影辭典》

這個標題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比利時畫家馬格利特的作品《這不是一只煙斗》,在那幅奇怪的畫中,馬格利特迫使觀者重新思考詞語和圖像的關系,讓一些約定俗成的關聯變得動蕩起來。
《1416攝影辭典》不是一部辭典,這就好像“1416教室”也不是一間教室一樣。但是,如果拋開我們腦中舊有的有關“辭典”和“教室”的想象,這本書就是一本辭典,而“1416”也同樣能夠成為一間教室。
1416是我上大學時一間教室的名稱,當初坐在這間教室開始上攝影課的時候,我對攝影的認識是一片空白。9年前,博客流行的時候,我將之作為博客的名字。我希望保持這種空白的狀態,因為它能帶來更多的渴求,更大的好奇心。最重要的是,在這里,攝影是一個個疑問,我的每一次寫作,都是一次出發去探險,我的全部努力是將這些疑問變成陳述。
攝影有種包容一切的感覺,這是它吸引我的原因。不過,很快我就發現這里存在一個悖論,因為圖像本身是不能言說的,所以,如何“寫攝影”就成為一個問題,也是攝影人不得不面對的尷尬,這也正是馬格利特在其“煙斗”作品中巧妙顯示出來的——詞語和圖形是兩個世界以及兩個軌道。很多時候,我們并未真正去“看”,而是用詞語束縛了形象。
當我們在談論攝影的時候,我們可以談論什么。用文字復述攝影的畫面以及熱衷生成圖像的技法,都不是我的興趣。因為前者是不可言說的,后者則并未有太多玄妙。就拿肖像來說,其拍攝秘訣在哪里?有人認為人像攝影領域的女王安妮·萊伯維茨(Annie Leibovitz),她的成功關鍵在于大成本大制作,但實際上其最好的照片都是年輕時候拍的;英國攝影師大衛·貝里(David Bailey)也閱人無數,他認為唯有那些只身前往其影室的大人物,才會讓他拍得好照片。很多畫框之外的事物,甚至是攝影師所不能操控的偶然,決定著攝影的成敗。
在9年的寫作之后,我似乎真的擁有了一部辭典。我從兩千多篇博客文章里選出367個詞條,它們在建構一個任悅所理解的、攝影的世界,同時可能也在拆解大眾慣常所認為的攝影世界。在這里,熟悉變得陌生,陌生卻可能會被引入當做熟人。在談論布列松的時候,我更好奇的是他家工廠生產的毛線,這并非八卦,而是因為這一社會身份潛在影響著布列松的觀看。我的詞條里收錄了很多和攝影不相干的人,他們是數學家、科學家、詩人、作家,我認為這些異類之所以不被接納,是因為我們的邊界不夠開放,并反而在攝影技術越來越民主的時候建筑高墻。
讓我編制這樣一部辭典的原因,是因為我將攝影視作一種人人都需掌握的新語言,一種獨特的視覺文化實踐——不但響應著特定的社會文化,同時也因其強大的(且越來越強大的)傳播力,影響并介入到社會文化之中。從這個層面講,技術、風格、歷史、當下都可以融合在一起。我們可以從印在錢幣上的林肯肖像出發,談及照片的拍攝者馬修·布蘭迪(Mathew Brady),作為一個技藝精湛的早期照相館師傅,他卻因為一個雄心勃勃的商業計劃參與了早期戰地攝影的實踐,布蘭迪和林肯的關系幫助他記錄南北戰爭,而他的照片則成就了一個總統,通過這個我們興許又可以談談影像和宣傳的關系。如果這本書讓你感到攝影相當有趣,那并非是我將攝影變輕松了,而是因為它幫你看到攝影的更多層面,這家伙就在你的生活里面,無需在旅游的時候才想起。
這本書從布列松的“一本小藍書”開始,到澤德·尼爾遜(Zed Nelson)的《槍支國度》,完成了從A到Z的所有詞條,這其中沒有讓讀者感到親切的分類,人像、風光、紀實……反而連接了各種毫不相關的詞匯。我喜歡偶然和奇遇。就好像有一段時間去圖書館看書,因為并非是要去看“某本書”,我就隨便從書架上抽出一本來看,總會有一些不期而至的結果。我希望用這種“無組織無秩序”打破人們對攝影的刻板成見。
《1416攝影辭典》除了辭典部分,還有一間“麻辣教室”,在這個篇章里面,我用“如何做”“為什么”“讀書”“家庭作業”這幾個小篇章構建了一個虛擬的教室。這些內容其實也來自1416博客和現實世界的連接。隨著我的寫作進行,我和讀者的互動也多了起來,我們一起做了很多在傳統課堂上沒有的攝影實踐,嘗試一種不同的攝影教育。我們曾一起討論如果去太空只帶十張照片會帶什么;我們對家庭相冊展開觀察;“北京回龍觀項目”是對城市超大社區的記錄,“還鄉計劃”是對故鄉的審視。我一共做了20個攝影幻燈放映會,參與過這個活動的攝影師應該還能回憶起現場的氣氛,尤其是里面出現的各種爭論的聲音。這間教室并非只是黑板上的言論,而是一個行動的文本。
在今天這個到處都是攝影的世界里,我們更應該思考攝影和我們的關系。從“PS”到“挪用”,這無疑是一部當代的攝影辭典,但談及這些復雜的當代文化現象,我不想用“后現代”、“后殖民”、“后媒介”這些拗口的學術辭藻,在這本書里,我只想用一個孩童的眼光去看攝影,我最希望的是,你能讀著這本書笑起來,更不妨將之當成我給各位讀者的一套樂高玩具,你可以用之搭建自己的攝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