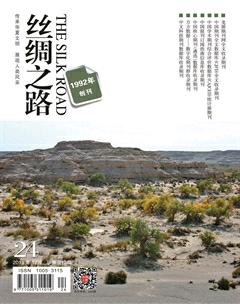張掖寶卷
文圖/本刊記者 楊文遠

蒼涼悠遠的《河西走廊之夢》是紀錄片《河西走廊》的主題曲,由音樂大師雅尼譜曲,歌曲彰顯了河西走廊與華夏文明厚重綿長的歷史感。片曲雄渾古樸、遼遠曠蕩。聞聽此曲,如同游走在狹長的河西走廊,馳騁于西部的廣袤河山。這讓人不覺聯(lián)想到河西走廊曾經(jīng)喧囂繁盛的古樂舞,僅敦煌壁畫中就繪有3000余身樂伎和數(shù)千件樂器,久遠的《佚名·匈奴民歌》、漢朝的《文康伎》、西魏時期的《安國伎》、隋煬帝時期的《康國伎》等,皆源于張掖舞樂。為此,我曾寫過《焉支悲歌》、《八聲甘州》等有關(guān)張掖舞樂的小文。
在此,我想約略敘寫流傳于民間的張掖寶卷。
寶卷是從佛教的俗講發(fā)展來的,是變文的嫡傳。河西寶卷則是在唐代敦煌變文、俗講以及宋代說經(jīng)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而成的一種民間吟唱的俗文學(xué)。河西寶卷是活著的敦煌俗文學(xué),從其可以進一步認識敦煌變文的特質(zhì),也是研究中國民俗文化史、中國民俗文學(xué)史的珍貴資料。另外,河西寶卷也是一種帶有宗教色彩的通俗文藝。
河西地區(qū)地處戈壁大漠,古時交通不便,天災(zāi)人禍頻發(fā)。在這樣的社會環(huán)境下,寶卷作為河西人民的精神寄托和文化娛樂載體,歷經(jīng)數(shù)百年而不衰,實屬罕見。
寶卷真正成熟、盛行于明清時期,是漢族民間宣講宗教教義的說唱腳本,說唱者多為出家僧尼,其內(nèi)容包含儒家、佛家、道家等經(jīng)典,并有大量非宗教的歷史人物、民間神話、傳說和戲曲故事。其中,以佛經(jīng)故事、神話傳說居多,也有懲惡揚善、忠孝仁愛等主題。講唱地點多在戲院、廟會、村鎮(zhèn)等地。
在《金瓶梅》一書中,曾多次描寫了西門慶家中請道姑或尼姑宣唱寶卷的情景,這說明,在明代中期,民間說唱文學(xué)“寶卷”已經(jīng)發(fā)展為當時社會一種非常普遍的文藝娛樂活動。
寶卷在河西流傳面很廣,涉及幾十個縣區(qū)。其傳播方式主要為文字傳播和口頭流傳。寶卷的篇幅普遍較長,最短的有幾千字,最長的達數(shù)萬字。
2006年,河西寶卷經(jīng)國務(wù)院批準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名錄”,2007年,酒泉肅州區(qū)農(nóng)民喬玉安被命名為河西寶卷的國家級代表性傳承人。張掖山丹東樂鄉(xiāng)大橋村和甘州花寨村先后成立河西寶卷傳習所。
張掖寶卷是河西寶卷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以前的臨澤、甘州農(nóng)村最為流行,它作為老百姓的一種精神寄托和文化娛樂,影響頗深。現(xiàn)張掖民間保存的寶卷大致有以下幾類:一是反映佛教等內(nèi)容,如《觀音寶卷》、《何仙姑寶卷》、《唐王游地獄寶卷》等;二是歷史故事、寓言類,多反映社會生活,如《丁郞尋父寶卷》、《金鳳凰寶卷》等;三是民間神話傳說故事,如《天仙配寶卷》、《孟姜女哭長城寶卷》等。
張掖寶卷的基本形式為散說和韻文相結(jié)合。散說部分一般交代故事的時間、地點、人物、經(jīng)過等。韻文部分則主要重復(fù)散說部分的故事,句式以十字句為主,且有一定的平仄韻律。散說和韻文之間進行過渡的時候,會增加一組明確曲調(diào)的唱詞。韻文雖在重復(fù)散說內(nèi)容,實則是在細講,是寶卷內(nèi)容的核心部分。
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刊于張掖的《敕封平天仙姑寶卷》刻印本又名《仙姑寶卷》,是根據(jù)臨澤縣板橋鎮(zhèn)一帶民間尊奉的女神平天仙姑神話故事編輯而成,臨澤縣博物館就收藏有一件木刻的《仙姑寶卷》,為康熙三十七年木刻本,據(jù)說是從板橋鎮(zhèn)東柳村征集來的。2014年1月,《絲綢之路》雜志社赴張掖采風團一行,曾在臨澤縣博物館實地了解考察過《仙姑寶卷》概況。
在驃騎將軍于河西征討盤踞邊外的渾邪王期間,曾有紅衣婦人指揮向?qū)В羧ゲ〈筌娪蓸蜻^河,霍去病征戰(zhàn)勝利后,奏請漢武帝為其請功。紅衣婦人的尸體埋在板橋仙姑廟,據(jù)史料記載,古代曾掘出“敕封平天仙姑”鐵牌。仙姑的感人事跡世代相傳,在河西人民的心目中發(fā)展成為具有大智大勇、向善懲惡精神的“平天仙姑”。西夏時期,其被尊為“賢覺圣光菩薩”,每逢農(nóng)歷四月初八,張掖及臨近地區(qū)的漢、蒙、藏、裕固族的人都會前來拜謁仙姑廟。由此形成了著名的民間文學(xué)念卷——《仙姑寶卷》。《仙姑寶卷》是張掖土生土長的一部寶卷,講述仙姑修行、得道、顯靈、懲惡揚善以及在黑河上修橋的傳說故事。《仙姑寶卷》刻印后,刻本和根據(jù)刻本的手抄本便在社會上廣為流傳。
除木刻本《仙姑寶卷》外,張掖民間有許多根據(jù)木刻本抄錄的手抄本。而在張掖流傳的寶卷中,大多是來自于民間的這種手抄本,如甘州花寨鄉(xiāng)發(fā)現(xiàn)的《仙姑寶卷》,即民國三十年代(1941)根據(jù)木刻本手抄的。“家藏一部卷,平安又吉祥。”歷史上,河西百姓把家藏寶卷視為鎮(zhèn)宅之寶與神圣之物,把抄寫、贈送、收藏寶卷視為行善積德之舉,這可以說是寶卷代代流傳的根本因素。
關(guān)于河西寶卷、念卷能夠存在并得以傳承的緣由,一些學(xué)者也作過探討、分析,他們認為,清政府對民間宗教鎮(zhèn)壓極為厲害,而河西地區(qū)的民間宗教卻幸運地躲過了這場劫難,故民眾對依附于民間宗教活動的念卷有了一種敬畏感,這種活動又滿足了民眾教化和信仰的需求。另外,河西廣大農(nóng)村地區(qū)文藝活動貧乏,老百姓經(jīng)濟貧困,外來曲藝、戲曲難以供養(yǎng),而念卷這種簡便的說唱文藝在民間易于普及;再則,為了行善積德,一些有文化的人也樂于傳抄和編寫經(jīng)卷。
張掖寶卷在張掖民間源遠流長,深受老百姓喜愛。寶卷雖通俗,卻寄托著人民群眾最質(zhì)樸的情感,從而使得這種通俗易懂、寓教于樂的活動深深植根于鄉(xiāng)間村落,并世代相傳。不管是在夏日的濃蔭下,還是在冬天的熱炕上,村民們?nèi)宄扇海踔翈资畟€人聚成一團,津津有味地聆聽著寶卷。念卷人念到一定的“接口”上,聽眾們還會不約而同地集體朗誦或合唱,其情景莊嚴而活潑,不僅使寶卷成為一種簡樸實用的娛樂活動,還使人從中受到一定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