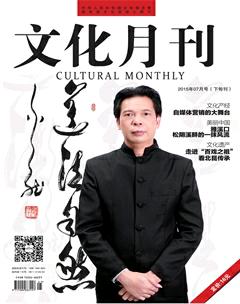歷史的花朵當下的芬芳
葉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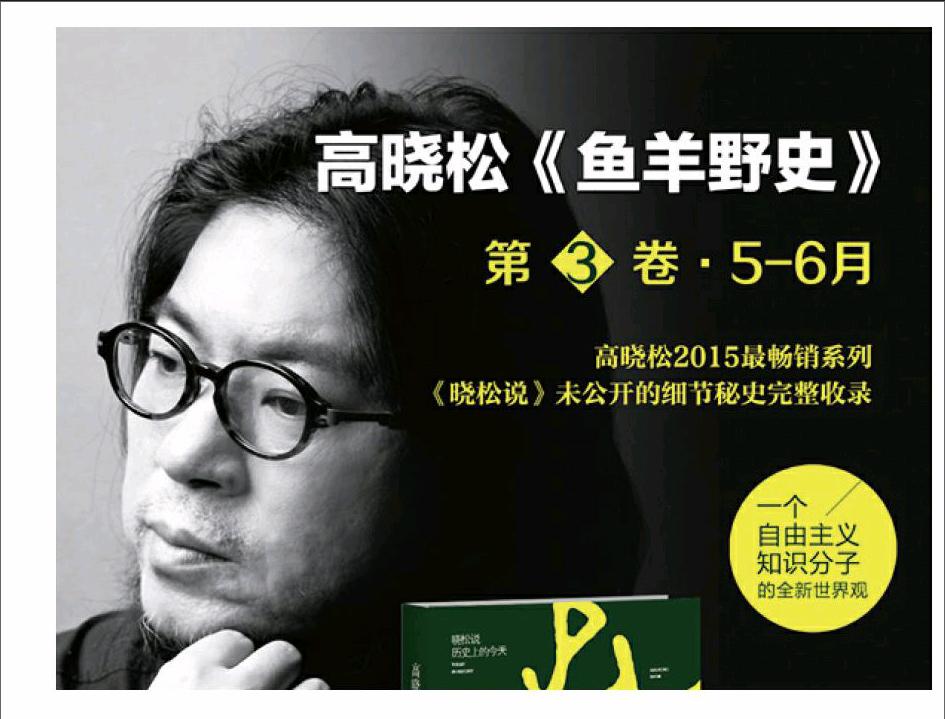
早晨的花,黃昏就落了 ,時間短暫。歷史也一樣,當年的風云,轉眼就成了“歷史上的今天”。早晨的花,有的嬌艷欲滴,有的沁人心脾,有的透著冰涼的滋潤,有的也散發著難聞的異味。歷史上的今天,有的時候是故事,有的時候山重水復疑無路,有的時候柳暗花明又一村。是否朝花夕拾,憑的是一種心境,拾起來有什么味道,靠的是一種意境。是否重溫歷史,憑的是一種情懷,怎樣打扮歷史這個“小姑娘”,靠的是一種見識。
泰戈爾說:“天空沒留下翅膀的痕跡,但我已飛過。”朝花已過,盡管“暗香盈袖”不再,然帶著想象的夕拾,依然會“拂了一身還滿”。歷史是開了又落的花,你可以無聞無知,可以熟視無睹,但如果重溫故國、故城、故人的芳華剎那,卻依然可以神往那風中飄落的片片花瓣,感受到魚羊混燉的那一勺鮮味。高曉松的《魚羊野史》,盡情發揮“野史”的張力,或當作老大媽來整容,或當作小姑娘來打扮,但宗旨依然是“讀史使人聰明”,讓人類進化。
毛澤東主席曾說:“ 《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謂野史也大半是假的”,但是,我們還必須要“扎扎實實地把二十四史學好”、“過去所謂的稗官野史也要讀”。“史”只要一“記”,就難免夾雜記述者的私貨,就少不了野史的成分。也正因為此,歷史才會鮮活, 《三國演義》才會比 《三國志》流行。單純編輯一本“歷史上的今天”,遭遇或許就會和高曉松的電視脫口秀節目《曉松說》一樣,“司空見慣的歷史內容,毫無精彩之處”。
然而,不形而上學,己來搞一套歷史,而是將功夫放在“記”上,將節目中未公開的“野史”和盤托出,悉數古今歷史、中外文化,侃侃而談文學、哲學、電影、音樂,書籍《魚羊野史》便立馬登上暢銷書榜,創下百萬冊的銷量。盡管高曉松說不辨是非,按“天”索驥,呈現“不整容、不化妝、素顏的歷史”,實際上,高曉松卻在“猜”上下足了功夫,猜當下的歷史所需,臆造動機,讓歷史照進現實,再次散發意味悠長的芬芳。
我們不妨以《魚羊野史·第3卷》為例。比如,近年來,國人糾結于國家假日辦的放假安排,高曉松說“五一”國際勞動節,便將重點放在了美國這個“五一”勞動節開始的地方,放假慶祝不是在“五一”這一天,而是每年9月的第一個星期一。由此,進一步拓展美國的節日放假制度,“基本上都是在某月的第一個星期一、最后一個星期四之類的”,正好湊成一個長周末,不用每年由“國家假日辦公室”來調整節假日。
又如國人不可能忘懷的“五四”青年節,高曉松不是將重點放在了“五四運動”本身,而是聚焦當下熱議的大學精神,并用哈佛大學門上寫著的“你進了這個門,就是為了讓國家相信真理”來激人思考。5月4日這一天,高曉松還濃墨重彩地說了“鐵托去世”,只是將落腳點,也放在了面臨民族分裂勢力威脅的今天,多民族國家“是靠經濟、法律、教育,而不是靠軍事或威權強行融合在一起”,并以新加坡為例來進一步佐證。
嚴格考據分析歸納立論的“高大上”歷史,是“業有專攻”的那些所謂的歷史學家的事情。盡管高曉松被譽為“音樂、影視、文藝三棲才子”,但這樣的重任,他也是無力承擔的。實際上,他也不愿意承擔,因為高曉松追求的歷史,“不是鏡子,而是精子”,不是簡單地鏡鑒,而是要力圖找到“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基因。所以,他“無門無類,凡舉政治、軍事、科技、文藝、體育甚至天文地理古董迷信,信馬由韁”,魚羊雜交,產生新的基因,才有“鮮”味。
歷史只有照進現實,才能煥發新的芬芳,才能生長智慧、啟迪青春。基于現實追問歷史,不僅需要歷史眼光的深刻,更需要世界眼光的廣闊。《魚羊野史》的市場成功,正是因為高曉松不只是將歷史作為現實的參考,拋棄了簡單化的影射,而是跨學科、跨時空、跨地域地穿越揉融,將一天一天的歷史小插曲,雜交成化解現實糾結的藥方。其實,我們是誰?我們從哪兒來?要去哪兒?答案從來就蘊藏在“魚羊野史”之中,只是看你能否嘗出鮮味。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