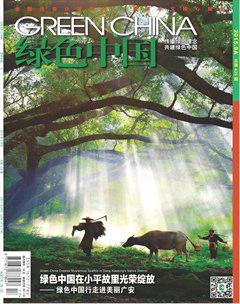白春蘭 扎根沙漠的女勞模
劉倩瑋


白春蘭是一位極其普通的農家婦女,常年在外治沙讓她擁有了黝黑的面龐,這幅面龐似乎記載著歲月的流逝,記載著治沙的艱辛。老太太今年雖已62歲,但治起沙來仍然充滿干勁,正如她所說的:“一看到這滿眼的綠色,看到樹林里活蹦亂跳的野兔、狐貍、野雞,我渾身就有使不完的勁!”
扎根“一棵樹”
白春蘭的治沙往事要從1969年說起,那年,年僅18歲的她嫁到了鹽城縣柳楊堡鄉冒寨子村。當年的冒寨子村風沙災害十分嚴重,水源極其缺乏,“一年一場風,從春刮到冬”就是當時的真實寫照。干旱、風沙經常使得莊稼顆粒無收,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很多人都吃不飽穿不暖,吃飯基本上都要靠國家的救濟,食物種類更是單一,主食只有玉米、紅薯。“我和丈夫兩個人在那個地方苦干一年,一分錢都收不上。”白春蘭說。
離白春蘭家30里的地方,周圍荒無人煙,只有一棵樹,于是大家便稱那地方為“一棵樹”。1980年,白春蘭聽說“一棵樹”的沙層淺,能挖到水,這讓一直生活在滴水貴如油環境中的白春蘭夫婦興奮不已。于是,白春蘭夫婦和其他十幾戶村民一同來到了“一棵樹”。
因地處毛烏素沙漠邊緣而得名的沙邊子村是名副其實的沙子村,這里每年有多達36?40天的沙塵暴天氣,風速超過每秒5米的起沙、揚沙大風達300多次,夏季的最高溫度更是可達50攝氏度。
惡劣的環境頓時將白春蘭一行人的熱情澆滅了大半,可白春蘭骨子里的那份堅韌支撐著她在這里種下了最初的3畝麥子。但這批麥子不是被沙埋就是被野兔吃,到了年底顆粒無收。
“這個地方,你要想種莊稼非得治沙。不治沙莊稼就種不成。”于是,白春蘭和丈夫在這干旱貧瘠的沙丘上開始了年復一年的植樹種草之路。
每天天剛亮,夫妻二人就從冒寨子村趕到“一棵樹”平沙整地。沙漠的早晨寒風凜冽,白春蘭和丈夫就頂著寒風刨坑栽樹,經常是一陣狂風襲來,剛種下去的樹苗不是連根拔起就是被沙掩埋,他們就一次次的刨揀出來再種上。
沙漠的中午又赤日炎炎,沒有樹沒有草的沙漠被太陽烤得如蒸籠般酷熱難耐,有的時候實在受不了了,他們就用鐵鍬撐起一兩件衣服乘乘涼。餓了就啃幾口干糧,渴了就刨個沙坑取水喝。
最初和他們一起來的十幾戶人家在殘酷事實的打擊下相繼回了村,但白春蘭堅信:這里既然曾經長過一棵樹,就一定能長出千萬棵樹。她斬釘截鐵地說:“別人走,我不走!我要在這兒干20年,非讓這沙坨子長出白面饅頭、長出樹林不可!”
開始的三四年白春蘭夫婦是“只有種,沒有收。”在白春蘭的記憶中,那時候每天都是風,“那些草啊,樹啊,一年載下來全部給荒沙壓了。壓了第二年開始重新再干。每一年干下來,一場大風刮過來就什么都沒了。”
在白春蘭大女兒冒珍仙的記憶中同樣如此,“有一次,父母從鄉鎮上拉來的柳條,都用塑料袋裝著,他們一棵棵地拉出去,往沙窩子里栽。后來幾場風沙過去,埋得什么都沒有了。沒有了他們就重新栽。”
白春蘭和丈夫就像愚公一樣,不斷地挖不斷地種,堅持不懈地和風沙抗爭著,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直到1984年秋,執著不屈的白春蘭終于從沉寂多年的沙漠中得到了饋贈,“當時打了四麻袋小麥。我丈夫趕著毛驢車把我拉上回到冒寨子村,他一路唱著歌,高興地說我們打了四麻袋小麥。”自此,他和丈夫更加堅信治沙能吃到白面,更能增收致富。
1987年,政府在當地實行沙漠分配到戶制度,白春蘭家分到了八百畝的沙漠。他們一家人憑著一鍬一鍬硬是壘起了一道高一米長五千米的防沙墻,可好景不長,一場大風瞬間將防沙墻刮倒,一家人六十多天的努力頃刻化為烏有,這令他們既難過又無奈。
面對這一切的困難和不理解,白春蘭的丈夫顯得十分樂觀:“咱們雖然現在艱辛一點,但是將來這里肯定比冒寨子要好得多。像我們每年都治理這個沙,以后綠化起來,這個地方一定挺美的。”“前十年叫人家笑話咱們,后十年叫人家來看。”在丈夫的不斷安慰和開導下,白春蘭最終選擇了留下。
在和風沙的不斷抗爭中,他們逐漸摸索出了一套實用有效的治沙方法,即在栽植喬木的同時,選擇適應沙地生長、防沙固沙的沙柳、沙蒿等灌木進行栽植,這樣能起到很好的防風固沙效果,就這樣,暑來寒去,點點綠色漸漸出現在了荒蕪多年的“一棵樹”中。
1989年,白春蘭和丈夫從市場上買回了第一批仔豬、羊羔和一臺飼料加工機;1992年,又推沙開挖魚塘4畝,投放魚苗數千尾,成為鹽池縣第一家沙漠養魚戶;1993年,投資1萬元,建起全縣首座農家養豬溫棚……白春蘭夫婦逐漸摸索出了一條又一條通向富裕的道路,治沙產業也在一天天地興旺起來。
沙漠雖然蹉跎了白春蘭的青春,但卻給了她豐厚的回報,而這一切離不開白春蘭科學求實的態度。
1984年初春,縣科委獎勵她家一捆優良品種的葡萄苗。雖然白春蘭十分小心地栽種照顧,可樹苗最終還是死了,并且他們在請教專家后才知道具體緣由,自此他們意識到,要想治好沙,離不開科學技術的指導。
從此,夫妻倆想方設法地參加培訓班學科學。那么多年的治沙經歷,讓這個只有小學文化的農村婦女變成了“土專家”,她曾說:“干啥事不能光靠流汗、苦干,還得加個‘巧字,這個‘巧就是學科技。”
對此,鹽池縣委常委、宣傳部長李耀強說:“科技一旦被群眾所掌握,便會產生巨大的創造力。28年來,白春蘭利用自己所學的林草栽植技術,創造了‘三行制治沙法,即以草擋沙,以柳固沙,栽植果樹楊樹防沙,既有效地遏制了流沙危害,又提高了經濟效益。這種方法,已經在鹽池縣推廣。”李部長還稱贊道,白春蘭利用三條帶子井,采取立體復合種植法,楞是在沙灘上創造出了“噸糧田”的奇跡。
沙漠中的奇跡
可生活往往出乎我們的預料,正當白春蘭一家的生活慢慢好起來時,一個噩耗卻突然降臨,白春蘭的丈夫因為過度勞累患上了肝硬化。白春蘭每天既要侍奉生病臥床的丈夫,又要照顧孩子,還要種田、喂牲口、植樹、飼魚,全家的重擔全都背在了她一個人身上,“哪個中午我就沒有睡過覺。一到中午,人家都休息,我就沒有休息過,而且一直在灘里面,基本上就是一天都在灘里面。”作為家中頂梁柱的白春蘭日漸消瘦著。
可這一切終究還是沒能留住丈夫。六年后,1997年的深秋,和他朝夕相處并肩在沙漠中苦戰,年僅47歲的丈夫冒賢永遠地離她而去。
丈夫去世后,很多人都勸白春蘭把這個地方賣了,可她卻一定要留下來。“冒賢純粹是為了治沙而累死的,我不走就是為了繼承他生前的遺志,把這里變成沙漠綠洲。”白春蘭不僅說到也做到了。
她沒有停下治沙的腳步,丈夫去世后,她就帶著大兒子兒媳婦一起干,她這種執著的精神感動著村民們,當初搬出去的十幾戶村民都回到了沙漠,白春蘭也毫不猶豫地將多年的治沙經驗盡數傳授給他們。
“全都富起來才能算富,只有我一家,我富的也沒有意義。住下來的都是些窮人,到這個地方,能夠富起來,我們也高興。”這么多年來,白春蘭不斷說服和幫助村民投身治沙事業中,帶領著他們共同富裕,鄰村村民尤虎就是眾多受益者中的一員。
尤虎過去是個出了名的懶漢,除了喝酒就是賭博,直到1991年夏,白春蘭拉著四十頭豬崽找到了他,語重心長地對他說:“虎子,人活著要有志氣,你再這么胡折騰咋行?這豬你先養著,飼料盡管去我家拉,錢先賒著,等賣完豬再還我。如果賠了本,我就不要了。”
回想起當時的情景,尤虎仍是激動不已,正是在白春蘭的幫助指導下,他用養豬得來的錢承包了一片沙地,開發沙產業。如今,他家在毛烏素沙漠邊緣經營了一座占地80畝、資產約20多萬元的家庭農場,成為遠近聞名的“防沙治沙示范戶”。
靠著白春蘭傳授的經驗幫助過上好日子的沙邊子村村民白兆貴談到白春蘭時同樣十分感激,“是白春蘭引我走上這條致富路!”除了尤虎、白兆貴,還有很多村民都是在白春蘭的幫助下走上了致富之路。
2000年8月,“白春蘭沙產業開發有限公司”在沙邊子村正式成立。公司聯合了全村88戶農民,總投資112萬元。除此之外,白春蘭還建議組織全鄉的年輕婦女成立了“女子治沙排”。
為了配合發展鹽池的生態旅游業,2006年5月,白春蘭的治沙旅游區正式向游客開放,并且她還投資建設了白春蘭事跡展廳、涼亭、垂釣中心。
這么多年來,白春蘭累計種樹6萬多棵,風沙育苗900畝,治理沙漠2200多畝,種植喬木5萬株,種植灌木1200畝,封山育林1000多畝,圍欄草原100多畝,發展棗樹套種藥材60畝,建立起110畝的育苗基地,拉沙平整水澆地80畝。
這些卓越的業績讓白春蘭先后獲得了自治區勞動模范,全國 “三八”綠化標兵,全國環保百佳先進個人,全國 “三八”紅旗手,全國 “十大綠化女狀元”,全國防沙治沙十大標兵,全國綠化勞動模范,全國扶貧貢獻獎等榮譽,并被授予 “三北防護林”體系先進工作者,環境保護杰出貢獻者,第二屆、第三屆中國 “十大女杰”提名獎等稱號。
治沙 ?一輩子的事業
一切似乎都朝著好的方向在發展著,正當白春蘭準備趁著好勢頭再大干十年時,命運又和她開了個玩笑,給了她一個致命的打擊。
2007年10月,在丈夫去世后一直陪伴著她治沙的大兒子意外去世。“實際上當時丈夫有病去世,我都沒有那么在乎。去世就去世,我還有兒子。打擊都沒有那么大。這次,兒子突然一下去世,我就接受不了。”“大兒子一直跟我在這干著。他1994年結婚,結了婚就一直在這兒干。”白春蘭提起大兒子時仍舊十分傷心。
如今,白春蘭大多數時間都獨自守著這片“生態莊園”。“我大兒子去世后,我想我這地方沒辦法待了,我小兒子勸我,干脆跟我走銀川。后來也想,我跟他到銀川,我這多少年,政府對我支持,關心,我反起一走,不是對不住政府?政府給我這投資也不少呢,蓋這個展館,公路都鋪到門口。你說我把這撂著一走……”她嘆息道,“尤其這地方呆慣了。寸草不長的地方我現在都把這治理得草長得滿滿的。我咋能舍得走?現在還能干幾年。照管還能照管幾年,我也不想走。有些人對我說,你到城里面。我咋想我都舍不得,把多少苦都受在這兒了。”
白春蘭默默地承受著這一切,但她并沒有因此而倒下,她說打從她開始治沙就面對無數困難,但這并沒有壓垮她,她還要繼續治沙,還要帶領更多的群眾一起治沙。
1980年白春蘭和丈夫在“一棵樹”種下的第一棵樹如今已經長大成材,這棵樹被一片三千畝的綠色海洋包圍著。白春蘭常說:“我已經老了,看這些樹究竟能長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