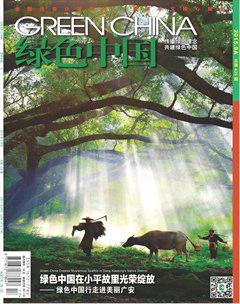生態旅游 20年概念尚未統一
鐵錚


近日,記者參加了一個有關生態旅游的高端研討會。與會專家爭先恐后,發言十分熱烈。3個多小時議程過半之后,記者發現,在中國已有至少20年歷史的“生態旅游”,至今連概念和內涵都沒有形成共識。
這次研討是中國生態文明研究與促進會生態旅游分會組織的。來自大陸和臺灣的20多位專家學者參加了研討。主題是討論確定有關全國生態旅游典型的評選辦法、制訂中國生態旅游發展相關報告的編撰提綱等。
專家發言非常認真,也都很有道理,但的確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其原因在于,在他們心中的“生態旅游”并不是一回事兒。不同的立場,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考量,雖然談論同一個問題,但得出的結論顯然不同。
有資料表明,1995年,在西雙版納召開了中國首屆生態旅游研討會。會議由中國旅游協會生態旅游專業委員會組織。與會的118位專家學者就生態旅游的定義、內涵等進行了研討。這被看成是我國生態旅游研究的一個重要起點。
20年滄海桑田、萬事俱變,生態旅游的研究在中國取得了長足進步。但專家們對于生態旅游概念的定義和內涵依然是各執己見。
生態旅游(ecotourism)是由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特別顧問謝貝洛斯·拉斯喀瑞1983年首次提出的。1990年國際生態旅游協會將其定義為:在一定的自然區域中保護環境并提高當地居民福利的一種旅游行為。在國際上,關于生態旅游的概念也不一致。從自然保護的角度、旅游業角度、研究者角度給出的定義不勝枚舉。這個國際化的定義在中國本土化的過程中,同樣經歷了漫長的道路。
在中國生態學學會旅游生態專業委員會副秘書長、北京林業大學生態旅游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張玉鈞教授看來,“生態旅游”的概念由三個基本要素構成。一是在生態旅游過程中的自然保護。二是在這一過程中強化生態、環境教育。三是通過這一過程促進旅游地的社區發展。
十一屆全國政協副秘書長、九三學社中央原常務副主席陳抗甫則從四個方面來表述“生態旅游”的內涵:首先是有自然資源作為生態旅游的基礎;其次是強調保護優先的原則;再次是積極開展科普教育;還有就是要惠及當地百姓。
臺中教育大學永續觀光暨游憩管理研究所所長吳忠宏教授解讀“生態旅游”時用了五個指標。它們是,建基于自然環境、具備環境意識、環境教育與解說、利益回饋造訪地和永續經營發展。
和這些專家看重旅游地的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不同,有專家認為,“生態旅游”和生不生態本身并沒有關系。關鍵是旅游的過程中是否呈現出生態保護的意識。尊重自然、保護自然、學習自然,就是生態旅游。持這樣觀點的專家認為,生態破壞十分嚴重的地方,環境條件惡劣的地方,開展生態旅游恰恰最有
意義。
有專家特別強調,一定要把“生態旅游”和“旅游”的概念明確區分開來。無論是在研究中還是具體實踐中,兩者混為一談的情況時有發生。
關于“生態旅游”的經濟效益,專家們的看法也不盡相同。西南林業大學生態旅游學院院長葉文教授認為,生態旅游要淡化對經濟的貢獻,而要強調和重視對生態的貢獻。中國生態文明研究與促進會生態旅游分會副會長王興國也對生態旅游評價中參考其在GDP中的比重頗為反感,認為不能過度強調。
對此,有專家提出,對生態旅游效益的評價要堅持定性和定量相結合,不能只是一般性的描述,而要有一定的量化指標。要充分利用互聯網革命產生的各種數據。生態旅游不能搞賠本買賣,其收入要在當地GDP中占一定的權重。
在如何看待生態旅游年接待人數多寡的問題上,專家們的意見也不相同。一些專家提出,一個縣的生態旅游年接待人數要在百萬計才算強縣。生態旅游強不強,不能只由大陸游客說了算。要得到境外、海外游客的認同。馬上就有專家反對說,生態旅游一定是小眾化的而不是大眾化的。游客的多少不能作為衡量指標,也不能過分看重游客的評價。
王興國說,有外國朋友問他,中國哪個地方生態旅游搞得最好?跑過1500多個縣的他竟一時語塞。是啊!評價生態旅游好與不好的指標體系在哪里?
在發言中,王興國推崇的地方是四川的措普。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生長著茂盛冷杉、云杉、鐵杉,有湖泊、有濕地、有溫泉,有品質最好的松茸,還有一段顛簸的土路。沒有越野車根本就過不去……那才是名副其實的生態旅游。
四川省生態旅游協會常務副會長馬朝洪隨聲附和說,措普的確如此。最神奇的是,湖里的魚兒真的能夠隨著人的呼喚游來。幸虧當地建了國家森林公園,否則寶貴的生態環境早就被采礦的、建電站的破壞了。
他說,四川在建立生態旅游評價指標體系上先行一步,用一把尺子量到底,對200多個生態旅游地進行了統一打分。措普的資源生態分全省第一。
青海民族大學的卓瑪措聽了卻不以為然。她名字中的“措”在藏語中就是湖泊的意思。她小聲告訴我,像措普這樣的地方,她的家鄉青海有的是。那里的草原、高山、湖泊,都是生態旅游的好去處。
臺灣的吳忠宏教授強調,評選標準的標準是八個字“簡單、好用、可行、具體”。
有專家建議直接使用國際化的生態旅游定義和內涵,但更多的專家學者認為,打出中國本土化的生態旅游旗幟,不僅對本國有指導意義,對亞洲乃至更大地區都更具示范意義。
張玉鈞教授認為,生態旅游沒有權威性的定義被普遍認可的原因在于:一是各方面人士對生態旅游保持關注的同時,往往從自身角度出發來定義生態旅游,因此提出來的定義在內容的涵蓋面上往往存在片面性;二是各種定義的內涵側重點有所不同,表現在從理論到實踐的各個環節上,包括旅游對象、旅游移動空間、旅游團體的大小、旅游活動的形態以及旅游理念等等。但是,各個定義的著眼點分別是從自然保護、旅游業及研究者的角度出發,來體會生態旅游內涵的。
一位專家直言不諱地說,他不大愿意參加各種各樣的研討會。他認為,許多專家都是自說自話,討論的不是一個話題,也不在一個層面,常常會出現“張三罵雞”、“李四打狗”的現象。他認為,研討不能求寬,而要求深、求實。
中國生態文明研究與促進會生態旅游分會副秘書長、華僑大學教授李洪波說,有問題、不一致,才證明有進一步研究和討論的空間。
的確如此。20個春秋過后,盡管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并未達到共識,但生態旅游事業在不斷發展、生態旅游研究在不斷深入,卻是不爭的事實。硬性統一一兩個概念或許容易,但對于生態旅游事業的發展而言,學術上的百家爭鳴更有益處。因此,和異口同聲的套話空話相比,這樣認真、嚴肅的研討有意義得多。
對下一次有關生態旅游的研討充滿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