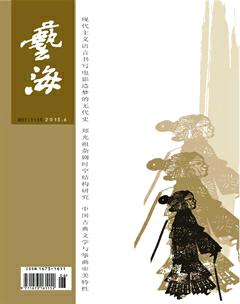全球化時代下的“我城”空間呈現(xiàn)與主體建構
郜杏
〔摘要〕本文以許鞍華“天水圍兩部曲”中香港老社區(qū)的空間呈現(xiàn)為切入點,通過全球化時代“無地域空間”對香港本土地域空間的日益解構,淺析影片中的香港社會邊緣人群是如何應對全球化所帶來的社會現(xiàn)實問題,以及在跨界往返的過程中如何完成主體身份的建構。
〔關鍵詞〕全球化空間呈現(xiàn)跨界往返主體建構
在現(xiàn)實主義的敘事電影逐漸減少,奇觀電影充斥中國電影市場的當下,香港新浪潮電影運動中唯一的女性導演———許鞍華,是為數(shù)不多依然堅守敘事電影陣營的導演中最出色的踐行者。她曾在第三十一屆香港電影金像獎(2012年)頒獎典禮發(fā)表獲獎感言時說:“可能從此以后,我很難再走上這個舞臺,趁此機會,我要感謝香港這個城市。我從小在香港長大,在這里受教育,拍電影、拿獎,謝謝香港鼓勵我,這里有很好的菠蘿包和奶茶,我希望我可以多幫這個城市做事。”誠然,她執(zhí)導三十多年來,一切與港人有關的生活方式、感受,或愉悅或痛苦,都是她電影所關注的重心。她從導演以動蕩的越南映射香港九七后處境的“越南三部曲”起,便開始抒寫個體生命在大時代背景下的不可抗拒與無可奈何,并有意刻畫香港的本土性,進行香港的自我歷史闡述,即便是她去年的新作《黃金時代》中客死異鄉(xiāng)的蕭紅,也難逃貫穿她所有作品中“流徙不安”這個最重要的母題。在全球化進程日益加速的香港社會,人被環(huán)境所迫而飽受流離無根之苦的窘境,在許鞍華的“天水圍兩部曲”中尤為突出。
一、全球化對香港社會景觀的影響及在影片中的“我城”空間呈現(xiàn)
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開始步入快速發(fā)展的現(xiàn)代化進程,到七十年代中后期,正式進入黃金發(fā)展時期,并一躍成為亞洲的金融中心,逐步具有國際化大都市的全球化特征,而這一特征主要體現(xiàn)在香港都市空間的發(fā)展規(guī)劃中。香港大學教授阿克巴·阿巴斯(AckbarAbbas)認為,香港的城市空間景觀主要表現(xiàn)在建筑的不斷重建和過度密集①。他指出,隨著香港標志性建筑的日益涌現(xiàn),中環(huán)天際線也處在不斷的變化中。其中尤為醒目的標志性建筑,當屬位于港島中環(huán)黃金商業(yè)地段的香港匯豐銀行大廈和中銀大廈,它們的拔地而起,不僅象征著香港在全球領先的經(jīng)濟地位,也成為全球資本主義浪潮影響下的香港全新城市景觀形象的代言。但香港城市建筑頻繁的重建,也在某種程度上使香港淪為一座缺乏辨識度的“無地域空間”(non-locality),老香港空間所承載的歷史、文化記憶被全球化的空間特征所替代,高聳入云的摩天大樓和大型購物中心成為香港商業(yè)電影中的一大視覺噱頭,而那些真正具有香港本土特色的“次屬空間”(subalternspace),則慢慢淡出人們的視線,為人們所熟悉的老香港將面臨著被消失的命運。然而,值得慶幸的是,這些具有濃厚生活氣息和歷史意味的次屬空間,在許鞍華的電影中依然作為不可取代的港式地域“空間呈現(xiàn)”(representationofspace)的特征所在,被完整地保留下來。在“兩部曲”之一的《天水圍的日與夜》(以下簡稱《日與夜》)中,天水圍是一個迥異于香港腹地文化空間特征的舊社區(qū),它不同于香港商業(yè)電影中所呈現(xiàn)的香港城市形象,沒有現(xiàn)代化的寫字樓和大型商場等全球化無地域空間,而是一個充滿著集體記憶和懷舊色彩的次屬空間,有著濃厚的生活氣息和歷史意味,凝聚著傳統(tǒng)獨特的在地經(jīng)驗的香港經(jīng)濟邊緣地帶,近年來還因發(fā)生過轟動全港的倫常慘案,被媒體稱為“悲情城市”。但導演并沒有去刻意渲染它的悲情性,而是通過對影片中主人公生活的日常性敘事和對舊影像資料的插入,來表達對逝去時光的緬懷。皮埃爾·諾拉(PierreNora)曾說:“懷舊是一種對回憶、記憶的深層渴望,而這些所謂的記憶是基于斷裂的全球后現(xiàn)代文化情境的到來,而產生的對過去傳統(tǒng)家庭、社區(qū)、生活形式結構的認同”②。從水塘到輕軌、從圍村到新市鎮(zhèn),這段帶有懷舊色彩的天水圍的今昔比照,一方面可以視為導演對現(xiàn)代社會人際關系冷漠、疏離的失望;另一方面也通過對舊有生活場景的影像再現(xiàn),來抵抗全球化時代無地域空間對本土地域文化的侵蝕。
二、全球化浪潮下的主體身份追尋與建構
許鞍華“天水圍兩部曲”分別通過香港本土居民在遠離香港腹地的天水圍的空間實踐和來自中國內地的新移民于香港、內地間的跨界往返,來呈現(xiàn)全球化時代背景下,個人尋求主體身份過程中的遭遇與全球化之間的關系。《日與夜》圍繞著均已在空間上逐漸脫離香港社會的單身母親貴姐、幼子張家安和鄰居阿婆三人展開。他們所生活的天水圍,在影像中并非香港全球化特征的物理空間,而是具有香港舊有特色的空間映像,這種對地理位置去全球化特征的呈現(xiàn),暗示了其邊緣化的文化身份。片中,貴姐母子在與香港腹地的家人聚會中總是處于被孤立的狀態(tài),打牌作為聯(lián)絡親人感情的活動之一,貴姐卻不能融入其中。張家安在參加學校組織的教化本地年輕人的“團契”時,一連四問的回答都是一個字:哦。表象是乖巧聽話的兒子形象,暗示的卻是一種離席的在場,沒有真正參與到討論中去。阿婆與貴姐母子的處境相似,在女兒去世后,便搬至天水圍獨居,生活拮據(jù)的她為填補自己與女婿和外孫間的情感裂縫,不惜買黃金首飾,卻遭到女婿的婉言謝絕,重返家園(香港腹地)的向往化為泡影,可見,在重建與腹地家人的親情關系的空間實踐中,貴姐母子和阿婆均以失敗告終。雖然在與腹地家人的人際關系建立過程中障礙重重,可同樣生活在天水圍的鄰里間的人際關系卻迅速地被搭建起來,這主要表現(xiàn)在貴姐母子與阿婆在鄰里關系處理上。片中,貴姐不僅幫阿婆解決了工作問題,在生活上也傾其所能,同樣阿婆對貴姐母子也予以回饋。片尾,三代人圍坐著吃柚子,一個升格鏡頭漸漸高起,仿佛俯瞰著整個天水圍,這不僅是以香港老社區(qū)最質樸的鄰里關系對抗香港腹地冷酷疏離的資本主義全球化因素,也是對香港不同區(qū)域空間中不同程度的全球化所帶來的空間彼此間的差異而影響人們正常交際的暗諷。
相較于香港本土居民自我身份的尋回,《天水圍的夜與霧》(以下簡稱《夜與霧》)揭示了香港在全球化進程中給本土社會和本土居民,在面對去地域化這一問題上所帶來的一系列影響,和新移民尋求身份認同過程中的掙扎。劍橋大學教授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認為,全球化進程的加速與社會關系的延伸,加劇了地方治理和文化認同的壓力。全球化社會關系的發(fā)展,不僅深刻影響著民族國家或地方社會,也引發(fā)了更為強烈的在地文化認同或民族主義情緒。③在這樣的情況下,全球化不僅表現(xiàn)為人與人社會關系的緊密和強化,同時也折射出當在地社會在面對非在地社會的合力時,所凸顯的焦慮與不確定性。男主人公李森就生活在這樣的境況下,作為香港人,他的風光和自信一方面受益于香港是全球化都市,另一方面他的落魄和憂慮也因香港這一全球化金融中心遭受金融危機而成為無業(yè)游民,每個月靠政府援助金過活。作為本港居民,卻因主體身份的不穩(wěn)定性難以主體身份自居,這也成為他和新移民曉玲在融合過程中的一重阻礙。他試圖在跨地域的往返過程中,在封閉落后的內地農村尋求男性的主體地位,但到了后才發(fā)現(xiàn)自我主體的迷失。這不但源于香港所處的復雜的歷史背景,也因自己作為成年男性卻沒有與之年齡相符合的社會生存能力,所以,四川農村也必然成為天水圍的異地鏡像,使李森淪為“他者”。當他們再次回到香港的日常生活中時,邊緣身份的窘迫和主體身份的不穩(wěn)定,使他們再度陷入一觸即發(fā)的矛盾狀態(tài),而李森試圖通過性暴力,將曉玲置于情欲客體的“他者”地位,從而重建“自我”的意圖也并未得以實現(xiàn)。曉玲通過婚姻完成了從閉塞農村到全球城市的華麗變身,但卻無法依靠李森實現(xiàn)自己的“香港夢”,歸根結底還是源于李森自我主體性的不穩(wěn)固,這一形象似乎象征的正是“九七”回歸后的香港,在面對“去殖”和“回歸”的雙重語境下,因對未來方向的不確定,而引發(fā)的焦慮,與此同時,全球化發(fā)展中的去地域性,也加劇了香港社會在新的社會歷史狀況中尋找自我身份的難度和痛苦。
湯姆林森(TomLinson)指出,“全球化從根本上使我們賴以生存的地方與我們的文化實踐、體驗和認同感之間的關系發(fā)生了轉型”。④他認為,全球化給地方社會帶來的去地域化過程,會使地方社會被新的社會關系和文化形式所取代,因此,在全球化時代背景下的流動人群,其自我主體性的確立不再完全依賴與生俱來的特定地域性優(yōu)勢和資本,而是具備了某種跨地域性的特征。但是《夜與霧》中的女主人公曉玲,作為香港新移民在尋找主體性的過程中所遭遇的阻礙和付出的代價卻更為沉痛,一方面,天水圍并非香港腹地,全球化特征弱化;另一方面,不論是救助站的姐妹還是曉玲自身和家庭灌輸給她的父權意識,都成為其建立主體身份的阻礙。出身于四川農村的曉玲,基本沒有教育背景,傳統(tǒng)觀念暗示她女人是男人的附屬,因此便把自己稱作“李太太”,放棄了自己的姓名權;在第一次遭遇家庭暴力時,鄰居們勸說她找區(qū)議員,曉玲的反應是要給李森留面子;當在尋求議員幫助時,議員問曉玲的名字時,曉玲脫口而出的卻是“我丈夫姓李”。曉玲的母親是一個具有典型男尊女卑觀念的鄉(xiāng)村婦女,在曉玲的自我認知過程中,母親所持的腐朽的宿命論、迂腐的家長制觀念,沒有給曉玲任何在價值觀念方面實現(xiàn)自我突破的可能,當曉玲遭到家暴后向母親訴苦時,母親卻說“我們鄉(xiāng)下人,哪個村,哪個巷里頭都是男人打老婆的事”,這表明母親已默認了女性在兩性關系中的受虐地位,曉玲在失去家這條唯一的退路后,便注定了死亡的結局。片中,婦女救助站的其他女性形象,大都出于內心對傳統(tǒng)文化價值的認同而接受了這一切。她們常常湊在一起算命,這種沒有科學依據(jù)的客觀唯心主義,暗示了這些女人對自我主動性的放棄,阿瓊甚至自欺欺人地認為“到明年春天,我和我的丈夫就會穩(wěn)定下來,雖然現(xiàn)在分分合合,但是會白頭到老的”。在這樣的大環(huán)境中,曉玲那微弱的主體意識顯得愈發(fā)力不從心,自食其力、獨立謀生的念頭最終無法付諸于實踐。
結語
“天水圍兩部曲”摒棄了香港社會無地域性空間的呈現(xiàn),而是在凝聚了香港本土歷史和文化記憶的天水圍這一特定空間,把鏡頭對準在該空間普通港民的日常生活上,在某種程度上,可視為導演借香港本土地域空間,對快速發(fā)展的“全球化空間”(globalizingspace)的抵抗。如果說《日與夜》撫慰了處于社會變遷中港人的焦慮心理,那么《夜與霧》更多的是通過兩位主人公跨地域尋回自我主體地位的失敗,來揭示大陸和香港兩地在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差異,以及香港在全球化的進程中需要重新認識和調整自己與大陸關系的必要性與迫切性。(責任編輯尹雨)
注釋:
①[英]阿克巴·阿巴斯,《香港:消失的文化與政治》,明尼蘇達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②王海洲等著,《城市、歷史、身份———香港電影研究》,中國電影出版社,2010年版
③AnthonyGiddens,TheConsequencesofModernity,StanfordUniversityPress,65
④約翰·湯姆林森,《全球化與文化》,郭英劍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56頁
參考文獻:
[1][英]邁克·費瑟斯通,《消費文化———全球化、后現(xiàn)代主義與認同》,楊渝東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2]洛楓,《盛世邊緣:香港電影的性別、特技與九七政治》,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3]孫紹誼,《電影經(jīng)緯———影響空間與文化全球主義》,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4]羅卡、法蘭賓合著,劉輝譯,《香港電影跨文化觀》,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