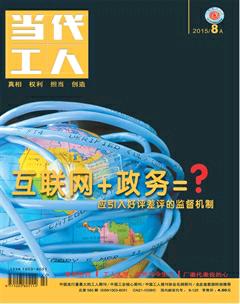地下室
李憶鋒
對于汪采琪來說,地下室不是地下室,是地獄。
她在巴黎一個街區的地下室住了將近兩年,那是一段非人生活。
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外國,地下室都是一樣的。不見陽光,陰暗潮濕。住地下室,不僅對人的身體健康造成損害,對心理也是一種戕害——眾人眼中,住地下室的人都是窮人。
采琪不是因為窮才住地下室。她有錢,但不能住酒店。她是逃亡者。或者說是被逃亡者。
因為一個男人她被迫逃亡。
這個男人是市一級領導,汪采琪和他有男女關系。這種你情我愿的男女之事,要是發生在老百姓身上,頂多算是搞破鞋,沒人舉報沒人追究。但是到了官員這里,就是違紀違法,大多被定義為:利用職務之便,與女性(現在有了“多名女性”這個詞)保持不正當男女關系,道德敗壞。
很多內部的事情采琪并不知情,那個深夜,一條突如其來的短信讓她如夢方醒,心驚肉跳。短信上只有一行字:吳主任被紀委調查,涉及你,趕快出國。
俗話說做賊心虛,采琪也是如此。她立刻訂了飛往法國的機票,把女兒托付給大姐,告訴大姐自己出國考察一個月,請大姐幫忙照顧女兒,帶著簡單的行李迅速離開國內。
如果白天能走出地下室,在地面上出行、工作、生活,晚間再回地下室過夜,這樣的生活還勉強接受。而采琪幾乎是一天是24小時在地下室,剛來的時候,她甚至是一連幾天不出地下室。
她不敢白天走出地下室,害怕被人發現。選擇晚間出來購物、放風。只見月光,不見陽光。她非常渴望見到地面上的陽光,但是就是這樣的對于大多數人來說極其簡單的事她根本做不到。
在狹小的地下室住房里,除了思念上小學的女兒,除了幻想沐浴地面上的陽光,她就一直琢磨那條半夜發來的神秘短信。那是一個陌生的電話號,他是誰?他怎么知道老吳被紀委調查?他怎么知道我和老吳的關系?他怎么知道我的手機號?他為什么給我發短信?
當然她也想:這樣躲在異國他鄉地下室里的日子,什么時間是頭?
為了防止被跟蹤,她換了手機號。她最想給兩個人打電話:一個是大姐,告知她自己現在真實的狀況,請大姐原諒自己說了謊,請她照顧好女兒,再聽聽女兒清脆稚嫩的嗓音。除此之外,她還想給那個發來短信的陌生號碼打電話,一是問問他是誰,再想問問:他是否知道老吳現在的情況。但是采琪一直忍著不打電話。現在科技太發達,也許一次通話,就能讓人發現自己的行蹤。
最開始,她還敢照鏡子看自己。到后來,她不敢照了。面黃肌瘦,一臉黑斑,頭發枯焦,說她像60歲的老太,一點不夸張。可她還不到40啊。1米65的身高,體重不到80斤……她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縷魂兒。
原來的她談不上是絕色美人,卻也是氣質不俗的美女。一頭秀發是她的驕傲,黑又亮,像是黑緞子。皮膚白皙得透明,仿佛能看見表層下的血絲……她的缺點是不大愛笑,這個美女有點冷。但是,老吳就是喜歡這樣的冷意矜持,他們就在一起了。
老吳不是那種看見美女就走不動道的男人,他挺有男人氣質,能讓女人動心。老吳工作很忙,和采琪見面只能抽空。約好時間找個高檔飯店吃吃飯喝喝酒,纏綿半日。老吳好像知道采琪的家境,同情她的際遇,對她很貼心,偶爾帶給她購物卡,實心實意地說:你自己去買衣服,一是我實在抽不出時間陪你逛街,再一個我怕在商場里遇上熟人,對你和我影響都不好。衣服要買牌子貨,穿來給我看。偶爾他帶給采琪高檔手包、首飾,世界品牌的內衣,還說,要送車給她。采琪拒絕了:不想張揚,以后再說吧。
和老吳在一起不久,采琪在本單位提職了。
天底下沒有不透風的墻。很快單位同志開始在私下里議論她。汪采琪做好了成為議論中心的心理準備:嘴巴長在人家臉上,愛怎么說就怎么說吧。
不過,傳到采琪這里的“流言蜚語”倒不是一味的諷刺挖苦譴責鄙薄,而是還帶點人情味。這個說:她丈夫長年生病,她一個人帶孩子生活不容易,家外面有個男人幫襯下,也是應該的。那個說:人家采琪長得好看,才能跟市一級領導扯上。像咱這樣的黃臉婆丑八怪,就是倒貼人家也不愿意呀。
現在的人們似乎對風流韻事已經見怪不怪,不再咬牙切齒地痛恨,是社會進步了還是世道墮落了?
汪采琪出國時,隨身帶了一張銀行卡,這張卡里面的錢可以讓她在異國他鄉生活一段時間。一年過去了,沒有任何動靜。既沒有來自國內的通緝令,也沒有來自親戚朋友的其他音信。(當然,她把手機換了,沒人能聯系上)
她在惶恐中度日,度日如年。什么時間可以結束這樣的地下室逃亡生活?她冒出這樣的一個念頭,就是不被緝捕死在國內的監獄里,也會死在異國他鄉的地下室。想著這些,她幾乎崩潰。
這天她看著日歷,忽然像發瘋一樣,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今天一定要在白天走出地下室,走到大街上去,就是被發現了,被抓走了,也要走上去。
她踏上地下室通往地面的臺階,走出地下室。
太陽光明正大掛在天空,陽光明晃晃地照耀大地,一切都是那樣的理直氣壯。采琪像久居地下的老鼠,對明晃晃的太陽很不習慣。她把手貼在眼皮上,露出一條縫隙,去看溫暖的久違的太陽。
身邊有熙熙攘攘的人流走過,那些一個人打著小旗身后跟著幾十人的小隊伍,是中國旅游團。在巴黎的大街上,看見中國人不足為奇。聽見親切的家鄉話,采琪心里五味雜陳。
突然,一個聲音大聲叫著她的名字:“汪采琪!”隨后采琪的肩膀被一雙手重重地搭上。
采琪頓時被嚇得沒了魂,她一下子癱坐地上:真的就這么倒霉?第一次白天走出地下室就被認出來、被抓住?或是命該如此,認了吧。就這樣被押解回國,然后被審判,然后……
事情如果能就此了斷,也算好事。那就不用再東躲西藏,不用再住地下室,能自由的呼吸陽光的味道……
對方扶起癱軟在地的采琪:你怎么在這里?你怎么變成這個樣子?采琪抬起頭看對方——不是警察,是單位的同事,就是那個說自己黃臉婆丑八怪勾不上男人的女同事。
你怎么在這里?采琪問同樣的問題。
我退休了,跟著旅游團旅游,歐洲五國,巴黎最后一站。
采琪咬咬牙,向同事說了實情:怕受老吳牽連,跑到國外躲起來,一直不敢回國,怕被抓。 同事睜大眼睛:你是說市政府吳主任的案子?已經結案了,據我所知,沒你什么事呀。
沒我事?真的?
真的。紀委已經通報了,內部也傳達了。沒你事,我當時還為你慶幸呢。
是嗎?采琪再次確認。
其實也沒啥,你不就是和老吳挺好嗎。
可是——我提拔的事,老吳給人事局打過招呼……采琪有些心虛。
嗨,你提拔的事,我最清楚。你的業務水平夠格。局務會上全票通過了,就等市人事局編辦批復。在這個節骨眼上,吳主任給編辦打了電話,這樣就順水推舟地批下來了,不涉及買官賣官。哦。采琪長舒一口氣。
沒事。那就是說自己白白住了將近兩年的地下室。采琪再一次癱軟下來。胖同事扶起采琪:你趕快回國吧,瞧你現在這個樣,沒一點人樣兒,比我這個老太太還——還丑——還老,真可憐。同事發自內心憐惜地說。
采琪和胖同事在異國他鄉的街頭相遇,但是身份不同:她是旅游者,而采琪是逃亡者。
同事跟上旅游團走了,邊走邊回頭對采琪說:回家吧,別說沒事,就是有事被審查,也是呆在國內踏實。跑到國外住地下室,那是人過的日子嗎?采琪回到地下室,關上門,大哭起來……
汪采琪回國后,先到大姐家。大姐對采琪突然進門并沒表現出過度驚訝。大姐說:過了一個月你沒來接孩子,給你打電話也不通,我就覺得不對勁,再聯想到你和市里某位領導的特殊關系,心里多少明白點,就不盼著你回來了,但還是非常惦記……大姐告訴采琪:女兒在寄宿學校,周五回家,娘倆能見面。采琪哭。
還有,孩子他爸去世了。丈夫重病臥床多年,走了也是解脫。只是臨終前,沒能見上一面。采琪哭。
大姐說:腳下的路靠自己走,但有的時候,我們能控制自己的腳,卻控制不了路。很多的路帶著陷阱,你沒法躲避。現在的風氣就是這樣墮落,坑了好些女人。采琪擦干眼淚。
晚上,在大姐家的床上,采琪攤開四肢,踏踏實實睡了一覺。她做了一個夢,夢見在巴黎的地下室里,一個50歲左右的女人,用厚厚的粗胖的溫熱的大手,握住采琪瘦小的干枯的冰涼的小手,說:那條深夜里的短信是我發的。一切都過去了,別想太多,快點適應新生活,照顧好孩子,母女相依,過平實卻踏實的生活。
采琪一下子醒來,她按照記憶中的那個電話號撥過去,耳邊傳來提示音:該號碼是空號,請您核對后再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