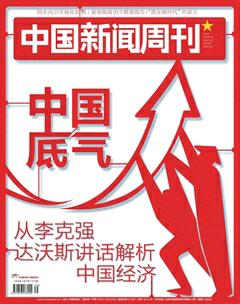王千源:豺狗與天鵝
溫天一

王千源可能是最熱衷于看探索頻道與《動物世界》的演員。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在他的表演里,仿佛也充滿了一種過濾掉人類浮華、生猛又粗糲的自然質感。
在他與劉德華共同主演的新片《解救吾先生》中,他扮演了一個不相信任何人、有著變態執念的綁匪。用他自己的話形容,“像一條瘦骨嶙峋的豺狗,在鬼火磷磷的荒原上,用精光閃爍的眼睛,尋求著每一個可以收入囊中的獵物。”
“每一天, 我都在搏斗。” 王千源這樣形容他拍攝電影的45天。
豺狗
電影《解救吾先生》的故事改編自當年轟動全國的真實事件:“明星吳若甫被綁架案”,如果用一句話概括劇情,那就是北京警方如何斗智斗勇,從一個喪心病狂的變態綁匪那里解救出了陰差陽錯間被劫持走的大明星。劉德華演明星人質“吾先生”,而王千源飾演綁匪。
按照中國警匪片約定俗成的套路,無論是一個怎樣惡到極致的歹徒,最終要么暴露出溫柔的一面,要么表示懺悔。但在電影《解救吾先生》中,導演丁晟似乎并沒有給王千源這個柔情的機會。
“他就是這么討厭,從頭到尾。”王千源對《中國新聞周刊》這樣形容自己的角色。
“我能想象到這個角色,他就像是一條豺狗,一條喪家之犬,在陰冷的冬天,雪花星星點點地飄過,它無聲無息地徘徊,一邊在垃圾堆里刨食,一邊時刻警覺地聆聽著周圍的動靜。”王千源這樣比喻。
而在塑造角色的過程中,王千源提前做了大量的案頭功課。演員吳若甫在電影中飾演一位解救人質的警察,他用自己的親身經歷給了王千源很多一手素材,而王千源也自己閱讀了大量犯罪心理學方面的書籍,并去公安局做田野調查式的采訪,但是即便有這些“底子”,王千源也依舊覺得不夠逼真,他需要給自己營造出一個被逼到絕境的感覺。
“華子(劇中綁匪的名字)是一條豺狗,他一定是那種骨瘦嶙峋的狗,稀稀疏疏的毛,寒風已吹過,像疏落的野草一樣抖動。”為了讓自己的身體呈現出他自己想象中的這種形象,王千源開始了自我折磨,在演繹華子被槍斃之前、在監獄里與自己母親見最后一面那場戲的時候,提前三天給自己斷了水,每天緊靠一點饅頭干、地瓜干和葡萄干過活,而在拍攝前一晚,王千源沒有回家也沒有在劇組休息。
為了角色的疲憊感,“我去找朋友喝酒,喝到天亮,然后直接在周圍找了個洗浴中心蒸了桑拿,瞇了一會。”王千源回憶到。
“誰會知道馬上要死了是一種什么感覺?”第二天早晨,王千源問自己,那時他正坐在車里,行駛在去拍攝地點開工的路上。
陰天。他望了望車窗外,空氣中繚繞著經久不散的霾。車正路過國貿橋,一路奔赴通州,而這條路,也是電影中華子所踏上的那條不歸路。王千源的眼睛里布滿血絲,他開始聽提前預備好的悲愴音樂,然后自己開始抑制不住地流淚。
但到了拍攝場地王千源發現,自己的臉龐因為昨夜攝入了大量酒精而略顯浮腫,于是他又開始繞著監獄跑圈,整整一個多小時,直到徹底脫水為止。
而在正式拍攝這場戲的時候,王千源扮演的華子第一次面對母親,留下了眼淚,但那淚水似乎不是為了悔過,也不是為了殘存的一點溫情而流。“你說不清是為了什么,在最后一刻,他還顯得那么不著調,但說他不著調,這眼淚又是從何而來?”
王千源在戲里哭了,但就是那場戲,讓導演、攝像和助理,全部在工作現場抱頭而哭。
斯坦尼
康斯坦丁·謝爾蓋耶維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大部分人知道這個聽上去有些拗口的俄語翻譯名字,很可能是從周星馳那部著名的電影《喜劇之王》里,心懷演員夢想的草根小人物常年在枕頭底下藏著一本翻閱了八百遍的卷邊兒舊書:《演員的自我修養》。
在這部被后人奉為“演員圣經”與“表演教材”的殿堂級理論書籍中,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詳細闡述了一個演員應該如何利用“體驗”的方法去塑造角色。按照斯坦尼體系的要求,為了讓表演足夠令人信服,演員應該做到與角色合二為一,換句話說,演瘋子就該進精神病院去生活一段時間,演罪犯就要進監獄去體驗下從身體到精神的雙重折磨。
而王千源給斯坦尼體系加了一個更為中國本土化的解釋:不瘋魔,不成活。
雖然作為演員的王千源身上總是自然而然地散發出濃烈又澎湃的生猛草根氣場,總使人疑心他的一身本事都來自于長期跑江湖的實踐經驗,但實際上,王千源是正經八百的科班出身,他畢業于中央戲劇學院—— 一所完全以斯坦尼體系為教學基礎的正統戲劇學校。
他是學校里真正的好學生,甚至每次在假期中就已經提前完成了老師為下學期布置的表演體驗練習作業。
事實上,《解救吾先生》絕非是王千源用第一次使用瘋狂自虐式的“體驗派”手段尋找角色感覺。早在大學三年級時,出演霍建起導演處女作《贏家》時,他就已經那么干了。
聽起來似乎有點瘋狂。在那部電影中,王千源需要演一個只有一只胳膊的殘疾人運動員。而在確定下角色后一個多月的時間內,他長期把一只手綁在身后,強迫自己學習只用一只手和牙齒輔助去系鞋帶,然后終于憑借這手“絕活”,獲得了導演的認可。
從此以后,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王千源都憑借著一股近乎迂腐的熱情,嚴格地按照“體驗派”的方式,或長或短地“活”在每一個角色的身體里。
1997年,他出演陳凱歌的《荊軻刺秦王》,統共三句臺詞,而按照劇本提示的要求,這個角色需要“爬著進場,跪著說話,表現出從抽泣到號啕大哭的過程”。為了這句提示,王千源提前嘗試了所有他自己能夠想到的人類的哭法,甚至半夜不睡也要練習,怕吵醒同屋,他就自己躲進浴室,然后對著鏡子大放悲聲。
大學畢業后,王千源告別了他打了四年交道的斯坦尼,進入北京兒童藝術劇院,成為了一名體制內的兒童劇演員。
那段時間,他很郁悶,雖然從小跟隨父母在話劇團長大,使得他早早就分清了做戲與生活的區別,并且打心眼里也并沒有覺得話劇舞臺比別的藝術門類更神圣,“我父母就是話劇演員,小時候,大家都覺得話劇很神圣,很酣暢淋漓。但我看到的是大幕后邊的東西:為分房子打架,為漲工資罵人。”他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
在兒藝,王千源所有的“體驗派”經驗似乎完全派不上用場,“那時候,我基本是演樹,演風,演石頭和太陽,我還有同學一起分配進來,他得在屁股上插根棍,演小蜜蜂,滿臺飛來飛去。”王千源回憶。
覺得無聊,沒勁,多余的精力無處發泄,同時也為了補貼生活,王千源甚至開起了小飯館,賣盒飯。“其實我心里挺難受的,那會兒劉燁什么的都已經成名了,他們回學校都會意氣風發地和傳達室大爺打招呼。我回去,就臊眉耷眼的騎著自行車,大爺問我干嗎的?我說,送盒飯。”
很多年以后,這樣的經歷讓王千源再演繹起那些低到塵埃中的小人物時,鮮活感撲面而來,也許對他來說,生活本身就是一種“體驗”。
但現在,王千源并不承認自己完全是斯坦尼的忠實擁躉,“丁晟(《解救吾先生》導演)是,我并不完全是。”這位中央戲劇學院的畢業生打了文縐縐的比喻,“我希望自己的表演是體驗和體現的結合,像那種帶有油畫技巧的中國水墨畫。”
荷爾蒙?
探索頻道制作的野外探險紀錄片是王千源最喜歡看的電視節目。
“你知道嗎?很多時候動物是靠著氣味來傳遞信息的。它們在戀愛、求偶、搶地盤、廝殺時候所分泌的氣息都是不同的。”王千源煞有介事地說,然后他頓了頓,“其實人也一樣,只不過現在進化得太好,好多本能都被掩蓋住了。”
仿佛從童年時候起,王千源就能夠以一種本能的、專注于各種氣味的體察方式,來建構著屬于自己獨特的記憶空間。
王千源的父母都是遼寧人藝的演員,小時候,他的活動空間就基本上是話劇團家屬院、排練廳和劇場。
他記得沈陽冰天雪地的冬天,吸進口里的凜冽空氣的味道,還有老式劇院的化妝間,房間里常年繚繞著的脂粉香,混雜著陳年戲服的樟腦味,以及一點點的煙草氣息——那仿佛是屬于另外一個世界,區別于日常凡俗生活的味道。
十幾年前,王千源在滕華濤導演的電視劇《危情時刻》中扮演一個戲份不多的小警察。為了塑造角色,他特意跑到北京崇文分局體驗了一個多月的生活,真正與基層民警們同吃同住同審訊嫌疑犯。
但那段經歷,讓王千源印象最為深刻的細節并非來自什么錯綜復雜的案件抑或手段兇殘的罪犯,而是他所參與的一次跟隨警察帶領歸案小偷去指認犯罪現場的行動,而這次行動所賦予他最大的感悟是:人肉是臭的,真真正正的臭味。
那次的經歷看上去似乎可以寫成一篇短篇黑色幽默小說。一個倒霉的小偷,深夜順著水管爬到居民樓里偷竊,不慎跌落下來,摔傷動彈不得,只能趴在地上等待警察將其抓獲。第二天,王千源和派出所的其余警察們帶著小偷一起,去居民區里一一指認他之前所盜竊過的場所。
“一個小型吉普車,平時最多只能坐四五個人,那天一共塞了9個人,小偷披著毛毯,擠在我們中間。大冬天的,也不大洗澡,加上緊張、煩躁,人就容易散發出一種氣味,我永遠記得那段短短的路程,狹小的密閉空間內充斥著滿滿的人肉氣味,臭,酸,騷氣沖天。”
不知道是不是由于對氣味的敏感,王千源的表演看上去也充滿了一種荷爾蒙式的敘述方式,直接,熾熱,并且直沁心脾。
在《解救吾先生》中,王千源也執拗地用氣味給自己搭建出了一個只屬于綁匪華子本人的精神樓閣,“七八天不洗頭,那個味道,即便最好的化妝師也不可能賦予角色。”而電影中那副銬了華子的手銬,則是監獄中貨真價實的真品,“舊舊的,帶著之前人的油氣和血氣,遮蓋著本身的金屬味道。”
而在拍攝華子和女朋友分別的一場戲時,王千源即興扇了女人一記耳光,隨后又把她摟在懷里揉著頭發,“人渣談戀愛總不能含情脈脈地對女人說,你放心吧,等著我回來,我也沒有時間去和對手戲演員講清楚對角色的理解,最后也不知道怎么就耳刮子扇了上去。”王千源說。
演繹那場戲的王千源頗有點馬龍·白蘭度的味道,一種底層地痞流氓式簡單又粗暴的魅力,他們渾身散發出汗水淋漓的味道,但那似乎比高級香水為更讓人迷醉,他們從不善待女人,但要命的是,女人還是會前赴后繼地愛上他們。
天鵝
生活中的王千源其實遠沒有電影中的他那么生猛。他是父母的孝順兒子,還是一個寵溺女兒的父親。
專業演員出身的父母是他最忠實的觀眾,任何一部出現王千源身影的電視劇或者電影,他們都會反復觀看。甚至在《鋼的琴》中,王千源的父親還親自上陣,客串了一個留戀過去時代的留蘇退休工程師。
“他們會給你的表演提意見嗎?”記者問。
“從來不會。”
“但是他們是專業的話劇演員啊!”
“專業不專業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看見兒子在電視里啊。”
王千源的女兒叫小蘋果,就像那首流行歌中所唱的那樣,是她的父親眼中最美的云朵。
為了讓女兒上一家好的公立幼兒園,王千源天天發愁,最后他干脆厚起臉皮,拿著自己演出的光碟站在通往幼兒園的過街天橋上“堵截”園長,“一見到園長我就湊上去,說我是演員,你看看這是我的碟,我家孩子要上學了,你看看能不能想辦法讓我孩子去你那上學?”
大學時代,王千源曾在學校中演過一出契訶夫的獨幕短劇《天鵝之歌》,一個郁郁不得志的老演員,最終在曲終人散的黑暗劇場里,臆想著自己從來沒有獲得過的輝煌,他大段大段朗誦著莎士比亞的臺詞,像生命中最后一曲天鵝之歌那樣莊重又孤寂。
為了體驗角色的孤獨,王千源一個人在排練廳里住了三天。但第四天夜里他實在忍不住,打開窗子跳出去跑回宿舍了,那時外面正下著大雪。
現在的王千源可能不會再去刻意體驗孤獨的滋味,而且看多了科學探索頻道的他也知道天鵝之歌只是存在于傳說里,真實世界中的天鵝,是一種極為兇猛的動物,會攻擊人類,而且韌勁極強。
但其實,不論是豺狗還是天鵝,都有著各自存在的意義,在他們身上所貼有的或真或假的標簽,都是人類投射的自己的影子。而契訶夫的戲,抑或是探索頻道的動物王國,其實都在不同程度上向觀眾展示著生與死的艱辛與孤獨,還有宿命的意義。
電影《解救吾先生》選擇了一首老歌作為主題曲,劉家昌作曲的《小丑》,由劉德華演唱。歌詞中這樣幾句:掌聲在歡呼之中響起,眼淚已涌在笑容里;啟幕時歡樂送到你眼前,落幕時孤獨留給自己。
對于未來,王千源并沒有特別的規劃。
“李默然伯伯有名吧?但其實過去遼寧人藝的好演員太多了,能出來,某種程度上 也是運氣。”
“隨遇而安。”這個在銀幕上將英雄和小丑雜糅在一起的男人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