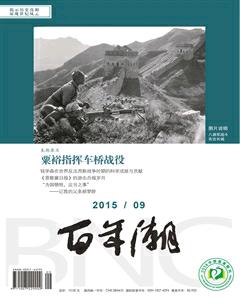錢學森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時期的科學成就與貢獻
汪長明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在這場曠日持久、災難深重的世界性戰爭面前,身處異域他鄉的錢學森,懷著對科學真理的不懈追求與竭力探索,以及對人類正義的堅定捍衛,以自己的聰明才智和滿腔心血,從一位愛國青年學子成長為著名空氣動力學家和應用力學家,在諸多科技領域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開創性成就,為現代航空航天科技發展和盟軍技術水平與戰斗力的提升,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及人類和平與進步事業作出了引人注目的科學貢獻。
立志航空救國,負笈大洋彼岸
1929年,錢學森從北師大附中畢業后,懷著振興祖國的堅定決心和交通救國的遠大理想,以優異成績考入交通大學。在校期間,1931年,日本法西斯精心策劃九一八事變。中國軍民奮起反抗,打響了世界反法西斯局部戰爭第一槍。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日本憑借飛機數量和性能上的優勢掌握了制空權,對上海狂轟濫炸,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遭受嚴重損失,中華民族處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錢學森耳聞目睹,痛感中國航空工業的落后及航空技術對國家安全的重要性,痛感中國必須擁有強大的航空工業,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為此,他決意為航空救國貢獻自己的力量,毅然將人生志向從交通救國轉向航空救國,并在大學期間密切關注航空技術的發展,選修了航空方面的課程,并撰寫、發表了多篇相關論文。
1934年,錢學森從交通大學畢業后,考取清華大學留美公費生,專業為飛機設計。1934年至1935年,錢學森按清華大學的規定先后到杭州、南昌、南京、上海等地的飛機制造廠和修理廠見習。清華大學指定我國航空事業的兩位先驅王助、王士倬為錢學森的導師。兩位導師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學術理念對錢學森影響至深。1935年8月,錢學森懷著航空救國的遠大理想,從上海黃浦江碼頭登上“杰克遜總統”號郵輪,赴美深造。出國前夕,親朋好友紛紛寄語留念,寄托美好祝愿和期望。錢學森的表哥章鏡秋在留言本上寫道:“他日學成歸來,于祖國防空政策自必有偉大之貢獻。”臨行前,錢學森說道:“現在中國政局混亂,豺狼當道,我到美國去學技術是暫時的,學成之后,一定回來為祖國效力。”
1935年9月,錢學森進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攻讀航空工程。次年9月,錢學森從麻省理工學院畢業后,進入加州理工學院航空系,在世界著名力學大師馮·卡門教授指導下,從事航空理論和應用力學的學習研究。
留美期間,錢學森一直心系祖國航空事業的發展。1938年6月7日,他就延長公費留學期限一事致函清華大學校長辦公處,表達了日后學成歸來報效祖國的迫切愿望:“如能在馮·卡門教授門下再有一年之陶冶,則學生之學問能力必能達完善之境,將來歸國效力必多。”
探索科學前沿,攻克學術高地
二戰爆發前后,錢學森經過不懈探索,取得了非凡的學術成就,解決了空氣壓縮效應、熱障、薄殼失穩等當時航空界面臨的難題,為高速空氣動力學作出了重要貢獻,也為日后回到祖國奠定了堅實的學術基礎。

二戰前夕,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和軍事競爭的推動,制空權理論引起現代軍事技術和軍事工業的革命性變化,航空界開始由低速飛行向高速飛行發展。但受當時技術條件制約,需要解決眾多極具挑戰性的科學問題。飛機在接近音速飛行的過程中,由于空氣可壓縮性產生的累積壓力引起飛機尾翼蒙布皺折,導致機身強烈震動并失去平衡,嚴重時曾多次發生機毀人亡事故。當時航空學界迫在眉睫的難題之一是如何改進飛機外形設計以消除空氣壓縮效應對高速飛行的影響。
1939年,錢學森在導師馮·卡門教授指導下,經過深入細致的研究,提出計算飛機翼面壓力分布的空氣壓縮作用修正理論公式“卡門-錢近似”,其理論成果是他于1939年在美國《航空科學》雜志發表的《可壓縮流體的二維亞聲速流動》一文。這一公式的發表使他一躍成為世界著名的空氣動力學家。在二戰期間以及戰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在現代計算手段(電子計算機)出現以前,這一近似計算方法通過大量亞音速風洞實驗,直到最大局部速度達到臨界馬赫數,鑒定結果相當準確,被廣泛應用于飛機翼型的設計,在當時直接對飛機的設計起了重要作用。美國航空航天領域資深科學家弗蘭克·馬勃教授認為,在快速、經濟的數值計算方法出現之前,“卡門-錢可壓縮性修正”一直是最準確的計算公式。
20世紀30年代,航空技術取得顯著進展,隨著戰爭對軍用飛機速度要求的不斷提高,全金屬應力蒙皮結構和大推力發動機成為飛機研制的主流技術。全金屬結構具有重量輕而強度高的優點,但當其受到的載荷超過某一數值時,殼體會發生皺癟而失效,這種現象稱為屈曲。如果采用經典的線性理論計算,發生屈曲的臨界載荷值比實驗值要大許多。飛機設計師需要精確地計算出發生這種現象時殼體的具體載荷,但經典的薄殼理論卻不能提供有價值的指導,在理論和實驗之間存在一個不為人知的大誤差,這使工程師陷入沒有理論可循的困惑境地。如何解決帶曲率薄殼結構的穩定性,即薄殼失穩問題成為困擾航空學界多年的一個不解之謎。
錢學森在系統分析前人的理論和實驗工作之后,從1939年開始著手解決薄殼失穩問題。1940年,他與馮·卡門發表《球殼在外壓屈曲》論文,提出計算屈曲臨界載荷的能量躍變準則,從理論上解決了臨界載荷矛盾和受壓球殼屈曲失效這一航空界久攻不克的難題。這一重大學術成果不僅在理論上對當時的力學界和航空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而且在實踐上為多家飛機公司設計部門所采用。專家們普遍認為,錢學森關于屈曲臨界載荷的計算結果接近實驗值的臨界判斷,這一理論很快被學術界和工程界所接受;這篇論文堪稱20世紀板殼非線性力學的開創性論文。
第二年,錢學森與馮·卡門發表《圓柱殼在軸壓下的屈曲》論文,準確推導出圓柱殼屈曲的臨界載荷的特征方程。著名空氣動力學家、中國工程院院士莊逢甘指出,錢學森關于屈曲臨界載荷的研究成果與實驗符合得很好,很快為飛機公司所引用;這些成果不僅在學術上有很大影響,而且在實踐上為多家飛機公司的設計部門所采用。
參加火箭研究,助推短距起飛
二戰前夕,錢學森以巨大的勇氣和科學遠見,參加了被稱為“自殺俱樂部”的加州理工學院火箭研究小組,為戰爭期間美國火箭助推起飛技術的發展、扭轉太平洋戰爭戰略格局奠定了堅實的理論與實踐基礎。1936年2月,馬里納、帕森斯和福爾曼三位加州理工學院學生成立加州理工學院火箭研究小組。1937年,錢學森加入該小組,負責研究燃燒室、噴氣推力和火箭性能的理論問題。
在參加火箭研究小組期間,錢學森做了大量理論研究工作。1937年5月,錢學森完成《火箭發動機噴管擴散角對推力影響的計算》一文。同年5月,他還向火箭小組提交了一份研究報告,具體描繪出一個燃燒室和廢氣噴嘴大小都固定的理想火箭的理論模型。不久,該報告被收入火箭研究小組的論文集。該論文集被小組成員視為“圣經”,成為他們研究火箭研究和計算的重要基礎。1937年6月至9月,錢學森做了有關火箭研究文獻資料的調查研究,并在自己的博士論文中,通過探討和論證以逐次推進的固體火藥作為推進劑,進行多次快速燃燒排氣而獲得脈沖式推力的火箭發動機燃燒方案,從理論上證明探空火箭可以達到10萬英尺的飛行高度。
火箭研究小組卓有成效的開創性工作引起美國科學界的廣泛關注。1939年1月,美國國家科學院接受馮·卡門的建議,決定在加州理工學院設立火箭研究中心,以解決火箭助推飛機起飛問題,并劃撥1000美金研究經費予以支持。火箭研究小組的命運由此預示著即將掀開新的篇章。

加州理工學院是美國最早開展火箭技術研究的機構之一。在二戰時期,該校的噴氣推進實驗室已發展成為美國火箭導彈技術的一個重要研發中心。戰爭期間,錢學森參加了由美國軍方資助的加州理工學院火箭助推起飛裝置研究計劃及其他軍工項目,為噴氣推進技術和高速空氣動力學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由于馮·卡門的推薦,火箭研究工作開始得到美國航空工業界、陸軍航空兵和政府的重視。1938年5月,美國陸軍航空兵司令亨利·阿諾德上將訪問加州理工學院古根海姆實驗室時,對火箭研究給予特別關注。由于預見到世界大戰不可避免,阿諾德要求加州理工學院研制火箭助推起飛裝置,使美國軍用飛機,特別是重型轟炸機能從航空母艦及太平洋小島的短跑道上起飛。為此,阿諾德與加州理工學院簽訂了協議,并給予了經費資助。
1939年初,美國國家科學院撥款資助在加州理工學院設立火箭研究中心,工作重點是研制重型飛機的火箭助推起飛裝置,而二戰的爆發更使整個火箭計劃出現了新局面,特別是在固體推進劑的研究方面。同年,火箭研究小組制訂了美國陸軍航空兵第一個火箭研究計劃—“古根海姆1號”。1941年,該中心在阿羅約·塞科河谷建造了第一批實驗室,并成功進行了美國首次噴氣助推起飛和單純以火箭為動力的有人駕駛飛機飛行試驗。當年8月12日,一架執行本次飛行任務的飛機從加利福尼亞馬奇機場順利起飛。這是美國轟炸機第一次采用固體火箭動力裝置起飛。據馮·卡門回憶,飛行試驗結果遠遠超出最佳期望:本次試驗表明,“噴氣助推起飛能使跑道縮短一半,這意味著重型轟炸機能夠在更短的跑道上起飛。”同年,美國國家科學院不僅繼續向加州理工學院提供研究基金,還從1942年財政年度開始,將資助金額總數提高到12.5萬美元。
1942年4月15日,馮·卡門、錢學森、馬里納等火箭研究小組成員在摩哈維沙漠中的慕洛克空軍基地成功進行了道格拉斯A-20轟炸機火箭動力裝置起飛試驗,標志著美國第一個火箭助推起飛裝置研制成功。這種重型轟炸機火箭助推起飛裝置很快就在太平洋戰爭中被美國空軍廣泛應用。錢學森在其研究、設計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面對法西斯的瘋狂肆虐,馬里納高興地說:“我們現在可有了真正管用的東西,應該可以把法西斯主義者們送到地獄里去了!”馮·卡門指出,A-20火箭助推起飛是美國轟炸機第一次采用固定的火箭動力裝置起飛,標志著美國實際應用火箭的開始。
洛杉磯《帕薩迪納星報》1950年1月的新年專版,對包括錢學森在內的該校科學家在二戰時期的工作,尤其是噴氣推進實驗室的火箭研究給予了充分肯定。據該報報道,加州理工學院噴氣推進實驗室是美國當時唯一的此類實驗室,在二戰期間向美軍提供了超過90%、總值約8000萬美元的火箭武器裝備。
為了成批量向美國軍方產銷火箭助推器,火箭研究小組于1942年創辦了航空噴氣公司,馮·卡門任總裁,錢學森任顧問。隨著戰爭規模不斷擴大,美國軍方對加州理工學院火箭及相關研究成果的資助迅猛增長,公司大量生產裝備航空母艦艦載戰機的火箭助推器。錢學森在其中的研究、設計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1943年,錢學森與馬里納合作完成《長程火箭的評論和初步分析》研究報告,提出了三種火箭導彈的設計思想,為地地導彈和探空火箭研制奠定了理論基礎。這是美國導彈計劃的第一份正式記錄,被譽為“美國導彈先驅”。同年12月20日,馮·卡門、錢學森和馬里納共同提出了一項被稱為“JPL-1”的美國遠程火箭導彈研究計劃。作為這一計劃的產物,1944年1月,美國陸軍炮兵部向加州理工學院噴氣推進實驗室提出“炮兵部和加州理工學院聯合計劃”,請求加州理工學院噴氣推進實驗室盡快研制可以用于實戰的導彈,并對導彈的性能提出了要求。同年,錢學森等火箭研究小組成員制訂了研制帶發射架的遠程導彈計劃。
馮·卡門在他的回憶錄中高度評價了錢學森的科學成就:“錢作為加州理工學院火箭研究小組的元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美國的火箭研制作出過重大貢獻。”1946年2月13日,阿諾德上將在致錢學森的信中,表彰其在火箭和噴氣推進等領域作出了“巨大而無可估量”的貢獻。
從1940年起,因火箭研究計劃被美國政府列為高度軍事機密,錢學森作為僑民無法獲得參與資格,被迫退出火箭研究小組。直到珍珠港事件發生后,因中美戰略聯盟的需要才獲準錢學森參與美國機密研究計劃。1942年12月1日,錢學森獲得了安全認可證,獲準參加涉及軍事機密的工作。此前,錢學森于1940年為馮·卡門主持建造的加州理工學院一個彈道試驗用超聲速風洞完成了設計方案論證和分析計算,并為此撰寫了《彈道試驗用超聲速風洞的設計》論證報告。
錢學森獲得參與美國涉及軍事機密研究項目的資格后,陸續承接了美國軍方的多項研究任務,并向其提交了一系列研究報告:1943年,錢學森先后完成了一項關于高速飛行時XSC2D整流罩上方壓力分布的研究,一份關于使用噴氣機所產生的噴射力作為啟動液態推進泵能量來源的報告以及一份關于向固體推進劑中添加金屬固體以改善性能的可行性報告;1944年,他先后提出討論壓縮機或渦輪機中葉片變形所帶來的影響的報告,并為噴氣推進實驗室完成了一份關于平坦表面與高速氣流間熱轉換的論文。當年,錢學森還向美國陸軍航空兵提供了《遠程火箭的飛行特性》的內部報告,對遠程火箭的技術要求等進行了分析計算,并且提供了兩個實際算例。
指導飛機研制,培訓盟軍軍官
作為一名應用力學家,錢學森一直以理論分析和計算論證見長。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他不但時刻關注祖國航空事業的發展,與國內航空界保持密切聯系,還一度深入洛杉磯地區的航空企業,發現并解決飛機設計與生產過程中遇到的應用力學問題。這些飛機制造公司在二戰期間研發生產的先進戰機,為盟軍戰勝法西斯、贏得戰爭勝利發揮了巨大作用。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軍航空母艦艦載飛機和微型潛艇對美國在太平洋的海軍基地珍珠港以及美國陸軍和海軍在夏威夷歐胡島上的飛機場發動突然襲擊,美國太平洋艦隊損失慘重。12月8日,美國總統羅斯福簽署對日宣戰聲明;當日,美國國會通過正式對日本宣戰的決議,太平洋戰爭爆發。
二戰時期,美國的航空工業生產能力迅猛發展,航空從業人員由1939年的4.8萬人猛增到1943年的200萬人。飛機產能迅速提高,每年產量達到5萬架,戰爭期間生產的各種飛機總計20.44萬架。以洛杉磯為中心的南加州是美國航空工業最發達的地區之一,整個20世紀40年代,該地航空業迅速發展,從事飛機制造的工人人數從1939年的1.33萬人猛增至1941年的11.3萬人;為美國政府制造的飛機達10萬多架;飛機制造業為整個城市提供了40%以上的就業機會,被稱為“奇跡10年”。道格拉斯、洛克希德等著名飛機制造公司都集中在這一地區,生產了眾多代表當時美國乃至世界航空工業最高水平的先進戰機。例如,道格拉斯公司在二戰時期生產的SBD“無畏”式俯沖轟炸機在珊瑚海海戰和中途島海戰中重創日本艦隊,先后擊沉日本四艘航空母艦,為打破日本航空母艦的絕對優勢,扭轉太平洋戰場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整體戰略態勢立下了赫赫戰功。

1941年,時為密歇根大學工學院航空系研究員的周明鸂受馮·卡門邀請,參加加州理工學院古根海姆航空實驗室研究工作,并經常與錢學森一起探討學術問題。珍珠港事件發生后,周明鸂于1942年到道格拉斯飛機制造公司工作,任高級工程師。在此期間,錢學森曾一度去道格拉斯公司,與他一起研究解決飛機設計中遇到的力學問題,從而間接地參加了中美共同抗日的行列。
培訓盟軍軍官,提高指揮能力。二戰后期,錢學森除了參加美國軍方的保密項目外,還為美國政府選派至加州理工學院攻讀航空學碩士學位的空軍和海軍軍官講授課程,并親自編寫教材,為戰時培養美軍第一批火箭和噴氣推進領域軍事技術干部,提高盟軍軍事指揮能力作出了很大貢獻。
為了強化軍隊的技術知識,美國軍方于戰爭后期開始遴選一批軍官到加州理工學院學習。陸軍航空兵空軍技術后勤司令部要求加州理工學院為1943至1944學年派往該學院的一批軍官提供火箭與噴氣推進方面的研究生課程。馮·卡門和他的加州理工學院古根海姆實驗室和噴氣推進實驗室的同事制定了課程。1944年,錢學森受聘主講《工程數學原理》和《噴氣推進理論》兩門課程,并組織、編輯了內容豐富的教材《噴氣推進》,全面論述噴氣推進的基本原理和噴氣推進飛行器的性能。這是美國第一部全面系統論述噴氣推進基本原理和火箭性能與科技的專著,成為以后十幾年間不可或缺的參考書。
美國專欄作家米爾頓·維奧斯特對錢學森的科學成就給予了高度評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錢的幫助下,大大落后于德國的非常原始的美國火箭事業過渡到相當成熟的階段。他對建造美國第一批導彈起過關鍵性作用。”“錢一直被公認為世界上航空科學領域最具獨創見解的學者之一……他是馮·卡門雄心壯志與事業的繼承者……是幫助美國成為世界第一流軍事強國的科學家銀河中一顆明亮的星。”
隨團赴歐考察,科學捍衛和平
1944年12月1日,美國國防部科學咨詢團成立,馮·卡門任團長。咨詢團的任務是評價航空研究和發展的趨勢,為美國國防部準備有關科學技術事務的特別報告。由于錢學森為美國火箭研制作出過重大貢獻,“他的研究工作大大推動了高速空氣動力學和噴氣推進技術的發展”。于是,馮·卡門推薦他為咨詢團成員。1944年底,錢學森辭去加州理工學院各項職務,赴華盛頓參加美國國防部科學咨詢團的工作。佩戴國防部科學咨詢團成員身份證及出入證的錢學森得以進入美國軍事科學與國防科研最高智囊機構。
1945年3月,德軍在歐洲戰場全面崩潰,盟軍勝利在望。同年4月底,錢學森以美軍上校身份,身著美軍制服,隨馮·卡門率領的國防部科學咨詢團一行36人,赴歐洲考察德、英、法等國在航空和火箭領域的研究情況,重點是考察德國的高速空氣動力學研究、脈沖噴氣發動機和渦輪噴氣發動機的發展以及火箭與導彈的技術情況。錢學森一行先在德國薩克森州東部小城不倫瑞克考察。戰爭期間有上千名德國科學家曾在該地的戈林空氣動力學研究所從事火箭研究工作。
5月5日,錢學森在慕尼黑附近的小鎮科赫見到了德國火箭研究最高權威馮·布勞恩。應錢學森要求,馮·布勞恩寫出《德國液態推進火箭的發展與未來展望》的書面報告。這份報告受到了美國軍方的重視。此后,錢學森與馮·卡門在哥廷恩會見了馮·卡門的導師、近代流體力學奠基人、德國火箭研究工作的主要領導者、被譽為“空氣動力學之父”的普朗特,了解到德國火箭研究的技術問題及進展情況。此外,錢學森還詢問了研究V-2火箭的著名理論家赫爾曼·奧伯特等人,并視察了美軍發現的德國布倫茨威格秘密實驗室和諾德豪森V-2火箭工廠,查閱了德國火箭和空氣動力學的秘密研究報告,對德國導彈研制計劃進行了深入細致的了解。
錢學森在德國考察期間,于5月17日至21日寫出了一系列反映戰時德國在飛機、火箭、炸彈等領域發展狀況的調研報告。包括《箭形機翼》《火箭》《超聲速氣體動力學》《沖壓發動機》《脈沖式空氣噴氣發動機》《液體炸藥炸彈》《飛機上的噴氣渦輪發動機的安裝》等。
經過長達數年血與火的洗禮,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同盟國的全面勝利告終。1945年5月7日,德國無條件投降儀式在柏林舉行,標志著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爭的結束。8月15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9月2日,日本簽署無條件投降書。中國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經過十四年浴血奮戰,中國人民終于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9月9日,中國戰區受降儀式在南京舉行。
毅然回歸祖國,譜寫科學新篇
錢學森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時期取得了科學上的巨大成就,為這場戰爭的勝利作出了獨特的貢獻。然而,由于國際政治風云變幻,冷戰隨之而來及美國麥卡錫主義盛行,錢學森被無情地卷入了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偏見的政治漩渦之中,在回國的道路上遭遇了漫長的不公平對待。從1950年到1955年,錢學森為爭取回國身陷囹圄、備受屈辱,遭受了漫長的身心迫害。在此期間,他懷著對科學的無限執著和報效祖國的堅定信念,轉向并潛心從事工程控制論、物理力學等前沿領域的研究。1954年,錢學森出版自動化領域劃時代著作《工程控制論》并贈與自己的恩師兼學術上的親密合作者馮·卡門。馮·卡門看后百感交集,千言萬語化作一句話:“你在學術上已經超過了我。”
回憶爭取回國這段艱難的經歷,錢學森曾說道:“我實際上是被美國當局驅逐出境,押送回國的。這一段歷史我絕不會忘記。它使我深深懂得了什么叫帝國主義。我也領教了美國的民主和自由,深知美國的民主是什么樣子。”“我是中國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國住一輩子。”
經過不懈抗爭,在黨和政府的親切關懷和幫助下,1955年9月17日,錢學森終于沖破重重阻力,踏上了回歸祖國的航程。錢學森回國后,作為技術負責人,在領導我國火箭、導彈和航天事業的歷程中,用自己的赤子深情和卓越才智,譜寫了嶄新的科學篇章,為中國航天事業和國防現代化建設,為中華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今年適逢錢學森回國60周年。作為一位科學家,能將自己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如此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這是錢學森個人的幸運,也是他的祖國的幸運。(編輯 楊 琳 王 雪)
(作者是上海交通大學錢學森圖書館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