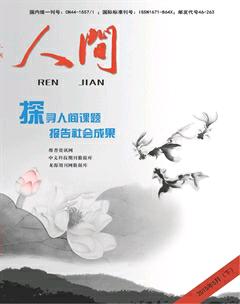論《邊城》人性美所導致的悲劇
楊文靜
(陜西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陜西 西安 710000)
論《邊城》人性美所導致的悲劇
楊文靜
(陜西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陜西 西安 710000)
沈從文的代表作《邊城》是作者表現理想人性的經典性作品,被許多讀者看作是“人性善的杰作”,而男女主人公的悲劇也被認為是一個似乎“誰也沒有錯”的悲劇。《邊城》的悲劇性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邊城》中人們看似理想的人性美實則是導致翠翠與儺送愛情悲劇的潛在因素。正是因了人性中善的一面,這樣的悲劇才更能引起讀者對“美”的毀滅的深沉思考。
邊城;人性美;悲劇
引言
沈從文的代表作《邊城》,以30年代湘西邊境山城茶峒為背景,寫了一個渡船老人和她的外孫女翠翠的生活經歷以及船總順順兩個兒子天保和儺送與翠翠的曲折愛情故事。小說圍繞這個故事,對邊城富有特色的山川景物、風土人情作了詩情畫意的描述,把湘西樸實的民風及獨特環境中的淳樸、親善、寧靜、和諧的人性美表現的淋漓盡致。但是在這部近乎天籟的田園牧歌式小說中,卻始終彌漫著一層淡淡的憂傷與哀愁,出現了天保身亡、儺送出走、祖父在一個雷雨交加的夜晚離世、翠翠看似順乎自然的愛情以悲劇告終的結局。沈從文在《水云》中關于《邊城》的表述中說:“一切充滿了善,充滿了完美高尚的希望,然而到處是不湊巧。既然是不湊巧,因之樸素的良善與單純的希望終難免產生悲劇。①”作者這句話的意思很顯然的,因了人性中善的一面,這樣“美”的事物的毀滅的悲劇便產生了。
一、邊城居民的人性美
沈從文在《邊城》中塑造的湘西人,是火辣的、原始的、完全依靠人性原則生存的生命形態。他們熱情誠實,人人均有古君子遺風。“一切莫不極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居樂業。②”無論是老船夫、翠翠、船總順順、天保、儺送,還是過渡的商客、吊腳樓上的妓女等人物,無一不是真真實實的生活著,構成了近似大同社會的理想社會。《邊城》中的湘西人的人性美,主要是從生命的健康自然美、品格高尚美和人與人關系的和諧美三方面來表現的。
(一)生命的健康自然美
這一點從兩方面表現出來:一是體魄、容貌的自然美;二是愛情的自然美。《邊城》中的年輕人因在自然的風日里長養著,故身體強壯、健康,具有蓬勃的生命活力。如寫天保和儺送,說他們“結實如小老虎③”,寫儺送的長相,說是“儺送美麗的很。茶峒人拙于贊揚這種美麗,只知道為他取出一個諢名‘岳云’”。④描寫翠翠,說她“為人天真活潑,處處儼然如一只小獸物。人又那么乖,如山頭黃麂一樣,從不想到殘忍事情,從不發愁,從不動氣。”從這些話語中不難看出,作者對于他們身上所具有的動物般的靈性充滿深深的贊譽之情,而對于翠翠相貌的描寫,也深具自然之美,說“翠翠在風日里長養著,故把皮膚變得黑黑的,觸目為青山綠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⑤這樣的描寫,仿佛翠翠是從那山林中走出的自然女神。愛情的自然美體現在翠翠對于愛情的初體驗和儺送對于翠翠不摻雜任何功利色彩的愛情上。翠翠是一名鄉村少女,她沒有多少文化也沒有母親的教育和引導,她對愛情的萌發完全是出自天性和本能。作品中寫了翠翠的三次端午節,第一次,與儺送相遇,產生一種朦朧情感;第二次,儺送下了清浪灘,已引起她對儺送的思念;第三次,與儺送在賽龍舟活動中相見,這時的感情已經明晰和堅定。而儺送對翠翠的愛也是純粹的、發自內心的愛。在他面臨對碾坊和渡船的選擇時,他明確表示選擇渡船,并且他對天保說愿意為翠翠唱三年六個月的情歌。作品在凸顯他們二人的愛情時,同時突出描寫了儺送的深情和翠翠的天性和本能之愛,這種愛是自然而然的且充滿身神性的。
(二)人的品格高尚美
《邊城》中的湘西人在作者筆下,具有誠實勇敢、樂善好施、熱情豪爽、守信重義的優美品格。如渡船老人守渡船,活了七十年,從二十歲起便守在這渡船上,五十年來不知渡了多少人。他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從不思索自己職務對于本人的意義,只是靜靜的很忠實的在那里活下去。”⑥當遇到過渡人要付錢時,他便吵嘴似的申明:“我有口糧,三斗米,七百錢,夠了!誰要你這個!”⑦船總順順疏財仗義、扶弱濟困、正直公平,如船工在水上出事,他常常送錢周濟,船工們鬧糾紛,請他來裁奪,他也總能給出公平圓滿的解決辦法。其他的人比如天保、儺送、翠翠也都是誠實正直的人。甚至就連妓女,也是淳樸、渾厚的,“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較之知羞恥的城市中人還更可信任。”⑧
(三)人與人關系的和諧美
這種和諧美不僅體現在窮人和富人之間,還體現在朋友之間。順順是當地的富人,渡船老人是窮人,而他們都能平等相處,和諧往來。每次船夫到順順家,都能得到長輩般的尊重和款待,祖孫倆生活困難,順順還經常給他們送錢送物。體現在朋友間的便是邊城人對待朋友的肝膽相照。楊馬兵年輕時追求過翠翠的母親,未能如愿,但他并未計較,與老船夫常來常往,甚至還成為忘年交,船夫去世后,他主動擔負起照顧翠翠的職責,與翠翠一起等待儺送歸來。
沈從文稱:“我要表現的是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⑨可見,沈從文在《邊城》里展示了一種理想愛情:真正的合乎人性的純粹的神圣的愛情,而并非世俗之愛。因此,作者所展示的《邊城》中的人物,都是具有“人性美”和“人情美”的理想人物,但作家卻并未給他們安排一個“美”的結局,小說中的人物在田園牧歌式的環境中承受著悲劇命運。作品讀到后面,感覺心就像是被擰成疙瘩又舒展開來,上面還有尚未舒展的褶皺。就好比曾經見過天花亂墜的美,所以后來的滿紙濃愁,一片慘淡,才顯得格外觸目驚心。
二、人性美所導致的悲劇
當我們試圖從小說中尋找這種悲劇的根源時,就會發現這些悲劇的發生是極其自然的,都是出自各自的善意。
(一)翠翠父母的悲劇
翠翠父母的悲劇之處在于他們本來可以選擇逃走,但出于對人性中責任和孝道的考慮,他們沒有那樣做,不逃走的原因是因為“一個違悖了軍人的責任,一個卻必得離開孤獨的父親。”⑩他們的想法是善意的,但他們很少站在自己的立場上考慮問題,一個將軍人的責任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一個擔心父親會孤單,他們身上具備的都是茶峒人固有的品質:重情守義。但如果無法逃走,便又覺得辜負了愛情,他們夾在親情、愛情、責任之間難以選擇,因此不得不選擇死亡。所以,如果他們能將軍人的榮譽和孝悌之義看淡看輕一點,或許他們就可以攜手天涯雙宿雙飛了。他們的死亡一方面是極其悲壯和令人嘆服的,但另一方面他們的死亡又是極其輕率極不負責的,因為他們在舍生取義的同時,間接造成了翠翠的愛情悲劇。在翠翠的成長過程中,母親的教育和引導是極其重要的,在翠翠初次遭遇愛情時,如果母親還在,她最起碼可以從母親那里得到指點和啟示,沒有父母養育教導的翠翠,只在爺爺和一只黃狗的陪伴下,內心其實是非常孤獨的,這對她內向性格的形成有莫大關系。
(二)天保的死亡悲劇
天保的悲劇在于將愛情與尊嚴等同起來,得不到愛情因此心結郁積以致溺水身亡。個性豪爽、率直的天保喜歡翠翠,托媒說親一直得不到結果,被稀里糊涂的拒絕回來,他就怪罪老船夫,并缺少與老船夫和翠翠的直接交流。當二老問他有何打算時,他回答:“我想告那老的,要他說句實在話。只一句話,不成,我跟船下桃源去了;成呢,便是撐渡船,我也答應他。”作者在此安排大老的死即是偶然也是必然,偶然之處在于“常在河邊走,哪能不濕鞋”,跑船的人風里浪里的出入出事也是常事,作品中一句“什么都來不及說!這幾天來他都不說話!”暗含了大老并未真正放下此事,體現了大老重情的一面。必然之處在于作者其實是有意安排大老的死,為翠翠和儺送的愛情除去人為因素的羈絆,以此展示郎有情妾有意的美好愛情潛在的因了人性美而導致的悲劇。
(三)老船夫郁郁而終的悲劇
老船夫的悲劇之處在于對翠翠的過分關愛和百依百順使得好事變成了壞事。勤勞樸實、忠于職守、任勞任怨、樂善好施的老船夫,因為女兒女婿的悲劇使得他心里留下不可磨滅的傷痕,也使得他對相依為命的外孫女多了一份更多的關愛和憐愛。他對翠翠“溫和悲憫的笑著”,表現了他內心的矛盾與不安,他一方面想讓孫女嫁給她自己所喜歡的人,一方面又怕她走她母親的老路。當船夫錯把唱了一晚上歌的人認為是天保并向他道賀時,卻不想遭到了天保的冷語和嘲諷,翠翠看出爺爺臉色難看,他卻“莞爾一笑,他到城里的事情,不告給翠翠一個字”。后來天保意外溺水身亡,老船夫因擔心孫女的未來和歸宿,又仿佛自我譴責似的將天保的死歸到自己身上,并無法像從前那樣坦然的面對順順和二老,以至于引起順順和二老的反感。二老不僅在言語神氣間表現出對老船夫的不滿,語含譏諷,甚至在與別人談及問題時,更是把大老的死歸罪于老船夫,“……至于我呢,我想弄渡船是很好的。只是老家伙為人彎彎曲曲,不利索,大老是他弄死的”。后來又因了中寨人做媒不成,心生嫉妒,在老船夫面前不但說謊說二老要碾坊不要渡船,還提起大老的死,戳老人的痛處,這些都成為了加速老人死亡的催化劑。老人在抑郁之死前仍在為孫女的幸福做努力,但他心里的苦悶又不能向人提起,因此他只能帶著無比的遺憾和對翠翠的不舍而離去。
(四)翠翠和儺送的愛情悲劇
翠翠和儺送的愛情悲劇是整部作品中最顯而易見且最讓人痛心的悲劇,造成翠翠悲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翠翠自身的性格缺陷因素卻是最關鍵的因素。花季少女翠翠“平時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對她有所注意時,便把光光的眼睛瞅著那陌生人,作成隨時皆可舉步逃入深山的神氣,但明白了前面的人無機心后,就又從從容容的在水邊玩耍了”。這很明白的告訴讀者,翠翠為避免傷害,對自己周圍的世界保持著高度警惕,而這顯然能說明翠翠那謹慎、敏感、羞澀的個性特點。翠翠在第一個端午節與儺送相遇后,“心里又吃驚又害羞,”且“但另一件事,屬于自己不關祖父的,卻使翠翠沉默了一個夜晚”。第二個端午節遇見了大老卻未見二老,翠翠在回家的路上向爺爺發問“爺爺,你的船是不是正在下清浪灘呢?”此時的二老就是在清浪灘過的端午。可見翠翠的心是屬于二老的,但她卻不對爺爺說起,只是一個人守著自己的心事和秘密。翠翠性格中羞澀、矜持的一面還表現在當她與二老正面接觸時她不懂抓住機會而是將機會白白放走。如二老給祖父送酒葫蘆,到翠翠家中做客,“客人又望著翠翠笑,翠翠仿佛明白為什么被人望著,有點不好意思起來,走到灶邊燒火去了”。待爺爺喊她待客時,她卻反而有意裝聽不到。再如二老從川東押貨物到了茶峒,時間已近黃昏,翠翠聽人喊過渡,就爭先走下溪邊去,待看清是儺送和他家中的長年,便“同小獸物見到獵人一樣,回頭便向山竹林里跑掉了”。翠翠這種害羞、矜持的性格在某種程度上而言表現出邊城少女淳樸、單純的一面,是女孩子特有的美好品質,但她的矜持在另一方面又使儺送搞不清她對自己的心意而喪失自信與勇氣。也就是說,翠翠的害羞、矜持與其說是美德還不如說是羈絆。而造成她這種性格的原因除了缺少母親關愛之外,還與邊城人人性美中的孤獨氣質有關。
邊城中邊民的生活是安靜的、祥和的,但這種寧靜祥和的氣氛和環境使得邊民的人性美之中一種與生俱來的孤獨的、憂郁的氣質,他們為人所推崇的人性美就來源于這種氣質。比如小說開篇就寫到:“四川過湖南去,靠東有一條官路。這官路將近湘西邊境到了一個名為‘茶峒’的小山城時,有一小溪,西邊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戶單獨的人家。這人家只有一個老人,一個女孩子,一只黃狗”。“他唯一的伙伴是一只渡船與一只黃狗,唯一的親人便是那個女孩子”。這種孤獨感隨之引發的便是寂寞。“一切總那么靜寂,所有人民每個日子皆在這種不可形容的孤獨寂寞里過去。一份安靜增加了人對于‘人事’的思索力,增加了夢。”。這種深深的孤獨感必然造成邊民過于內傾的性格特質,一方面使得邊民性格中多了一份含蓄與淳樸,另一方面又造成他們無法與他人順暢交流內心的體驗和情感,缺乏對自我主體意識的探究。因此,當翠翠后來從楊馬兵那里得知天保之死是因為得不到她的愛而由于出走落水身亡,儺送是因為得不到她的愛而離鄉遠行,也明白爺爺是由于替自己的幸福思慮奔忙而心力交瘁離世,明了了這種種的一切之后,她才如夢初醒的“哭了一個夜晚”。這一切都說明翠翠在她的愛情中主體意識的缺失是非常明顯的,她的矜持使她被動的而不是主動的、迷茫的而不是明確的面對自己的愛情,這種含蓄矜持實則使她葬送了自己的愛情。
三、結語
這部唯美而又哀傷的小說,先是塑造了一大群真實純粹的人,而后又一點一點將人的美夢撕碎,就像是曾經見過天花亂墜的美,所以后來的滿紙濃愁,一片慘淡,才顯得格外觸目驚心。就像魯迅所說:“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作者就是讓讀者從美好女子得不到美好愛情這一過程所產生的巨大落差中體會到美好事物被毀滅的心痛與惋惜,從而達到悲劇的心理共鳴。
注釋:
①沈從文.水云[A]沈從文全集(第十二卷)
②沈從文《邊城》人名文學出版社2000.7 第十三頁
③沈從文《邊城》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0.7 第十三頁
④同上
⑤沈從文《邊城》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0.7 第五頁
⑥沈從文《邊城》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0.7 第五頁
⑦沈從文《邊城》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0.7 第四頁
⑧沈從文《邊城》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0.7 第十一頁
⑨沈從文《習作選集代序》[A]沈從文全集(第九卷)北岳文藝出版社 2002.5
⑩沈從文《邊城》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0.7 第五頁
[1]沈從文 《邊城》[M]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0.7
[2]沈從文 《從文自傳》[M]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3]沈從文《水云》[A]生之記錄 京華出版社 2005.7(第328頁)
[4].沈從文《習作選集代序》[A]生之記錄 京華出版社 2005.7
[5]《沈從文<邊城>悲劇成因探析》 周紀煥[J]河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5卷第4期(第62—66頁)
[6]《牧歌背后隱藏的矛盾及其悲劇性——重讀沈從文<邊城>》 魏家文 理論月刊[J]2004年第6期(第127—129頁)
[7]魯迅《再論雷峰塔的倒掉》[A]魯迅作品精選 光明日報出版社 2009.2
I206.6
A
1671-864X(2015)05-0017-03
楊文靜(1988.09-),女,陜西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2014級碩士研究生,方向:文藝與文化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