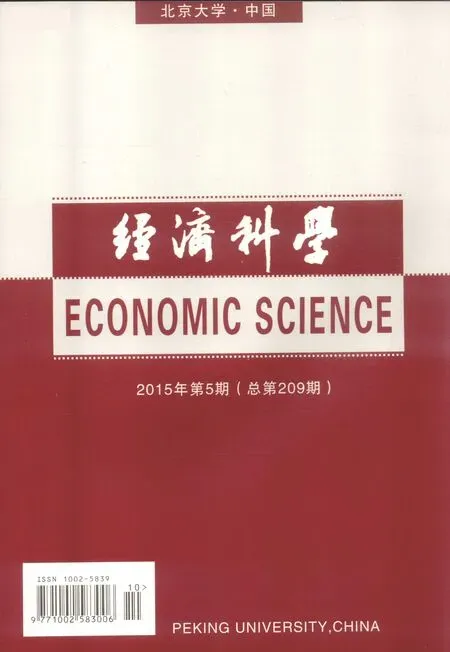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邊際效應遞減內在機理研究*——基于“兩部門劃分法”的理論框架
李 成 張 琦
?
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邊際效應遞減內在機理研究*——基于“兩部門劃分法”的理論框架
李 成 張 琦
(西安交通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 陜西西安 710061)
本文通過擴展“兩部門劃分法”構建了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理論模型,研究發現,由于金融部門在發展過程中對實體經濟資源的擠占以及金融部門自身發展過程中規模經濟遞減規律的存在,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最終會表現出顯著的非線性特征。實證結果顯示,在較長的時期內中國金融部門規模擴張對經濟增長具有持續的正向效應,然而在2008年之后卻反而抑制了經濟的增長。而且,盡管金融結構在整個樣本區間內得到了一定優化,但仍小于本文所測算的最優值。本文認為,只有通過提高直接融資的比例,加快金融結構優化,全面完善資本市場建設,才會取得更為理想的效果。
金融發展 經濟增長 效應分解 非線性激勵
一、引 言
長期以來,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內在作用機理一直為學術界關注的焦點。相關的理論研究可以追溯至Schumpeter(1912),其提出功能良好的銀行通過向最有機會在創新產品和生產產品過程中獲得成功的企業貸款,從而通過技術創新途徑促進經濟增長。之后,Patrick(1966)在研究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時將金融發展分為“需求尾隨型”和“供給推動型”。他認為,在經濟增長的起步階段,金融引導經濟增長;而當經濟進入快速增長階段,經濟結構變得日益復雜,此時經濟中的摩擦會對金融服務產生需求,并刺激金融發展。此后,學者們圍繞著這一標志性成果展開大量深入的研究,最終形成三種代表性的金融發展理論:第一種以Goldsmith、Mckinnon和Shaw為代表,系統闡釋了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第二種以Romer和Levine為代表,其最大貢獻則是在第一種理論的基礎上引入了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第三種以La Porta為代表,主要強調制度、法律等外生性因素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影響。按照不同的理論分析框架,國外學者們也通過各種實證研究揭示了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用。Demetriades和Hussein(1996)考慮到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可能是相互影響的對稱關系,運用2SLS(兩階段最小二法)檢驗了兩者間的關系,結果表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正向相關關系。Levine和Zervos(1998)利用47個國家1976-1993年間的跨國面板數據,發現金融發展與其后18年的經濟增長率、資本積累率和生產率的增長率均存在著顯著正相關。Levine和Loayza(2000)運用動態面板數據的GMM估計和2SLS估計,發現金融中介發展與經濟增長存在顯著正相關,但內生性問題的影響顯著。Michael(2009)通過實證分析得出發達國家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有較強的正向關系而發展中國家金融弱化問題普遍明顯。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進入一個飛速增長的階段,與此同時,金融改革也在平穩有序的推進,一方面為經濟的增長提供了強勁的動力,另一方面也有學者提出關于中國金融部門對實體部門利潤過度盤剝的質疑,認為一旦這種趨勢持續加劇將造成中國金融部門與實體經濟的脫節,金融部門的“本質功能”終將產生問題。隨著現實背景的不斷轉變,一系列相關的研究也在不斷地深入開展。趙振全、于震和楊東亮(2007)運用門限模型發現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較為顯著的非線性關系。張赫、黃琨等(2012)等運用線性模型研究了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發現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有著明顯的促進作用。周麗麗、楊剛強等(2014)通過β收斂模型對中國區域經濟增長速度和區域金融發展速度進行經驗比較分析,發現中國金融發展收斂速度遠大于經濟增長收斂速度。李春霞(2014)以上市公司為微觀基礎,驗證了中國金融發展能夠有效緩解企業的融資約束,進而促進經濟增長
縱觀國內已有研究,大多主要在國外理論研究的基礎之上,選取不同的指標體系進行實證分析,或者對原有模型或者指標進行進一步修正,抑或選取某一不同的視角簡單地將金融信息引入至經濟增長之中。本文通過理論與實證兩個方面對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內在影響機理進行不同層面的剖析。在擴展兩部門法的基礎之上構建了本文的理論模型,首次將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細分為“直接作用”、“溢出效應”和“擠出效應”三個方面,通過對這三重影響的交互作用進行剖析,更為深入地刻畫了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內在作用機理。論文對這一效應進行了實證檢驗,在非線性分析的基礎之上測算了中國金融發展的最優結構。本文內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從理論層面探討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機制;第三部分,實證檢驗中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非線性關系;最后得出了本文的結論與建議。
二、理論分析
“二部門劃分法”首先由Feder(1983)提出,用以分析出口部門擴張(另一個部門被定義為非出口部門)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隨后,兩部門模型被引入至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研究之中(Radha,2003)。基于“二部門劃分法”的思想,本文構建了一個包含金融部門和實際部門(非金融部門)的擴展兩部門模型,分析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作用機理,在所構建的理論模型中不考慮二者間內生性的問題,僅考慮金融發展如何影響經濟增長。金融發展實際上包括兩方面的含義,即金融部門規模的擴大(金融部門產出的增加)與金融部門結構的變化(Goldsmith, 1969)。為此本文做出如下假定:(1)社會只包含兩個部門:金融部門和實際部門,社會總產出由金融部門的產出和實際部門的產出共同構成;(2)金融部門和實際部門的產出都滿足一般生產函數的假定,依賴于各自的要素投入;(3)由于金融發展包括兩方面的內涵,金融發展對實際部門產出的影響亦涵蓋兩個方面:金融部門規模擴大對實際部門產出的影響與金融部門結構變化對實際部門產出的影響。
由于金融發展涵蓋兩方面內容,因此本文對金融發展的考量分為以下三種情況:一是金融部門的規模擴大,金融部門的結構不變;二是金融部門的規模不變,金融部門的結構變化;三是金融部門的規模與金融部門的結構同時發生變化。為了更為清晰地刻畫和分析金融發展對實際部門的影響,本文假設:(4)金融發展首先表現為金融部門規模的增大,然后才是金融部門結構的變化(抑或假設先是結構的變化,然后才是規模的變化,但這并不影響本文的分析);(5)金融部門規模的增大對實際部門產出的影響路徑為:金融部門的產出作為一種“要素投入”直接進入實際部門的生產函數,以反映金融部門規模擴大對實際部門的溢出效應(Odedokun,1996)。
分析金融結構變化的影響的前提為,對金融部門結構(實際上也就是不同類型的金融部門)特性的深刻把握。自Goldsmith開創性地提出金融結構的概念以來,后續的研究大多圍繞“金融二分法”和“金融功能視角”展開,但二者的本質相同,因為金融功能勢必需要通過金融中介或者金融市場加以體現,而不同導向型也是為了更好地實現金融功能。由假定(5)可知,金融部門對實際部門的溢出效應是通過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得以實現的。考慮到金融部門主要是通過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兩種方式進行配置資源,那么基于上述關于金融結構的思想,可以提出假定:(6)金融部門的產出包括兩類:第一類部門,產出通過直接融資方式作用于實際部門;第二類部門,產出通過間接融資的方式作用于實際部門。由林毅夫,孫希芳和姜燁(2009)關于金融結構定義“金融體系內部各種不同的金融制度安排的比例及相對構成”,本文定義金融結構變量為“金融部門第二類產出與金融部門總產出的比值”(實際上我們也可以定義金融結構變量為“金融部門第一類產出與金融部門總產出的比值”,因為兩個比值在內涵上是一致的)。
基于以上假定,可以得到如下表達式:

(2)
(3)
其中,Y表示總產出,F表示金融部門的產出,R表示實際部門的產出;和分別表示金融部門的勞動投入和實際部門的勞動投入,和分別表示金融部門和實際部門的資本投入;STR表示金融結構變量。由于金融部門和實際部門的生產函數符合一般生產函數的假定,因此金融部門的產出與金融部門的要素投入有如下關系:,,,。實際部門的產出與其投入要素(金融部門的產出作為與勞動投入和資本投入并列的第三種要素投入)的關系如下:,,,,,。
為了考察實際部門的產出和金融結構變量之間的關系,需要區別直接融資方式和間接融資方式配置資源作用于實際部門的特點。由于兩種方式分別以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作為載體,因此只需考慮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配置資源的特點即可。既然直接融資方式和間接融資方式配置資源各有優劣,那么如果整個經濟社會中只存在單一的配置方式(或全部是直接融資方式配置資源,或全部是間接融資方式配置資源),則該金融結構必定不是最優。若以“金融部門第二類產出與金融部門總產出的比值”作為金融部門結構變量STR時(因為這個比值有一個良好的性質,即其取值范圍為[0,1]),就可以做出以下合理的假設,即當時,;當時,,其中為介于0與1之間的某個值。
并且勞動投入和資本投入之間滿足下列關系:

(5)
其中,L表示勞動投入總量,K表示資本投入總量。
(一)投入要素固定時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
為了便于理解,首先分析勞動投入L和資本投入K固定時,金融發展對社會總產出(經濟增長)的影響。由于社會總產出由金融部門的產出和實際部門的產出構成,因此對方程(1)兩邊取微分:

由(6)式可知,社會總產出的增加取決于兩個方面:金融部門產出的增加和實際部門產出的增加,那么研究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實際上就轉化為研究金融發展對金融部門產出和對實際部門產出的影響。由表達式(4)和(5)可知,當勞動投入L和資本投入K固定時,金融部門的勞動投入和實際部門的勞動投入以及金融部門的資本投入和實際部門的資本投入均存在著此消彼長的關系。與此同時,由金融部門生產函數的性質可知,金融部門產出的增加實際上意味著金融部門勞動投入和(或)金融部門資本投入的增加,可見金融部門要素(勞動和資本)投入的增加和金融部門產出增加在衡量金融部門規模擴大時,其內在的含義是一致的。

金融部門規模的擴大也即金融部門要素投入的增加能否帶來社會總產出的持續增加取決于和的符號,為此需要求出社會總產出關于金融部門勞動投入和資本投入的二階偏導:

(9)
由此我們可知,當金融部門規模較小時,金融部門規模繼續增大會促進經濟增長;當金融部門規模超過某個界限時,金融部門規模的擴大反而抑制經濟增長,也即金融規模與社會總產出存在著倒U型的關系。
進一步來講,我們發現對于給定的勞動投入和資本存量,金融部門規模的擴大對總產出貢獻最大時,如果按照傳統的關于金融部門邊際生產力和實際部門的邊際生產力,其中金融部門勞動投入的邊際生產力和資本投入的邊際生產力分別為和,實際部門的邊際生產力分別為和,那么金融部門的邊際生產力將會小于實際部門的邊際生產力,即,。
接下來考慮金融部門結構變化對社會總產出(經濟增長)的影響。由假定(4)可知,金融部門結構的變化并不會引起金融部門要素投入的變化②,那么在勞動和資本投入總量固定時,也就不會影響實際部門的要素投入。于是可以得到金融部門結構的變化對總產出的效應為:

由實際部門產出與金融部門結構的關系可知,社會總產出與金融部門結構之間也存在著倒U型關系,即當時,金融結構變量的增加會帶來社會總產出增加(促進經濟增長);當時,金融部門結構變量的增加反而引起社會總產出減少(抑制經濟增長)。其中表示最優的金融部門結構,其值介于0與1之間。
(二)投入要素變化時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
上述分析均是建立在勞動和資本投入總量固定的前提之上。然而實際中勞動和資本投入并非固定不變,因此接下來將考慮勞動和資本投入變化的情況下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認識到兩部門的勞動和資本投入可能存在邊際生產力的差異(實際上基于前述分析,若是金融部門規模擴大對總產出的總效應最大,金融部門的邊際生產力低于實際部門的邊際生產力,其差值為和),我們定義如下的關系式:

(12)

將(11),(12)和(13)式代入(6)式,經整理后有:
(14)

(16)

(18)

三、實證檢驗
(一)指標的選取與處理
從生產函數理論的角度,F應該選擇金融部門的產出,但是金融部門產出的數據獲取困難,因此我們不得不選擇其他指標進行替代。本文借鑒Goldsmith(1996)、周寧東(2007)以及武志(2010)的研究,選取“金融機構的金融資產總規模”作為衡量金融部門規模的指標(SCALE)。由于金融部門結構與金融部門規模存在著內在的聯系,進而將“(金融機構資產總規模—貸款規模)/金融機構資產總規模”作為金融部門結構的衡量指標(STR)。選擇實際GDP作為社會總產出的衡量指標,選擇就業人口總數衡量勞動投入總量(L)。如果忽略資本的折舊,則dK=I,本文中將選取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量來衡量資本的變化。
另外,為了檢驗實證模型的穩健性,本文加入了中國特色元素作為控制變量。由于對外貿易對中國經濟增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依據Levine(1997)的建議,引入進出口總額(XM)與GDP的比值作為控制變量。與此同時,考慮到中國政府在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依據Levine,Loayza和Beck(2000)的建議,將政府支出規模(EXPE)與GDP的比值作為另一控制變量。
本文采用中國1978-2013年的年度數據進行實證分析,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金融年鑒》,為了剔除不同年份價格因素影響,以1978年價格指數為100進行了價格調整。
對中國歷年的宏觀經濟政策基調進行回顧,可以發現中央工作會議所確定的下年政策基調呈現出階段性的變化特征(至少我們可以看到近11年來宏觀經濟政策并不是穩定的),這正是基于當年經濟形勢變化的結果。為了達到熨平經濟波動的目的,中國政府采取“相機抉擇”機制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在“相機抉擇”調控機制約束下,宏觀經濟政策大體上與經濟形勢表現為相反方向的變化。而貨幣政策的調整必然會影響到金融發展,進而影響到金融發展規模指標SCALE與金融發展結構指標STR,最終,“相機抉擇”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為了研究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真正作用”,勢必需要排除“相機抉擇”調控機制的干擾,并且這樣做的另一個好處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內生性問題。因此,本文將借鑒李永友(2006)的處理方法,運用HP濾波法對本文各經濟變量(不含勞動投入L)進行了HP濾波分解。③本文選取的平滑參數為100,通過去除周期波動成分而保留趨勢部分,進而來考察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二)平穩性檢驗
為了消除偏態性影響和虛假回歸問題,我們首先對方程(19)中的部分變量進行對數處理,則本文最終選取的計量模型表示為:

其中,T表示HP濾波分解后的趨勢部分。對出現在模型中的所有變量包括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顯示,ADF檢驗下所有變量在10%顯著性水平下均無單位根,而PP檢驗下除變量STRT*DSTRT之外,其他變量在10%的顯著水平下也均無單位根。但變量STRT*DSTRT在PP檢驗下其P值也十分接近10%。因此,基于兩種不同的單位根檢驗方法,可以認為進入本文的計量模型的所有變量均是平穩的。
(三)格蘭杰因果檢驗
在我們的理論模型中,認定金融發展是經濟增長的原因本質上是一種先驗假定,是基于邏輯上的分析而得到的,因此需要進行科學的驗證。由于本文的模型中的所有變量都是平穩的,因此可以直接對其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其結果如表1所示。

表1 線性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
注:由于我們的目的主要是考察金融發展對經濟的影響,因此只報告了金融發展變量對經濟增長變量單向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
表1報告了1到5期滯后階數的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盡管檢驗結果對滯后階數敏感,但是總體來說,可以認為DLNSCALET、(SCALET/GDPT)*DLNSCALET、DSTRT和STRT* DSTRT是DLNGDPT的格蘭杰原因,這從統計上支持了這些變量進入我們模型的合理性。在本文的理論模型中假定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不存在內生性問題,檢驗結果顯示,DLNGDPT是DLNSCALET和(SCALET/GDPT)*DLNSCALET的格蘭杰原因,但不是DSTRT和STRT*DSTRT的格蘭杰原因,那么可以初步判斷金融發展規模變量與經濟增長變量之間可能存在著內生性問題,而金融結構變量與經濟增長變量之間存在內生性問題的可能性比較小。
(四)回歸結果分析
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內生性問題一直以來受到學者的較多關注,本文使用兩階段最小二乘估計(2SLS)對這一問題進行處理。在沒有更好工具變量的情況下,將內生解釋變量一階滯后項作為工具變量不失為一種合理的選擇。首先我們使用輔助回歸方法對金融發展規模變量和金融發展結構變量與經濟增長進行Hausman檢驗,其檢驗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2 內生性Hausman檢驗結果
注:“*”、“**”、“***”分別表示在10%、5%、1%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報告了p值。
由上表報告的Hausman檢驗結果發現,金融發展規模變量與經濟增長變量之間存在內生性問題,而金融結構變量與經濟增長之間不存在內生性問題。因此模型將選取DLNSCALET的一階滯后項作為工具變量,進行兩階段最小二乘估計。并且引入了AR(1),AR(2)和AR(3)來解決模型的自相關問題,其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回歸結果
注:括號“()”中報告t值,“*”、“**”、“***”分別表示在10%、5%、1%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Hausman檢驗中()中為p值。AR(1),AR(2)和AR(3)的原假設是“擾動項不存在一階、二階自相關和三階自相關”。
進行兩階段最小二乘估計后,重新對金融發展規模變量進行Hausman內生性檢驗,可以發現金融發展規模變量與經濟增長變量之間的內生性問題得到了很好的解決。由上表顯示的D.W.值來看,模型的自相關問題也得到較好的解決。從可決系數來看,我們的模型對數據擬合的較好,各解釋變量(除勞動投入外)均在統計上顯著,并且各解釋變量系數的符號與我們理論分析是一致的,這包含至少兩個方面的含義:金融部門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是遞減的,并且當金融部門規模與社會總產出的比值超過某個界限值時,其規模的繼續擴大反而會抑制經濟增長;與此同時,由于不同金融部門各有優劣,因此存在著一個最優的金融部門結構。具體來看,金融部門規模擴大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為,即當SCALET/GDPT<1.743時,金融部門規模增大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為正;當SCALET/GDPT>1.743時,金融部門規模增大反而抑制經濟增長。金融部門結構變化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為:,即當STRT<0.4724時,金融部門結構變量增大對經濟增長作用為正,當STRT>0.4724時,金融部門結構變量增大對經濟增長作用為負。
至此可以發現,改革開放以來盡管中國金融部門規模的擴大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在前期為正,然而從2008年開始金融規模的擴大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開始為負(因為金融部門規模與社會總產出的比值到2008年底為1.77)。因此試圖通過金融部門規模的繼續擴大以緩解經濟下行(經濟增長率)趨勢并不可取。與此同時,金融部門結構(直接金融部門與金融部門的比值)盡管在樣本區間內總體來說一直呈現出上升的趨勢,但是其值一直小于本文所估計的最優值(該比值在2008年達到最大值為0.4364,小于0.4724),在2008年以后,金融結構變量還呈現出一定的下降趨勢,截止2013年該值已經不足0.40,小于本文所確定的最優值。因此通過提高直接融資的比例,能夠有效緩解現階段經濟下行的壓力。
上述分析通過建立非線性回歸模型可以發現,從2008年開始金融發展規模變量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發生轉折,如果對2008年(不包括2008年)以前的數據做線性回歸,那么從穩健性的角度而言,非線性模型下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平均作用與線性模型下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應該是相同的,并且均是正向作用。兩種處理方法下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如下表所示:

表4 兩種處理模型下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注:模型(1)為表(5)中所代表的非線性回歸模型;模型(2)為線性回歸模型DLNGDPT = C(1)*DLNSCALET + C(2)*DSTRT + C(3)*DLNL + C(4)*LNIT + C(5)* D(XMT/GDPT)+ C(6)* D(EXPET/GDPT),并且模型2使用的數據為2008年以前的數據。
表4及圖1顯示了兩種模型下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通過計算可以發現用非線性模型估計的金融發展規模對經濟增長的平均作用為1.34389,金融發展結構變量對經濟增長的平均作用為0.983124。通過與線性回歸模型結果比較,發現兩者相差極小。從這個角度來說,本文所建立的非線性回歸模型的結果是合理的。
圖1 兩種模型下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作用比較
四、結論與建議
本文通過建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擴展“兩部門模型”,發現金融部門規模擴大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主要取決于金融部門自身的“直接作用”以及對實際部門“溢出作用”與“擠出作用”三者之間的比較。當金融部門規模、金融結構與總產出的比值小于某個臨界值時,即使規模的擴大能夠帶來總產出的增加,但隨著比值的增加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不斷減小最終表現為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非線性關系。
實證研究結果表明,我國金融部門規模的擴大對經濟增長長期以來為正向促進作用,但是其促進作用一直在減弱,甚至2008年之后金融規模的擴大反而對經濟增長產生抑制作用。金融結構變量盡管在整個樣本區間內有了明顯的上升,但是距離本文所確定的最優金融結構還有一定的差距。
因此,本文認為,現階段我國正處于經濟和產業結構轉型特殊時期,金融業承擔重要的“輸血”功能,只有進一步推進金融自由化改革,使金融業所獲取過度的超額利潤回歸至合理區間,鼓勵金融創新,全面提升金融機構競爭能力,才能夠在降低金融業對實體經濟“擠出效應”的同時提高金融業自身效率。同時,僅依靠金融部門粗放式的規模擴張來實現經濟增長已與中國經濟發展趨勢出現背離,未來的政策重心更應關注經濟結構的調整、市場制度的完善以及創新能力的提升。我國還應該加大直接融資渠道的構建,加大力度促進金融創新,提升直接融資比例,優化中國金融結構。這樣才能發揮市場經濟的優勝劣汰機制,實現金融業為實體經濟服務的本質,最終更為有效地促進經濟增長。
1. 李春霞:《金融發展、投資效率與公司業績》[J],《經濟科學》2014年第4期。
2. 李永友:《我國經濟波動與財政政策波動的關聯性分析——兼論我國財政政策的相機抉擇與自動穩定機制》[J],《財貿經濟》2006年第4期。
3. 林毅夫、孫希芳:《銀行業結構與經濟增長》[J],《經濟研究》2008年第9期。
4. 趙振全、于震、楊東亮:《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非線性關聯研究——基于門限模型的實證檢驗》[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7年第7期。
5. 張鶴、黃琨、姚遠:《金融發展、銀行資本結構與經濟增長內在關聯性的實證研究》[J],《經濟學動態》2012年第5期。
6. 周寧東、汪增群:《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一項基于面板數據的研究》[J],《財貿經濟》2007第5期。
7. 周麗麗、楊剛強、江洪:《中國金融發展速度與經濟增長可持續性基于區域差異的視角[J],《中國軟科學》2014年第2期。
8. Acemoglu D, Zilibotti F. “Was Prometheus Unbound by Chance? Risk, Diversification and Growth” [J],, 1997, 105(4): 709-751.
9. Balkaransingh, Radha.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Testing for Causality and Finance's Contribution to FTP" [J],60 (2003): 281-305.
10. Demetriades, Panicos O. and Khaled A. Hussein. "Does Financial Development Cause Economic Growth? Time-series Evidence from 16 Countries" [J],51.2 (1996): 387-411.
11. Feder G. “On Exports and Economic Growth” [J],, 1983, 12(1): 59-73
12. Fung M K.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J],2009, 28(1): 56-67.
13. Goldsmith, Raymond.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M],(1969).
14. La Porta, Rafael, et al. "Legal Determinants of External Finance" [J],(1997): 1131-1150.
15. Levine R, Loayza N, Beck T.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Growth: Causality and Causes”[J],2000, 46(1): 31-77.
16. Levine R, Zervos S. “Stock Markets, Banks and Economic Growth”[J],, 1998: 537-558.
17. McKinnon R I. “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M],, 1973.
18. Odedokun, Matthew O. "Alternative Econometric Approaches for Analyzing the Role of the Financial Sector in Economic Growth: Time-series Evidence from LDCs" [J],50.1 (1996): 119-146.
19. Patrick H T.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J],, 1966: 174-189.
20. Schumpeter J A. Das Gesamtbild der Volkswirtschaft [J],, 1912: 463-546.
21. Shaw S. “Financial Deepen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rowth”[J]., 1974, 57: 58-59.
(H)
①“直接效應”是指金融部門勞動和資本投入增加所帶來的金融部門產出的增加;“溢出效應”是指金融部門規模的擴大有利于實體經濟的配置效率的提高,從而帶來實際部門產出的增加;而“擠出效應”則是指金融部門規模的擴大所必須的勞動和資本投入的增加會使實際部門勞動和資本投入減少,從而造成的實際部門產出減少。
②如果假定(4)的內容改為金融結構先變化,金融規模后變化,那么在分析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先假定金融規模不變。
③因為一國總會試圖促進充分就業,即使頒布了勞動方面的宏觀政策也是為了促進其就業人口的增加,而不會像貨幣政策那樣抑制金融發展規模變量,因此本文并沒有對勞動投入變量L進行HP濾波分解。
行業壟斷收入分配效應的成因、測度與治理體系研究,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13CJY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