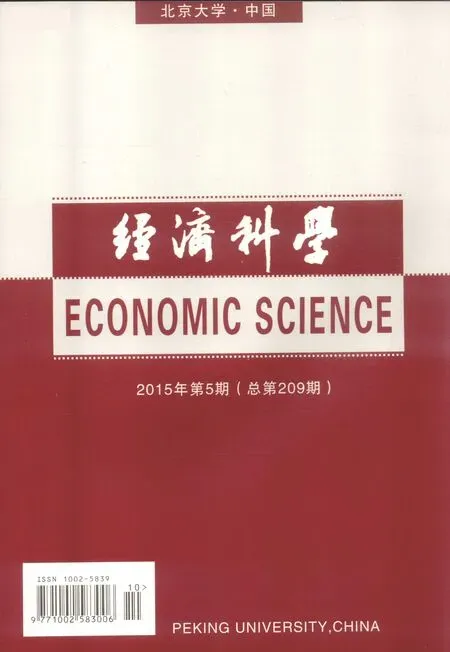工資剛性與國企效率損失*
張子楠 王高望 趙曉軍
?
工資剛性與國企效率損失*
張子楠1王高望2趙曉軍3
(1.中央財經大學中國經濟與管理研究院 北京 100081)(2. 山東大學經濟研究院 山東濟南 250100)(3.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 北京 100871)
通過在一個帶有異質性廠商的增長模型里引入政府關于國有企業的工資總額管理模式,本文揭示了國企職工工資決定的剛性特征,并分析了這種工資剛性對國企要素錯配和效率損失的影響。本文里,國企效率損失表現為兩個層面:微觀經濟層面上企業自身虧損程度的加深,以及宏觀層面上國有企業作為整體在經濟中要素和產出比重的下降。校準結果發現,工資決定方程的剛性特征大約解釋了1993-2007年國有企業在工業部門中24.84%的資本比重和36.40%的產出比重的下降。如果政府放松對國企工資的限制,將工資決定方程的剛性系數,從基準模型的0.347放松到0.1,則該段時期國企資本和產出的比重將平均分別增加13.84%和20.33%。本文的研究為國企效率損失問題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
工資剛性 要素錯配 效率損失
一、引 言
如何提高國有企業績效一直是中國國企改革的核心問題之一,對國企工資制度與企業績效關系的研究也是學術界研究的一個熱點。但現有的研究較多集中于高官薪酬方面(辛清泉和譚偉強,2009),有關職工工資的研究卻比較少(陳冬華等,2010)。然而,職工工資直接影響職工的積極性,是決定企業績效是否可持續增長的關鍵因素之一。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后,國企效率問題進一步升溫,重新對現有國有企業職工工資決定機制進行研究,探討它對工人的激勵效果,是否存在降低企業效率的因素,以及如何建立和完善與國有企業實際相適應的職工工資決定機制,仍是亟需研究和探討的重要問題。
改革開放之前,國有企業工資處于政府嚴格的計劃管制狀態,職工工資由上級勞動部門按統一的標準核定,職工得到的物質激勵很弱(趙耀輝、李實,2002)。從80年代開始,為調動職工的生產積極性,政府先后出臺了利潤留成,工效掛鉤(“兩低于”),工資總額包干以及工資總額預算管理等政策。這些政策的共同特征在于,它改變了政府直接規定工資的模式,轉向通過制定企業工資總額與企業效率掛鉤的規則這種間接方式,來管理職工工資的發放,是一種“工資總額管理政策”。
由于無需對舊有工資體系和職能部門進行大幅度修改,就可以建立起企業績效與職工物質獎勵之間的直接聯系,工資總額管理政策在國有企業中迅速地得到推行(Meng, 2000),至1996年已經有72.26%的國有工業企業實施了不同形式的工資總額管理政策,其中中央企業比例更是超過了90%(《中國財政年鑒》,1997),工資總額管理政策已成為國有企業最普遍的分配模式。眾多實證文獻也發現工資總額管理政策對了國有企業效率的增進作用。例如,Meng(2000)發現80年代實行的獎金政策顯著地提高了國有企業的效率;陳冬華等(2010)以556家國有非上市公司為樣本,發現對于實施工資增長與企業績效掛鉤的企業,企業業績均出現了顯著的提高。
但容易被忽視的是,國企工資總額決定機制仍保留著行政手段的色彩,職工工資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勞動部門的管制,形成了國企職工工資的“半市場化狀態”(陸正飛等,2013)。與私有企業工資增長等于邊際勞動產出增長不同,工資總額管理模式下國有企業職工工資增幅與邊際勞動產出增幅不完全同步,造成國有企業職工工資在一定程度上的剛性特征。陳冬華等(2010)的實證研究發現國有企業工資的剛性特征削弱了工資對職工的激勵作用,并降低了企業效率。陸銘(2003)也認為存在工資管制情況下進行企業激勵改革,反而可能會阻礙企業效率的提高。陸銘等(2001)則發現工資總額管理政策會提高勞動力的實際價格,誘使國有企業選擇資本替代勞動力,即國有企業資本深化水平的上升可能部分是企業面對的勞動力實際價格被扭曲的結果。數據顯示,1989年國有工業企業資本產出比是私有企業的1.16倍,1997年增加到1.48倍,2007年則進一步上升到1.94倍,比值上升了67.24%。
如果工資總額管理政策導致了國有企業要素的錯誤配置,那么要素錯配對國有企業效率損失的影響程度,以及對國有企業在整體經濟中比重的影響是怎樣?已有文獻從利率管制、政策性負擔、多重目標等方面發現在國企內部存在大量的要素錯配現象,而國企效率也是各類所有制企業中最低的(吳延兵,2012;劉瑞明, 2013;陳彥斌等,2014)。同時,對于低效率的國有企業,雖然可以依賴政府的補貼而存活(林毅夫和林志贅,2004),但面對國企虧損產生的財政包袱,政府可能會選擇將低效率的國有企業民營化,導致國企在整體經濟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王紅領等;2001;夏慶杰等,2012)。數據表明,1989-2007年國有企業在工業部門中勞動、資本和產出比重都出現了急劇地下降,分別從98.24%、97.25%和96.84%降到了41.51%、65.99%和50.01%。王紅領等(2001)利用1980-1999年企業調查數據發現,減輕補貼虧損國企而帶來的財政負擔是90年代政府實施“抓大放小”改革的重要原因之一。夏慶杰等(2012)認為來自工資總額管理政策的約束,可能是2002年以后國企就業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本文基于國有企業資本密度水平相對私有企業逐漸增大,勞動雇傭不足的特征事實,分析國有企業工資決定方程的剛性特征,進而研究這種剛性特征對企業要素配置和生產效率的影響。本文的貢獻主要有四點:第一,從理論上推演了國有企業的工資決定方程,并揭示了工資方程的剛性特征;第二,分析了工資方程剛性對國有企業效率損失的影響機制;第三,在傳統文獻上引入了資本變量,從理論上論證了國有企業內部資本替代勞動和要素錯配現象的成因,為國有企業效率損失問題的提供了新的解釋機制;第四,使用宏觀數據擬合了國有企業發展的幾個特征事實,如資本密度水平相對于私有企業逐漸加大,在整體經濟中要素和產出比重下降等。
本文其余部分的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構建了工資方程與企業效率關系的理論模型;第三部分刻畫了模型的均衡條件和動態特征;第四部分進行模擬和實證分析;第五部分是本文的主要結論和建議。
二、模型結構
本部分我們將刻畫國有企業工資決定方程,并構建工資決定方程對國有企業效率影響的理論模型。和Song et. al(2011)類似,我們考慮這樣一個小國開放經濟體,經濟體由居民、國有企業、私有企業和政府四類個體組成。居民提供勞動,獲取工資收入。居民可以在不同企業間自由流動。經濟體總人口增長率外生給定,等于。經濟體只有一種商品,既可以用于消費,也可以用于投資和購買國外債券,該商品由國有部門和私有部門生產。國有和私有企業生產技術相同,企業生產差異僅在于工資決定機制的不同:國有企業工資發放受工資總額管理政策的約束,而私有企業則可以根據利潤最大化原則自主決定工資。政府對國有企業和居民進行征稅,并將全部稅收所得補貼給國有企業。
(一)居民行為
居民目標問題為滿足預算約束下最大化貼現效用函數:

(2)
代表居民努力帶來的負效用①。其中為工人實際得到的工資,為參照工資,ρ>0為努力系數。由方程(2)可知工人努力帶來的負效用取決于實際工資和參照工資的比值。對于參照工資,本文中設定為工人的邊際勞動產出(MPL),這是由于MPL衡量了工人對企業的貢獻,當工人得到的工資越接近他的貢獻時,工人越被公平對待。從而有:

又第t期居民的預算約束為:
(4)

(6)
方程(5)為消費的歐拉方程。方程(6)則反映了消費者努力水平與工資公平程度的關系。
(二)私有企業
經濟體中代表性私有企業③的生產函數為:。其中p表示私有企業,a是資本份額。為技術水平,增長滿足,A0表示初始期技術水平,是技術進步率,為外生給定變量。,和分別為企業的產出、資本和勞動需求,為私有企業工人的努力水平。對于私有企業,工人工資等于邊際勞動產出,由方程(6)可知私有工人努力水平為。私有企業問題為面對要素價格最大化企業利潤,即:

(8)

由于國內利率等于世界市場利率,根據方程可知私有企業有效資本密度保持不變,根據方程(9)可知工資增速等于技術進步率g。
(三)國有企業
在國有企業先后實施的不同工資總額管理政策中,以工效掛鉤制實施時間最長,覆蓋面最廣。同時其它工資總額管理政策對企業效率的影響機制和工效掛鉤制相似,因此本文以工效掛鉤制為例,分析工資總額管理政策對企業效率的影響④。工效掛鉤是指企業工資總額增加比例同企業績效增加比例相“掛鉤”,其核心內容是規定了國有企業“被政府允許發放”的總工資水平——“管理工資總額”。管理工資總額主要包括管理工資總額基數,經濟效益增速和掛鉤浮動比例三部分。其中,工資總額基數總額一般為上一年管理工資總額,并根據計劃指標進行人數增減;經濟效益指標通常選取實現稅利、上繳稅利或勞動生產率等指標;浮動比例則由政府勞動人事部指定,一般在0.3-0.75之間。本文中我們采用上一期管理工資總額作為工資總額基數,(1-ε)為浮動比例⑤,以及勞動生產率(APL)作為經濟效益指標,可將管理工資總額方程表示如下⑥:

(11)
向前遞歸至0期,并化簡可得:

(13)
出于簡化分析和匹配現實的考慮,假定在初始期國有企業的管理工資等于實際發放工資:,且國有企業的有效資本密度不小于私有企業:,并令,從而有等式成立。代入方程(13),可知人均管理工資方程滿足:

方程(14)表明工資管理方程等于0期工資和t期的邊際勞動產出的線性加權:當時,管理工資固定不變,始終等于0期工資,此時工資管理方程類似于工資改革前實行的固定工資制;當時,管理工資等于工人的邊際勞動產出,⑧此時工資增長與企業效率增長完全按同步,工資管理方程規定的工資決定機制與私有企業類似。
在實行工資改革的過程中,政府是通過稅收等經濟手段進行調控:如果企業實際發放工資低于管理工資,則工資可在當年企業所得稅前扣除;反之,則實際工資超過管理工資的部分,不可以稅前扣除。⑨這種做法等價于以企業所得稅的稅率對超標工資征收工資調節稅(陳東華等,2010)。從而國有企業工資調節稅滿足:

(16)
將工資管理方程(14)改寫為關于有效資本密度的表達形式有:

由工資管理方程可知企業的有效資本密度的值決定了管理工資的取值。國有企業目標問題為在滿足工資管理方程(17),工資調節稅方程(15)和努力方程(16)下最大化企業的價值,即:
(18)

(20)
在市場經濟下,虧損的企業本應退出生產領域。但對于虧損的中國國有企業,卻可以依賴政府的補貼而維持生存,補貼的形式包括稅收減免、財政補貼等直接補貼,以及金融補貼、壟斷利潤等間接補貼(劉瑞明,2013)?。
(四)政府部門
我們假定政府的行為如下:在每一期政府對國有企業征收工資調節稅,并對居民以固定稅率τ征收稅收。政府將全部稅收補貼給國有企業,從而保持每期預算平衡。令分別表示t期經濟體的總產出、資本存量和勞動人口。利用企業生產的規模報酬不變的特征,可將對居民的征稅表達如下:

(22)
三、競爭性均衡及比較靜態分析
(一)競爭性均衡定義
經濟均衡時,居民和企業根據給定價格水平進行消費和生產決策,同時產品和要素市場實現出清。對于居民,其收入用以消費和儲蓄。如果居民總儲蓄超過下一期國內生產所需資本,則多余部分轉變為持有國外債券,反之則表現國外居民持有國內債券。對于國有企業,和林毅夫,林志贅(2004)類似,均衡時政府補貼等于國企虧損總額,結合方程(20)有:

4. 政府部門從居民和國有企業收取稅收,并將稅收所得全部補貼國有企業,滿足方程(21)(22)和(23)。
5. 政府補貼等于國有企業虧損總額,滿足方程(24)。

(二)均衡動態的性質
下述一系列命題刻畫了模型經濟的主要內生變量在均衡路徑上的動態特征。
命題一的結論來自于方程(19)和利率外生給定的假定。在命題一中,是國有企業第0期工資,衡量了第t期國企工人的邊際勞動產出。由命題一可知,均衡時國有企業工人工資等于政府規定的管理工資。當0<ε<1時,企業MPL增長高于工資增長,企業工資方程表現出剛性特征。且ε大小衡量了工資剛性的程度:ε越大,則國企勞動生產率增速越大于工人工資的增速,工資決定方程的剛性程度越大。因此在本文中,我們將ε定義為國有企業工資決定方程的剛性系數?。進而,我們分析國企工資決定方程的剛性特征對企業要素配置的影響,有下述命題二:
命題二:工資決定方程的剛性特征造成了企業要素資源的錯配,且錯配的程度隨剛性系數ε增大而增大,隨技術水平At增大而增大。
證明:均衡時,國有企業最優有效資本密度為:

進一步,我們分析這種剛性對企業效率的影響。國有企業效率損失的大小與工資方程剛性的大小(e大小)是怎樣?隨著時間推移,效率損失是否會變得越來越嚴重?由于企業的資本回報率(企業價值/資本)衡量了企業的盈利能力,我們選擇資本回報率作為企業效率的衡量指標,有下述命題三:
命題三:工資決定方程的剛性特征降低了國有企業效率,且國有企業效率隨剛性系數e的增大而減少,隨技術水平At增大而減少。
證明:由附錄一可知最優決策時國有企業資本回報率滿足:

最后,分析國有企業效率損失在宏觀經濟層面上的表現,即國有企業作為一個整體,它在整體經濟中的比重和工資剛性系數e的變動關系是怎樣?我們有如下命題成立:
命題四:國有企業在整體經濟中的勞動和資本比重隨剛性系數e增大而減少,隨技術水平增大而減小。
證明:利用企業生產規模報酬不變的特征,可將國有企業t期總虧損表示為關于國有企業總資本存量的線性函數如下:

又均衡時政府補貼等于國有企業虧損總額,由方程(21)-(27)可解得國有企業資本規模為:
(28)
以及國有企業勞動人口滿足:

進而,第t期私有企業勞動人口和資本規模分別為:
(30)

從而可計算得國有企業在整體經濟中資本和勞動份額分別滿足:
(32)

類似命題二中證明可知:
;;;
即隨著管理工資與企業績效掛鉤比例e的增加,國有企業的勞動和比重也隨之增加。而且隨著時間t增加,技術水平外生增加會加大國企要素錯配的程度,從而導致企業效率下降和在整體經濟中的份額下降。
(三)穩態均衡與比較靜態分析
模型經濟的動態變化的主要驅動因素來自于技術進步率At的變化。由方程(25)可知,國有企業有效資本密度關于技術水平At的一階導數大于0,二階導數小于0,從而隨時間增加但增速不斷降低,并趨近于穩定值。當不變時,國有企業投資回報率(方程(26))和在整體經濟中的比重(方程(32)和(33))也不發生變化,經濟體進入穩態均衡。當系統處于穩態均衡時,我們有命題如下成立:
命題五:穩態均衡時,國有企業有效資本密度隨剛性系數ε增大而增大,在整體經濟中勞動和資本比重隨剛性系數ε增大而減少。
證明:由方程(25)可知,穩態時國有企業有效資本密度為:

同時,穩態時國有企業在整體經濟中的勞動和資本比重分別為:
(35)

對方程求關于ε求一階導數,可證:
;;
因此,國有企業的有效資本密度即隨著國企工資方程的剛性系數ε增大而增大,而在整體經濟中的勞動和資本中比重隨剛性系數ε增大而減少。
四、數值分析
(一)參數校準
本部分數據來源于1993-2008年《中國財政年鑒》、《中國經濟統計年鑒》和《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主要涉及有工業產值,資本規模和從業人員三類數據,在數據處理上借鑒了陳勇和唐朱昌(2006)的方法。本文選取1993年作為模擬起始期,是由于1992年以后實施工資總額管理政策的國企已占據了主要比重。同時,為了避免2008年金融危機對整體經濟的結構性影響,本文選取了2007年作為結束期。參數校準結果如表1所示。
居民有關參數的設定。消費者主觀貼現因子β值設定為0.997。人口增長率數據來自歷年《中國經濟統計年鑒》,計算可知工業人口平均增長率為。居民努力系數ρ校準方法借鑒了Danthine and Kurmann(2004)的思路,校準使得國有企業相對私有企業資本產出比值增速匹配現實增長率。由《中國統計年鑒》數據計算得增速等于1.49%,從而校準可得ρ為0.79。
廠商部門有關參數的設定。資本份額α設定為0.6,資本折舊率設定為0.10。勞動增進型技術增長率來自于Song et al(2011),為3.8%。銀行利率選取央行公布的一年期官方基準存款利率作為名義利率,計算得校準期實際利率均值為4.15%。
政府部門有關參數的設定。對于剛性系數ε,由國有企業實際人均工資增長率與實際人均勞動產出增長率的比值計算而得。根據歷年《中國財政年鑒》數據,增長比值為0.653,從而校準可得剛性系數為0.347;對于工資調節稅稅率γ,由于工資調節稅合并到企業所得稅中,從而設定為0.33;對于居民征稅的稅率τ,由于無法直接估算出包括財政補貼、金融補貼、壟斷租金等在內的補貼總額,本文采用匹配起始期國企資本占全部企業資本的比重的方法來校準,可得0.63?。
初始狀態有關參數的設定。初始人口設定為100。初始技術水平標準化為1。對于初始相對資本勞動比,由《中國經濟年鑒》數據計算可得1992年國有企業相對資本產出比平均為1.53,從而換算出w值為2.89。

表1 模型參數校準結果
(二)校準結果分析
本文的校準結果如圖1所示。對于勞動比重,根據年鑒整理的數據,1993-2007年我國工業部門國有企業勞動比重下降超過了50%,而本文的校準模型顯示了44.8%的下降;對于資本和產出比重,數據顯示分別下降了24.86%和36.53%,而校準模型分別顯示了24.84%和36.40%的下降,兩者相差無幾。因而,本文低估了整體經濟中勞動比重的變化,而較好地擬合了資本和產出比重的變動。對于勞動比重變化的低估,一個可能原因是2000年“抓大放小”改革基本結束前,國有企業存在大量的勞動冗余(曾慶生和陳信元,2006),這部分勞動力實質上是不參與企業的生產的,而本文沒有刻畫這個現象。
(三)敏感性分析
為了更清楚地考察工資管理政策對企業效率的影響,本文進一步研究當國有企業工資決定方程的剛性系數ε不同取值時模型主要變量的變化特征。我們分別設定ε為0.7, 0.5, 0.347, 0.25和0.1,模擬結果如圖2所示。圖(2.a)和(2.b)表明了隨剛性系數從0.7下降到0.1,國有企業2007年相對資本產出比從3.50下降到1.62,而相對資本回報率則從0.41上升到0.75。資本密度的下降反映了企業要素錯配程度的減少,投資回報率的上升則反映了企業經濟效益的提高;圖(2.c)和(2.d)則表明了工資方程的剛性系數ε與國有企業在整體經濟中份額的關系。隨著隨剛性系數從0.7下降到0.1,國有企業2007年資本比重從43.27%上升到85.29%,而產出比重也從17.90%上升到78.20%。此外我們還發現,如果把國有企業工資決定方程的剛性系數ε,從基準模型的0.347放寬到0.10,則國企相對資本回報率將平均上升近6%,而國有企業在整體經濟中的資本和產出比重將平均分別上升13.84%和20.33%。
圖1 國有企業資本、勞動和產出份額:數據與模型(1993-2007)
(a)國有企業相對資本產出比????????(b)國有企業相對投資回報率
(c)國有企業資本比重????????(d)國有企業產出比重
注:圖形顯示了不同剛性系數取值下的主要關鍵變量的變動關系。B1,B2,B0,B4和B5分別代表剛性系數ε為0.7,0.5,0.347,0.25和0.1取值下的實驗。
五、結論與建議
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核心目標之一是通過建立激勵相容的薪酬體系來實現職工努力與工資報酬之間的關聯,以提高國有企業的生產經營效率。從80年代開始,政府逐漸放寬了對國有企業分配體系的管制,先后實行了多種以工資總額管理為特征的職工工資政策,有效地改善了計劃經濟時期職工激勵缺失的現象。但容易被忽視的是,國有企業職工工資仍受到勞動部門的管制,這使得職工工資具有一定程度的剛性特征。
通過刻畫國有企業工資決定方程的剛性特征,本文分析了國有企業工資決定方程對國有企業要素錯配和效率損失的影響。我們發現,工資決定方程的剛性提高了國有企業面對的實際勞動力價格,導致國有企業內部資本替代勞動和要素錯配現象的產生。本文還發現,要素錯配一方面降低了國有企業自身的資本回報率,另一方面使得國有企業作為整體在經濟中要素和產出比重出現了下降。通過使用1993-2007年的數據進行校準和模擬分析,我們發現工資決定方程的剛性特征大約解釋了國有企業在工業部門中24.84%的資本比重和36.40%的產出比重的下降。如果政府放松對國企職工工資發放的約束,將國有企業工資決定方程的剛性系數,從基準模型的0.347放寬到0.1,則1993-2007年國有企業在經濟中的資本和產出比重將分別平均上升13.84%和20.33%。
本文在理論和現實兩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創新性。首先,本文從理論上考察了國有企業工資總額管理政策對企業效率的影響機制,揭示了國企工資決定方程的剛性特征,為有關經驗研究提供了支持;其次,既有文獻在研究國有企業要素錯配問題時,大多強調資本因素的扭曲作用,而本文則發現勞動力因素同樣起著重要作用,從而為國有企業要素錯配和效率損失問題的提供了新的解釋機制;最后,隨著“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國有企業全面推行,國有企業產權結構多元化特征更加明顯,不同股權結構的相互制約機制將使得國有企業職工工資對企業效率的影響機制更加復雜。我們的研究表明,我國長期實施的自上而下的,通過控制工資總額來控制企業工資的方式并不是最優的。
本文認為,政府在實施國企職工激勵政策的同時,應當放松對職工工資的管制。工資政策本質上是企業要素資源配置優化的結果,應由職工的勞動價值和市場供求關系決定。如果國有與私有企業同處于充分競爭的市場,則利潤最大化原則會促使國有企業自動選擇最有效率的工資決定機制。相反,通過工資總額及其增長的管制模式會扭曲職工的激勵機制,造成企業的效率損失和衰退。因而,在減少國有企業的政策性負擔(優惠)和給予企業公平競爭環境的同時,政府應當放松對國企職工工資的管制,依靠市場競爭的力量來促進國企工資決策的優化。
本文的研究也存在著一定的不足。2003年以后中國工業部門的市場結構發生了一定程度的改變,特別是國有企業逐漸集中到壟斷性資源行業。這種市場結構的演化可能會改變工資總額管理模式的影響效果。因此,在國企工資決定機制與效率損失相關性的研究中引入壟斷因素,進而更精確地測量工資政策對國有企業效率損失的影響,將是我們進一步研究的方向。
數學附錄:
附錄一:分析國企工人努力方程、管理工資方程,工資調節稅方程可知,國有企業有效資本密度是影響工人努力水平和工資調節稅大小的關鍵因素。令表示使得第t期國有企業工資努力水平的有效資本密度值;令表示使得的有效資本密度值。我們可以分類討論:1);2),;3):。
分別將1)和2)的條件代入國有企業目標方程,利用庫恩-塔克條件和反證法可證明企業不會選擇在1)和2)區間進行生產。對于3),由可知。將條件代入到國有企業目標方程,兩邊同除以,轉化為關于最大化資本回報率(ROA)的表達形式,并同樣利用庫恩-塔克條件,計算可知當時,不是企業最優決策解的條件。從而可得。(限于篇幅,具體證明省略,可向作者來信索取。)
1. 陳冬華、范從來、沈永建等:《職工激勵、工資剛性與企業績效——基于國有非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經濟研究》2010年第7期。
2. 陳彥斌、陳小亮、陳偉澤.:《利率管制與總需求結構失衡》[J],《經濟研究》2014年第2期。
3. 韓朝華、周曉艷:《國有企業利潤的主要來源及其社會福利含義》[J],《中國工業經濟,》2009年第6期。
4. 靳來群、林金忠、丁詩詩:《行政壟斷對所有制差異所致資源錯配的影響》[J],《中國工業經濟》2015年4期。
5. 林毅夫、李志赟:《政策性負擔、道德風險與預算軟約束》[J],《經濟研究》2004年第2期。
6. 劉瑞明:《中國的國有企業效率:一個文獻綜述》[J],《世界經濟》2013年第11期。
7. 陸銘、范劍勇:《論國有企業的工資管制對就業的影響》[J],《上海經濟研究》2001年第3期。
8. 陸正飛、王雄元、張鵬:《國有企業支付了更高的職工工資嗎?》[J],《經濟研究》2012年第3期。
9. 王紅領、李稻葵、雷鼎鳴:《政府為什么會放棄國有企業的產權》[J],《經濟研究》2001年第8期。
10. 吳延兵:《國有企業雙重效率損失研究》[J],《經濟研究》2012年第3期。
11. 夏慶杰、李實、宋麗娜:《國有單位工資結構及其就業規模變化的收入分配效應:1988—2007》[J],《經濟研究》2012年第6期。
12. 辛清泉、譚偉強:《市場化改革,企業業績與國有企業經理薪酬》[J],《經濟研究》2009年第11期。
13. 楊瑞龍、周業安:《國有企業雙層分配合約下的效率工資假說及其檢驗》[J],《管理世界》1998年第1期。
14. 張杰:《漸進改革中的金融支持》[J],《經濟研究》1998年第10期。
15. 張勇、古明明:《重新評估我國的增長潛力——基于全要素生產率和數據分析視角的解釋》[J],《經濟科學》2013年第2期。
16. 趙耀輝、李實:《中國城鎮職工實物收入下降的原因分析》[J],《經濟學(季刊)》2002年第2期。
17. 曾慶生、陳信元:《國家控股、超額雇員與勞動力成本》[J],《經濟研究》2006年第5期。
18. Akerlof, George A. and Yellen, Janet L. "The Fair Wage-Effort Hypothesis and Unemployment." [J], 1990, pp. 255-83.
19. Collard, Fabrice and de la Croix, David. "Gift Exchange and the Business Cycle: The Fair Wage Strikes Back." [J], 2000, 3(1), pp. 166-93.
20. Danthine, Jean-Pierre and Kurmann, Andre. "Fair Wages in a New Keynesian Model of the Business Cycle." [J], 2004, 7(1), pp. 107-42.
21. Meng, X., Ownership structure, Labour Compensation and Labour demand [M]; Labour Market Reform in China. 20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2. Song, Z., K. Storesletten and F. Zilibotti, Growing Like China[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1. 101(1): p. 196--233.
(L)
①負效用函數來自于公平工資理論(Akerlof和Yellen, 1990),理論得到了眾多經驗文獻的支持。楊瑞龍和周業安(1998)也發現在中國國有企業存在公平工資機制的影響。
②小國開放經濟假定下本國利率等于世界市場利率r,投資實物資本和購買國外債券的回報率也均為r。
③本文中私有企業包括私營、外資和港澳臺投資企業,國有企業指國有、國有控股和集體企業。
④ 2009年以后,為了改變壟斷行業國企職工高收入的現象,國資委增加了對國企工資發放的審批環節,實行“工資總額預算管理”。工資總額預算管理政策并沒有改變企業工資總額增長與績效增長關聯的模式,國企工資決定方程的剛性特征仍舊存在,本文中所分析的作用機制也依然有效。
⑤本文用(1-ε)而不是ε來表示,是由于如下文所示ε衡量了國有企業工資決定方程的剛性程度。
⑥具體內容可參考《關于進一步做好企業工資總額同經濟效益掛鉤工作的通知》。本文選取勞動生產率作為經濟效益指標,是考慮到工效掛鉤制又逐漸演化出“兩低于”原則。同時,使用勞動生產率表達的管理工資方程也更具經濟學含義。
⑦此處利用了當趨近于0時,的近似。
⑧此時由于假定經濟體沒有其它扭曲因素,國有企業與私有企業在0期的資本密度相等,即。
⑨稅前扣除口徑的規定可參見《關于工效掛鉤企業工資稅前扣除口徑問題的通知》。對于工資調節稅,1994年以前存在專門的“國營企業工資調節稅”這一稅種,稅制改革以后統一合并到企業所得稅中。
⑩參見本文校準部分的內容,可知假設條件在參數一定范圍內均成立。
?根據張杰(1998)的估算,財政補貼平均1985-1994年GDP的5.63%,而金融補貼則平均占9.7%。韓超華和周曉燕(2009)發現壟斷是1997-2007年國有工業企業利潤的主要來源。如果扣除壟斷利潤,國企仍將出現虧損。
?值得強調的是,本文中的工資剛性是指由于政府對國企職工工資發放行為的限制而導致的國有企業工資增長與工人邊際勞動產出增長的偏離,不同于傳統凱恩斯理論中,由于企業不能靈活應對市場供求關系而導致的工資剛性。
?由τ值可以計算得政府對國企補貼占GDP比重為25.2%,這個值高于張杰(1998)文中大約15%的結論。一個可能原因在于本文沒有考慮金融深化等因素,低估了國企的資本回報率,從而校準得到的參數值是基于模型內的校準值,與實際數值不完全一致。
* 本文的研究得到社科重大基金項目(項目編號:15ZDA007)、山東大學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編號:2015TB006),特此致謝。感謝匿名審稿人提出的寶貴意見,但文責自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