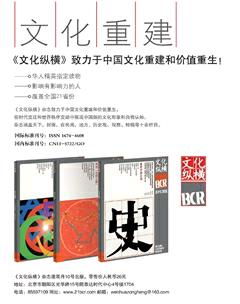泰國的政治戲劇
程東金
2015年8月17日的曼谷爆炸案將人們的視線又一次拉回到這個國家不平靜的政治上。他信派與反他信派最新一輪的較量以軍隊的再次出場而終結,自2014年5月的政變以來,軍隊逐漸鞏固了自己的政治控制,而且絲毫沒有表現出在第一時間還政于民的意向。與2006年的泰國政變相比,軍隊對管理一個復雜的現代經濟體似乎有了更多的信心。他們攬權不放,也意味要投下更大的賭注:除了應付迫在眉睫的王位繼承危機,還要制定一部新憲法,一勞永逸地終結他信派的選舉優勢。迄今為止,他信派并未發起大規模的動員,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們的忍耐克制只是蓄勢待發。這場經典的階級沖突不會因為上層建筑的憲法修改而終止。
兩大政治集團數輪搏斗的歷史已為人們所熟知。在過去的十幾年里,反他信派嘗試了各種手段來遏制他信體制——修改憲法,改變國家體制,縮小選舉機制在立法和行政機構中的作用,削弱總理權力,強化一系列非選舉機構的權力;司法政治化,以法院判決取消他信派政黨,在五年內禁止數百名他信陣營政治家參與政治;發動軍事政變。自2006年以來,已經有四屆他信派政府為非選舉方式的軍事政變和司法政變所推翻。
反對派明白,在現有的選舉體制下,占人口少數的他們無法掌握國家政權,因此該集團喪失了對選舉民主的信心。他們的解決辦法是,更高地舉起民主的旗幟,但加以重新定義,強調道德和權威的重要性,主張“好人治理”。對于王室、軍隊等傳統精英勢力而言,這一立場是順理成章的,但對于主要分布在曼谷及其周邊城市的中產階級來說,這就顯得有些奇怪了。在標準的政治學教程中,習慣于政治依附狀態的中產階級經常站在王室、官僚等傳統精英勢力的對立面,而在泰國,他們卻集結在代表傳統精英的王室、軍隊一邊,反對前大資本家他信領導的新體制。
根據泰國學者Pasuk Pongpaichit的分析,他信體制代表著商業資本在泰國的勝利。在通常情況下,大資本并不需要直接出面掌握政權,只要國家有能力為資本積累創造有利的社會和政治環境,或者至少不去侵害大資本,雙方就能相安無事。但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卻改變了這一狀況,危機重創了泰國經濟和社會,以他信為代表的大資產階級意識到,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新條件下,過時的泰國國家結構必須重組,以保障商業資本的利益。利用普遍的社會危機,他信發起了一場政治革命。為取得選舉勝利,他信選擇與東北部農民結成同盟。在這個國家的政治史上,這些農民長期處于弱勢地位。長期以來,泰國農民盡管人數眾多,但在政治上始終處于弱勢。在每次選舉時,他們也投票,但卻是在當地政客和頭面人物所編織的庇護體系下投票。那些民選議員根本不代表他們的利益,他們也從來不對政治抱有任何期望。
他信改變了這一狀況,他成為泰國歷史上第一個認真關注農村和農業問題的政治家,并從中收獲巨大的政治動能,顛覆了傳統精英主導的政治格局。一方面,他巧妙地利用泰國的“舊式政治”,利用選舉政治中的各種庇護—代理人網絡,收編、整合眾多小型政治派系;另一方面,他瞄準為數眾多的農村人口,廣泛建立能夠扎根基層的政黨和社區組織,通過選舉動員,一舉將這些政治消極的農村人口變成能動的“政治人口”。在農民這一邊,占據人口多數但在政治上沉默多年的他們發現,一個強勢的政黨與他們在政治利益上是互補的。他信的政黨需要農村選民的支持,從而保持政治優勢地位,直至實現“一黨執政”的目標;而農民則可以通過泰愛泰黨遍布全國的基層黨支部反映自己的訴求,分享中央財政的“草根政策”撥款——雖然有限,但畢竟是良好的開端。這意味著一種新型國家-農民關系的出現。此時,國家對待農民,不再是剝奪和榨取——通過地租、農業稅費、貿易剪刀差等各種手段,強制向城市和工業轉移農業剩余,而是轉向了反哺和支持。相應的,農民也開始以更加積極的態度看待政治,并期望能在更大程度上左右這一有利于鄉村的政治轉向。
美國學者Andrew Walker在其著作Thailands Political Peasants中,描述了他信體制與泰國東北部農村中占主導地位的“中等收入農民”之間的選舉聯盟。在這片已經開始被資本主義所侵蝕,但又未被徹底改造的鄉村經濟和社會結構上,他信建立起自己了的政治基礎。他敏銳地意識到占泰國總人口70%的農民對于發展的渴望。這些收入日益多元化的中農雖然不再貧窮,但仍然沒有擺脫半自足的經濟狀態。他信所做的,就是通過系統的國家支持與扶助,推動農村發展,換言之,他將農村整合進了資本主義體系。在這一點上,不同于拉美常見的民粹主義福利,他信針對農村的扶植項目是要解決農村小型信貸和資本的稀缺問題,培育中農的小企業家精神。用他自己的話說,“資本主義需要資本。我們需要將資本注入農村地區”。
而在曼谷的中產階級看來,他信那些傾向鄉村的政策是一種侵犯,是賄賂那些泥腿子、文盲和大老粗們的再分配。他們看到的政策本質是,占人口多數的農民通過民主的方式“侵占”了占人口少數的城市市民的財產。除了經濟上的損失,他們也不能容忍他信體制下國家權力的集中化。因為這違反了他們最小化國家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于是他們加入傳統精英所領導的反他信陣營,甘于充任傳統精英的小跟班。中產階級雖然弱小,但有一個特殊的優勢,即他們掌握著首都曼谷的媒體。
他信體制是1997年金融危機的產物,他是泰國歷史上第一個直接執政的大資產階級。執政之后,他信派所開創的新體制觸犯了傳統精英的利益,他們主要在幕后運作,必要時才沖到前臺。尤其是作為傳統利益格局的精神支柱的王室,其地位更是危險而微妙:既要維持受到他信嚴重沖擊的舊有體制,又不能太過偏倚,必須表現出某種超然性。這對王室的政治智慧提出了巨大考驗,在這個反對派陣營中,曼谷的中產階級是一股略顯奇異的力量,但置身于泰國獨特的歷史語境中,他們的選擇也屬合理。畢竟直到1973年,這個國家才迎來了他們的“1789年”——資產階級革命的時刻,但屬于另外一個階級的“1917年”又過早地在三年后降臨。歷史留給中產階級的政治空間很小。出于一個階層的政治直覺,他們知道自己不能在反他信運動中退讓,否則就意味著他信所開創的新政治模式的穩固。

回到短時段的時政分析,當前泰國的困局在于,他信新近動員起來的政治勢力在現行體制下不可能被打垮,一經選舉就會卷土重來。而城市民眾接受不了“民粹主義”和“腐敗”,在通常的議會選舉手段無效之后,他們開始嘗試街頭政治、“司法政變”,乃至軍人干預,來顛覆他信派政權,由此形成一個政治動蕩的循環。對于反他信派而言,似乎只剩下一個永久的解決辦法,就是推翻他信派政府后,成立一個不經選舉的政府,或者把憲法和選舉法大加修改,把農村勢力的代表壓縮到少數。在這種方案下,原有的精英階層固然會失掉他們所心愛的議會選舉體制,乃至相當程度的政治自由,但卻在經濟上保護了自己,免遭來自他信陣營的侵蝕。
葛蘭西曾經說過,當腐朽的力量拒絕退出舞臺,新生勢力難產時,就輪到鬼魅登場。葛蘭西目睹的是極右翼法西斯的上臺。今天的泰國將會上演的,除了軍人干預還會有什么,人們不得而知。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