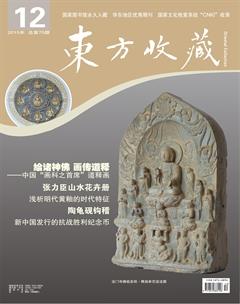《高僧圖》的畫派和年代小考



《高僧圖》,絹本,51×29厘米,美國回流。整個畫面的元素構成較為簡單,其背景一片空白,畫中主體僅為繪制單個高僧的正面立像,其身披袈裟,雙手托缽,表情溫和而透著虔誠(圖1)。畫的右上角有兩行題贊:一缽清凈水,能除饑和渴,世間諸有情,悉令獲安樂。何錀敬題。何錀的生平及相關資料,待考。何錀的書法與主體的高僧繪畫,墨色明顯不同,從古舊程度顯示書法要晚于繪畫。
單獨為高僧畫像,早在唐代便已存在,除了現存于大英博物館的白描紙本《高僧像》所繪制的無名高僧外,還有描繪不同時代的著名高僧,最為聞名的,便是存藏于日本京都教王護國寺的傳為李真的《不空真剛像》,還有近年筆者研究發現的八世紀中期的《金剛三藏像》(注1)。宋代時期,繪制名僧更是普遍,在日本東福寺,目前還存有《無準師范半身像》和《無準師范像》(圖2)等宋代重要作品。
本作《高僧圖》的畫面信息,如果單獨審視局部元素,似乎沒有任何特殊之處,但仍然具有可辨的南宋時代指向;若整體地串聯所有信息,其南宋的時代特征則清晰明顯,具體緣由筆者大致歸納如下:
一、畫面背景虛空。此作有意忽略了背景的描繪,去繁從簡,更能重點突出主體高僧形象,這種表現形式,正是南宋時期肖像寫生畫的典型風格,前面所述的東福寺的《無準師范半身像》和《無準師范像》,以及藏于美國各處的宋人《睢陽五老圖》(注2),便是采用類似的處理方法,《宋寧宗坐像像》和《宋寧宗后坐像像》等宮廷皇帝皇后系列畫像也同樣如此(圖3),當然,或因長時間寫生及畫中人物的身份,這些作品不乏配置座椅,除此,整個背景均是虛化放空。在南宋的諸多禪宗畫,也多是缺乏背景安排,以佛教禪宗的角度,或可理解為顯現空無一物的思想情懷。
二、衣紋結構簡潔。《高僧圖》的衣紋線條粗硬,簡潔挺括,方折剛勁,其結構展現清晰的南宋特征,這可從宮廷和民間兩方面的存世作品得到證實:
首先,與南宋畫院的馬遠這一派系的作品有頗多相似,從馬遠的《清涼法眼禪師圖》(日本天龍寺所藏)和《山徑春行圖》(臺北故宮藏)等山水場景中的人物結構,即可看出兩者的處理幾無二致(圖4),只是馬遠作品的線條帶有顫筆跡象,質感較為生拙。另外,馬遠基本保留線條的原始狀態,但《高僧圖》卻是敷上厚彩,線條略為模糊。宋人《孝經圖》雖然人物形象很小,也具備相似的特征(圖5)。此作原來定為南宋高宗書、馬和之畫,但園林石法的斧劈皴兼用淡墨染擦,卻是典型的馬遠、馬麟手法,其人物形態技法也顯示馬家法,且所題的書法,也與宋高宗不符,卻接近宋理宗。因此,以其核心的線條結構特征,結合馬遠、馬麟生活創作的年代,推斷《高僧圖》的繪制時間應在十三世紀初期。
其次,南宋時期的四明畫派陸信忠一脈,在衣紋結構的處理上也基本接近,這從陸信忠的《十六羅漢圖》中的書童及其流派所繪的《三童鼓板圖》的三個孩童,即可看出相互之間的關聯(注3、圖6),只是陸信忠的線條稍微柔性一些,不如上述作品的粗硬剛勁。
三、紋飾繁復且敷色趨于平面。《高僧圖》的袈裟在勾勒線條后,從背部鋪底,袈裟的正面再輕染紫灰色,在此基礎上,勾畫繁復的紋飾,最重要的是,在披肩和托缽采用金線勾畫,而服裝或道具勾畫紋飾,尤其是勾金技法,正是南宋四明畫派最重要的特征。
《高僧圖》的敷色,除了在個別的衣紋結構深凹處稍略加重,展現其起伏感,大多采用平面處理,而臉部更是完全的平面化,其顏色柔和,除了臉頰兩側微弱的降灰,五官凹凸起伏不作渲染,唯一可以顯示其立體感是眼睛微妙的深淺暈染,而這個方法,仍然是南宋時期四明畫派的基本特征。
分析宋元期間的四明畫派的敷色技法,可知時間靠前的作品,趨于平面化,時間靠后,則講究渲染結構變化,這個微觀局部的變化差異,也驗證了《高僧圖》歸屬南宋的基本斷代。
筆者在道釋畫系列研究序言(注4),曾經談到道釋題材發展到南宋,雖然流派紛呈,但歸納一下,無非三大流派:
1、以劉松年、李嵩為主的院體畫家,這一路基本延續正統主脈精整雅致的風格。
2、以牧溪、因陀羅為主的禪機畫,以簡練粗率的線條表現復雜的人體結構,屬于粗放野逸風格;
3、以四明畫派為主,風格色彩濃麗,充滿裝飾性和世俗化。
從挖掘的資料和現存的作品分析,這三大流派不乏相互轉換和借鑒。如梁楷由院畫轉為禪機畫,劉松年在羅漢題材也采用類似四明畫派的裝飾性的設色方法,根據上述的三大畫派的基本特征,且綜合《高僧圖》的所有繪畫信息,推斷《高僧圖》應是四明畫派的早期作品,其創作時間大約在十三世紀初期。
注釋:
注1、康耀仁《<金剛三藏像>考略》,《中國美術》 2015年02期 ,人民美術出版社。
注2、王連起《宋人<睢陽五老圖>考》,《故宮博物院院刊》 2003年01期。
注3、康耀仁《<三童鼓板圖>的創作題材和繪畫流派考》,《東方收藏》 2014年9期 。
注4、康耀仁《道釋題材研究系列——序言》,《東方收藏》 2014年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