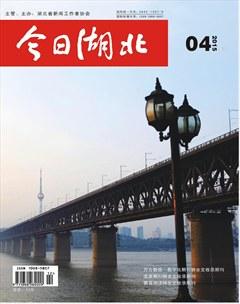《中國法制史》本科課程教學改革探析
李曉婧

摘 要 通過歷年司法考試“中法史”真題可以發現,司法考試強調對歷代法制及指導思想的總體認識、對專題性法制史、對貫概古今能力的考查。在《中國法制史》教學過程中存在很多問題,主要包括學生掌握知識的碎片化,缺乏現實關注。這不但不能使學生滿足司法考試的需要,更不能為解決現實問題提供歷史視角和借鑒。中國法制史教學應該側重法制思想和法律制度演變過程的系統考察,應該關注現實問題,培養學生古為今用的意識和能力。
關鍵詞 中國法制史 司法考試 本科教學改革
一、歷年司法考試《中國法制史》真題的特點
中國法制史自2003年首次列入司法考試大綱以來,大概占卷一總分值的8%左右(卷一總分值150分),即10分左右,題型主要集中在選擇題部分。其中,中法史試題的分值主要介于6~8分之間,當然也有例外,2003年和2005年的分值分別為10和11分。綜觀歷年司法考試“中法史”真題,其主要特點如下所述:
(一)強調對歷代法制及指導思想的總體認識
歷年司考“中法史”真題中,占據題數比例最大的不是哪朝哪代,而是對中國歷代法制的總體認識,高達16題之多(表1)。在這16題當中,對歷代法制指導思想的總體考查有4題(2005年卷1第63、64題、2009年卷1第57題、2014年卷1第56題);對中國古代法典總體演進歷程的考查有3題(2008年卷1第9題、2012年卷1第18題、2013年卷1第18題)。可見,司法考試“中法史”真題側重對歷代法制及其指導思想的總體認識,而不局限于單獨的知識點。在制度及其指導思想總體認識和發展脈絡之中學習中法史,是司考“中法史”題目的重點。
(二)注重對專題性法制史的考查
中國法制史傳統教學中主要以時間序列為線索向學生講述法制歷史的源流,法制的時代特性較為顯著,但與部門法教學不能相對應,致使教學內容的體系性方面常有缺憾。如果能以部門法史對之作補充,則有利于通過縱橫結合,使學生對知識的定位更加準確,加強和深化與現代部門法之間對比了解。以選拔實務性法律人才為宗旨的司法考試,已開始注重對專題性法制史的考查,如對中國憲法發展史的考查(2005年卷1第94題),對中國古代刑罰制度史的考查(2010年卷1第15題),對中國古代民事法制史的考查(2007年卷1第10題),對中國古代訴訟制度史的考查(2009年卷1第58題)。部門法史的發展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法史研究深化的重要表現之一,這說明中國法史學界已經開始突破中國古代的法律就是刑法的陳舊觀念而以一種更加開闊的視野來考察中國傳統法制,大量憲政、經濟、民事、行政法史等研究成果問世。可以看出,專題性法制史既是學術界關注的熱點之一,也是實務界所親睞的對象。
(三)貫概古今
值得一提的是,在2007年和2009年司法考試卷4中,有涉及到中國法制史的分析論述題,分值在20~25之間。如2007年卷4第7題,即要求根據題目中所提供的素材,從古代的“無訟”、“厭訟”、“恥訟”觀念到當代的訴訟案件數量不斷上升的變化,自選角度談談對該問題的看法。該題是一道理論聯系實際的典型,它告訴我們,學習中法史不僅僅是對歷史的回顧,更重要的是以史為鑒,如何服務于當下社會。中國“無訟”的價值觀念乃是在道、儒、法等中國哲學思想的長期影響下,形成的“和為貴”、“讓為賢”等根深蒂固的法律思想,老百姓“以訟為恥”,認為“對簿公堂”是極不光彩的事。統治者也力行“德主刑輔”,強調道德倫理教化,不重視運用訴訟方式解決爭議。在中國快速發展經濟的過程中,人們似乎又走上另一個極端,將訴訟當作解決糾紛的唯一或者最主要的方式,動不動就訴諸法院。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是國家民主法制建設進程加快,公民法律意識、維權意識的增強以及司法解決爭端的有效性、權威性和終極性特點的基本反映。但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訴訟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如程序繁瑣、費用昂貴,時間持久,特別是難以做到當事人之間不傷和氣與維持原有和睦關系。因此,在實踐中盡可能減少訴訟,引導、鼓勵當事人把訴訟作為最后的救濟手段,大部分案件盡量通過和解、調解、仲裁等方式解決。總之,要根據實際情況,均衡得失,采取一種更為恰當的解決方式。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告別無訟是歷史的必然趨勢,是社會進步的體現。但過于強調訴訟的作用,也非法制建設的本意。“好訟”盛行之下,大量的司法資源被無謂地浪費,當事人也為之付出了代價。所以,“厭訟”固不可取,“好訟”的負面效應也必須正視。這就是歷史帶給我們的經驗和教訓。
二、《中國法制史》本科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現在法學專業學生對《中國法制史》的學習興趣不大,動力不足,效果不好。現在法學教學觀念和方式不但無法滿足司法考試的需要,更遑論為解決現實問題提供歷史視角和歷史借鑒。
(一)掌握知識的碎片化
在中國法制史這門課的教學過程中,很多學生都反映這門課體系雜亂、知識點零散,因而學起來難度大,考試不容易拿到高分甚至不好通過。實際上,中法史兼具史學和法學雙重性質,同時也具有法學和史學的雙重難度。古代法律制度的產生與發展都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密切聯系,要想理解某一制度必須對當時的社會狀況與文化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如果單純用法律語言去解釋,只能使內容更加晦澀難懂。
中國歷史上有很多各具特色的法律制度,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很容易把心思傾注到對各個知識點的記憶,而忽視了從整個歷史長河的視角來把握法律制度的流變。比如說,明清時期“三司會審”中的刑部,其職能是國家最高審判機關,總掌“天下諸刑獄”;大理寺的職能是國家慎刑機關,“掌審讞平反刑獄之政令”。有的學生在學習了明清的司法制度后,忽略了對之前唐宋時期刑部和大理寺職能的回顧,而這一時期,大理寺主管審判,對應的是明清的刑部;刑部主管復核和司法行政,對應的是明清的大理寺。如果學生只是單純記憶各個時期的司法機關及其職能,而沒能將整個歷史時期的司法機關集中起來加以對比學習,那么知識的掌握就比較碎片化了。
(二)缺乏現實關注
中國法制史課程的教學目的是要幫助學生認識中國法制的歷史演進過程,認識歷史上法制的成功與失誤,認識當代中國顯性和隱性法制的本土淵源,認識中國法律傳統的基本特征,認識在西方法制沖擊下中國法制近現代化的得失利弊,認識中國傳統法律文化遺產對當今法制建設的正負作用和意義。但在授課過程中,有些老師忽視了對現實問題的關注,只講課本知識,同時,學生也沒有意識將古今聯系起來加以對比分析,導致很多學生在學完這門課之后便很快忘記了各色各類的知識點,將中法史知識扔進了歷史的海洋。歷史只有跟現實聯系起來加以分析才具有永恒的魅力,如果單單學習歷史而忽略其傳承性,缺乏足夠的現實關注,那么歷史只能是空中樓閣,毫無任何生命力可言。比如說,在講授漢代“親親得相首匿”法律原則時,切勿就事論事。具體來說,在法律儒家化的歷史背景下,除謀反、謀叛和謀大逆等嚴重危害皇權的十惡不赦罪行外,親屬間互相隱瞞罪行,即同居相隱不為罪。而在現行《刑法》中,親屬之間相互隱瞞罪行就會構成包庇罪。比較之后,教師提出問題:我國現在有無必要實行“親親得相首匿”原則?如有必要,哪些犯罪可以適用,怎樣界定親屬的范圍。進而讓學生思考:自清末變法至今,我國引進大量法律制度,建立了較為完善的法律體系,由于在某種程度上忽視了對自身法律傳統的總結、理解,導致在法律實踐中出現天理、國法與人情的現實矛盾沖突,作為法學學生,應該怎樣做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
三、《中國法制史》本科教學改革的方向
在對中國法制史本科教學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加以分析之后,筆者結合歷年司考“中法史”真題的特點,并以此為視角,認為有必要對中法史課程進行相應的教學改革,以達到中法史教學的目的。
(一)對歷代法制指導思想發展歷程的梳理
學習中國法制史必然離不開對歷朝歷代法制指導思想的深刻領悟。縱觀中國古代法律思想的發展歷程,從中我們可以尋找出其基本發展脈絡:中國早在商、周兩個朝代就已經形成了相當完整的法律,也開始形成有系統的法律思想。西周統治者提出的“明德慎罰”思想,對于后世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春秋戰國時期,文化領域出現了“百家爭鳴”,“百家爭鳴”時代的學說奠定了以后兩千多年法律思想的基本面貌。自秦朝后大一統政治局面形成,如何更好地維護和鞏固這種君主專制中央集權,成為以后兩千多年中國思想界討論問題的出發點和中心任務。兩漢時經改造的儒家禮教逐漸成為一種正統的官方理論,其對法律的定位和論斷也就成為指導立法和司法實踐的重要因素。思想的爭鳴已經過時,不能再被統治者所容忍,只是在若干的具體問題上后世的思想家有一定的發展。鴉片戰爭開始打破中國傳統社會的結構,隨著空前的統治危機以及民族危機的加劇,反映在思想界也再次出現了爭鳴的局面。維新運動時期,歐美的法律學說開始傳入,猛烈地沖擊中國思想界,這一趨勢在20世紀初依舊存在。然而由于20世紀初中國處在長期的戰亂之中,并沒有具備建設近代化法制所需要的穩定的社會條件,也沒有給思想界充分吸收消化匆忙引進的歐美各類法學流派的機會,更沒有創立本土法學學派的可能。尤其是引進的法律制度、法學學說和中國社會脫節,形成了西化的社會精英階層法律思想和保留傳統觀念的民間法律意識的巨大鴻溝。
(二)對歷代法典更迭與演進的梳理
歷朝歷代的法典編纂及其演進歷程是中國法制史課程的重中之重。宏觀地掌握整個歷史時期的立法動態,是我們學習中法史的基本任務。中國法制文明起源于炎黃時代,自那時起至今,已經歷了五千年漫長的進化。在這一漫長的法制發展歷程當中,法典的編纂代表了中國法律文化的基本走向。但由于中國古代朝代眾多,且每朝每代的法典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更迭,這就造成了學生在掌握這一知識點時存在困難。為了方便大家掌握該知識點,我們不妨將其演進歷程做成一張圖表,以便更加形象地加以對比分析(圖1)。
(三)注重古為今用
在中國法制史教學過程中,教師應該讓學生從比較法的視野來思考古今中外的法律制度。比如說:(1)在2008年刑法的修訂過程中,對于年滿75周歲的老人的刑罰適用,可以聯系中國古代尊老恤幼的法律原則加以探討。(2)在講授中國古代的直訴制度,即登聞鼓制度時,可以把擊登聞鼓這種古代進京上訪的主要形式與當今存在的進京上訪進行比較,使學生認識古代的“越訴”和“京控”與今天的上訪從歷史根源上是一致的,進而認識到現今上訪形成的原因并深入理解法律文化的傳承性。(3)在談到明代朱元璋“重典治吏”這個知識點時,可以聯系當下大力打擊貪污腐敗的現象,體味傳統與現今中央對治理貪腐的決心。總而言之,通過聯系當前法律實踐,能夠賦予中法史教學以更多的活力,必然能夠大大激發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在引導學生關注現實法律問題的同時,強化了對中法史知識的理解,提高透過表象從深層次把握法律問題的能力。
四、結語
博登海默曾言:“攻讀法律的學生如果對其本國的歷史很陌生,那么他就不可能理解該國法律制度的演變以及該國法律制度機構對其周圍的歷史條件的依賴關系。”①學好中國法制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現代大學生在學習中法史過程中暴露出很多問題,比如學習法制史缺乏系統,不能從古今中外比較的角度去認識中國法制史中的概念、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從司法考試的趨勢來看,從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的源流過程來理解具體的法律制度,是考試的方向。那么,無論是提高學生學習中法史的興趣,還是提高學生中法史的理論素養,還是應對司法考試,都需要在教學方面有所改變。教師在教授中法史課程時,應該在我國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源流和脈絡的背景下去講授某個具體法律制度,應該在古今比較的視野下去講授中國古代法律制度。這樣有助于提高學生學習中法史的興趣,有助于為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提供歷史思維。
注釋:
①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鄧正來,姬敬武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22.
(作者單位:安徽師范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