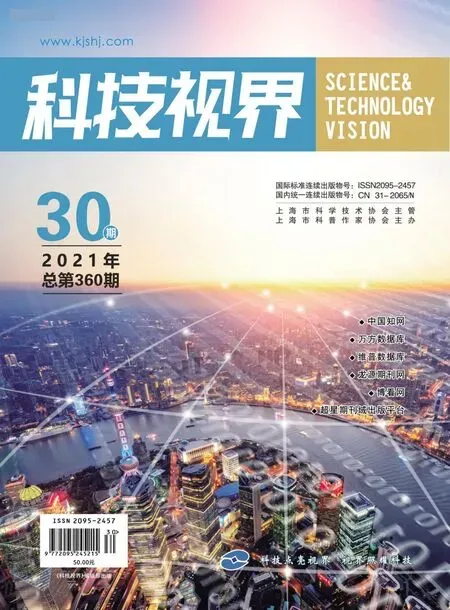淺述礦產資源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
訾閃 孟海東 陳杰
【摘 要】經濟增長作為區域發展的核心問題,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包括資本、勞動、技術、制度和資源稟賦等諸多因素。自然資源開發與資源開發地經濟增長的關系問題是發展經濟學的前沿熱點問題,也是區域經濟學、人口資源環境經濟學等學科領域的重點研究課題。
【關鍵詞】資源詛咒;促進作用;阻滯作用
胡援成,蕭德勇[1]年在論證我國省際層面存在自然資源詛咒的同時, 重點研究了制約資源詛咒現象的經濟因素。通過模型的構建和運用面板門檻回歸分析,分析后認為人力資本的投入水平是制約我國省際層面資源詛咒存在的關鍵因素, 人力資本投入能夠有效地解決資源詛咒現象。另外, 實證結果還揭示了金融支持作為緩解資源詛咒重要途徑的同時, 還可以有效地解決資源的硬約束, 促進經濟的可持續性增長。景普秋,王清憲[2]提出礦產資源,在區域經濟發展中是一把雙刃劍, 既可能成為經濟發展的催化劑或者“引擎”, 也可能給區域發展帶來區域收入差距擴大、反工業化、經濟增長波動、等“資源詛咒”現象。文章從省域、地級市、縣域三個層面, 通過對豐富的煤炭資源與山西經濟增長、結構演進、區域差異等方面的關系研究, 論證了煤炭資源開發給山西經濟發展帶來的正反兩方面影響: 是經濟增長的動力, 也加劇了經濟增長的波動; 推動了經濟與就業的非農化, 也是資源產業向制造業、第三產業進一步演進的制約因素; 加快了人口城鎮化進程, 卻造成工業化與城鎮化之間嚴重的偏差現象; 區域人均收入迅速提高的同時, 區域收入差距也在擴大。張復明,景普秋[3]提出由于制造業部門人力資本投資門檻的存在,在資源豐裕區域, 容易導致對資源部門的投資偏好。一旦資源部門成為主導部門,便會形成資源部門對經濟要素特殊的吸納效應、資源部門的擴張與延伸使產業家族形成粘滯效應、工業化演進過程中的沉淀成本與路徑依賴形成對資源功能的鎖定效應,產生發展的路徑依賴,陷入資源優勢陷阱,從而導致資源型經濟的自強機制。突破資源優勢陷阱的關鍵在于打破原有的資源自循環機制和路徑依賴,引入學習與創新活動,調整資源收益分配機制,實現產業協調和經濟轉型發展。王文行,顧江[4]對資源詛咒問題的研究進行了系統的文獻論述,對其形成的原因機理進行了介紹,最后針對我國資源型地區提出了一些防止“資源詛咒”的措施。邵帥,齊中英[5]利用1991—2006年的省際面板數據對“資源詛咒”現象進行了實證分析,并且分析了導致資源詛咒的傳導機制,并且實證考察得知人力資本投入是作用最強的傳導因素。景普秋[6]提出礦產資源開發與區域經濟發展正、反兩方面觀點,似乎都離不開資源行業出現的巨額利益。礦產開發中收益分配機制是否合理,相關制度是否健全,可能是資源豐裕地區是否陷入“資源詛咒”的關鍵,也是未來研究的關鍵問題。同國外研究一樣,盡管大量文獻表明礦產資源與經濟增長之間負相關,但是這并不是結論性的,因為在其他一些統計研究中并沒有資源詛咒現象。程志強[7]利用內蒙古省內的煤炭數據,經過計量分析,發現資源繁榮對內蒙古經濟產生了正向效應,倒是資源衰退對內蒙古經濟產生了負向效應。
進入新世紀以來,受資源價格持續走高所帶來的巨大經濟利益驅動,礦產開發得到了快速發展,釆礦業已成為資源型地區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的主導產業。但同時,隨著礦產資源的大規模開發和粗放利用方式導致資源型地區正面臨著諸多發展難題,例如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資源浪費和資源枯竭、失業率高和貧困加劇、礦難頻發和收入差距擴大等各類社會經濟矛盾較為突出。也就是說資源開發能為地區帶來財富和發展機會的同時,也帶來無法估量的負效應。
采掘業等資源型產業從制造業和技術產業中吸收勞動、資本等生產要素,使制造業和技術產業的發展受到一定程度的打擊,從而制約經濟增長。一是當某種自然資源被發現或者價格意外上漲,將會導致勞動和資本等生產要素向資源出口部門發生轉移,制造業部門不得不花費更多的時間與成本來吸引新的生產要素。由此導致制造業勞動成本上升將會打擊制造業的市場競爭力,最終阻礙經濟的增長。這是資源轉移效應。二是自然資源產品出口增加帶來相應收入的增加會對制造業和服務業產品需求的增加。但由于制造業生產要素被轉移到資源部門,故本地區對制造品的需求只能通過吸收外部價格相對便宜的同類產品來滿足,這將進一步打擊本地區制造業。
礦產資源與教育方面,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或地區資源產業部門本身不注重對高素質、高技術的人力資本需求,使得低估了教育和科技研發的長期價值,因此忽視了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并且自然資源 發部門的高利潤率誘使更多的人力資本從制造業部門和其他創造性部門轉移出來,削弱了制造部門“干中學”效應以及創造性部門的技術溢出效應,從而阻礙了整個經濟的技術進步。這是擠出效應。礦產資源與電力方面,作為礦產資源型產業,如果其能耗過高,將會嚴重降低礦產資源型產業的生產效率,進而影響礦產資源型產業的利潤和進一步發展。
結論:通過對礦產資源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研究可以為礦產資源的開發與利用提供決策支持。從而,使得資源城市經濟更加健康更加穩定的向前發展。指導適度的礦產資源開發力度充分考慮到了經濟、社會、自然、環境等的承載能力,將開發行為的外部性降到最低,并且為資源地區經濟協調、解決礦產資源地區可持續發展問題提供依據,加快我國實現共同富裕的最終目標,縮小區域經濟差距,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推動社會進步,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1]胡援成,蕭德勇.經濟發展門檻與自然資源詛咒-基于我國省際層面的面板數據實證研究[J].管理世界,2007:15-23.
[2]景普秋,王清憲.煤炭資源開發與區域經濟發展中的“福”與“禍”:基于山西的實證分析[J],中國工業經濟,2008:80-90.
[3]張復明,景普秋.資源型經濟的形成:自強機制與個案研究[J].中國社會科學,2008:117-130.
[4]王文行,顧江.資源詛咒問題研究新進展[J].經濟學動態,2008:88-91.
[5]邵帥,齊中英.西部地區的能源開發與經濟增長:基于“資源詛咒”假說的實證分析[J].經濟研究,2008:147-160.
[6]景普秋.資源詛咒:研究進展及其前瞻[J].當代財經,2010(11):120-128.
[7]程志強.煤炭資源開發地區發展滯后的原因分析[J].宏觀經濟管理,2007(9):28-31.
[責任編輯:曹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