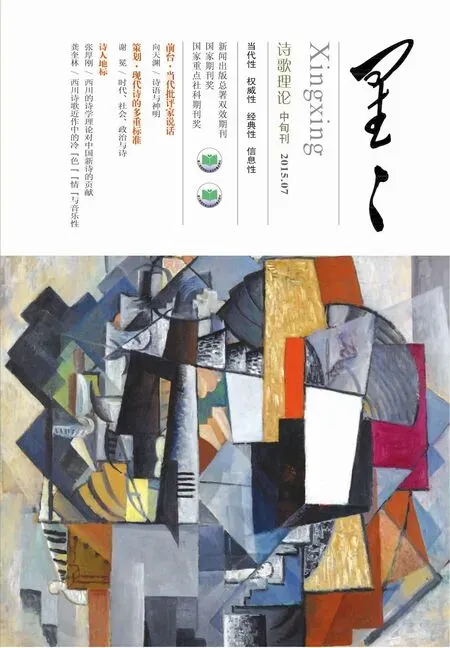詩(shī)歌,我生命中的精神家園——20世紀(jì)80年代大學(xué)生詩(shī)歌運(yùn)動(dòng)訪談錄之彭國(guó)梁篇
訪問者:姜紅偉
受訪人:彭國(guó)梁
詩(shī)歌,我生命中的精神家園——20世紀(jì)80年代大學(xué)生詩(shī)歌運(yùn)動(dòng)訪談錄之彭國(guó)梁篇
訪問者:姜紅偉
受訪人:彭國(guó)梁
姜紅偉:有人說20世紀(jì)80年代是中國(guó)大學(xué)生詩(shī)歌的黃金時(shí)代,您認(rèn)同這個(gè)觀點(diǎn)嗎?
彭國(guó)梁:我認(rèn)為不僅是中國(guó)大學(xué)生詩(shī)歌的黃金時(shí)代,也是當(dāng)代詩(shī)歌的黃金時(shí)代。我記得曾在網(wǎng)上看過一篇文章說,八十年代,女孩們對(duì)自己喜歡詩(shī)人的狂熱崇拜,一點(diǎn)不次于今天的美女們對(duì)富翁、名牌的崇拜,詩(shī)歌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姜紅偉:請(qǐng)您簡(jiǎn)要介紹一下您投身20世紀(jì)80年代大學(xué)生詩(shī)歌運(yùn)動(dòng)的“革命生涯”。
彭國(guó)梁:當(dāng)年我年僅十六七歲,在與數(shù)百名老知青的競(jìng)爭(zhēng)中考入大學(xué)中文系,剛進(jìn)入中文系時(shí),全班近60人,每個(gè)人都以為自己是理所當(dāng)然的作家,拼命地向有影響文學(xué)刊物投稿(需要說明一點(diǎn),當(dāng)時(shí)投稿無需花錢買郵票,只要寫上“郵資已付”即可)。遺憾的是,每個(gè)班級(jí)的信箱里,每天都是塞得滿滿的退稿,漸漸地,退出的人越來越多,我是堅(jiān)持到最后的,同學(xué)中有人戲稱我為“退稿專業(yè)戶”。
我記得第一次發(fā)表詩(shī)作是1981年2月,正值寒假,我隨手買了一本當(dāng)時(shí)較有影響力的文學(xué)刊物《滇池》,競(jìng)驚喜地發(fā)現(xiàn)發(fā)表了我的兩首短詩(shī),一個(gè)月后,我收到了第一次稿酬,12元人民幣(當(dāng)時(shí),那可是半個(gè)月的生活費(fèi))。從那以后,我投稿的采用率大幅提升,退稿越來越少,相繼在《人民文學(xué)》、《詩(shī)刊》、《中國(guó)作家》、《青春》、《星星》、《詩(shī)人》、《萌芽》、《青年作家》、《飛天》、《綠風(fēng)詩(shī)刊》、《丑小鴨》、《人民日?qǐng)?bào)》、《中國(guó)青年報(bào)》、《滇池》、《鹿鳴》、《百花園》等全國(guó)性報(bào)刊發(fā)表詩(shī)歌,至大學(xué)畢業(yè),應(yīng)該發(fā)表了近三百首詩(shī)作。
1983年,我獲得云南省首屆“魯迅文學(xué)獎(jiǎng)”。同年,我加入昆明作家協(xié)會(huì),并當(dāng)選為最年輕的理事。83年至84年,昆明作協(xié)、云南作協(xié),分別舉行過“彭國(guó)梁詩(shī)歌討論會(huì)”,當(dāng)時(shí)我還沒滿22歲。當(dāng)時(shí)的《詩(shī)選刊》、《讀者》及各種國(guó)內(nèi)青年詩(shī)選,大學(xué)生詩(shī)選幾乎都收錄過我的詩(shī)歌。
姜紅偉:為大學(xué)生舉辦作品研討會(huì),在當(dāng)年可是一件了不起的榮譽(yù),極為罕見,能否談?wù)務(wù)匍_“彭國(guó)梁詩(shī)歌討論會(huì)”的過程?
彭國(guó)梁:為我開個(gè)人詩(shī)歌作品討論會(huì),我的確沒想到。我印象中,中國(guó)作協(xié)開過楊朔、郭小川的作品討論會(huì)。1983年,我已發(fā)表了一百多篇作品,算是嶄露頭角,昆明作協(xié)的前輩們居然破天荒地組織了一次詩(shī)歌作品討論會(huì),討論了沈駿康、劉揚(yáng)和我的作品,參加者有前輩詩(shī)人、作家、評(píng)論家、出版社、文學(xué)雜志負(fù)責(zé)人,當(dāng)時(shí)各報(bào)刊皆發(fā)了新聞,我記得在這次討論會(huì)上,一位姓聶的詩(shī)評(píng)家(好像是聶耳的至親),說我“才情有余、功底不足,應(yīng)博覽群書、充實(shí)知識(shí)”,使我受益頗深,至今仍遵循此忠告。
市作協(xié)先行了,省作協(xié)也不甘落后,不到一年時(shí)間,省作協(xié)組織了一次規(guī)模更大的彭國(guó)梁、于堅(jiān)、劉揚(yáng)詩(shī)歌作品討論會(huì)。討論會(huì)歷時(shí)一天,爭(zhēng)論不休,有肯定的、有擔(dān)心路走偏的,云南的知名詩(shī)人、評(píng)論家、中文系教授、省委宣傳部、文化廳、各報(bào)刊,近八十多人參加討論會(huì),晚上還舉行了舞會(huì)。兩次討論會(huì)的報(bào)道、照片已很難尋找到了,但我的藏書中至今仍有這兩次討論會(huì)作協(xié)花錢購(gòu)買、蓋著紅章、送給參會(huì)者紀(jì)念品:兩本書,一本是《荊棘鳥》,一本是《蘇聯(lián)當(dāng)代詩(shī)選》。
據(jù)我所知,后來,再無青年詩(shī)人獲此殊榮。
姜紅偉:當(dāng)年,您創(chuàng)作的那首《男人的海和女人的網(wǎng)》曾經(jīng)很受讀者喜歡,能否談?wù)勥@首詩(shī)的創(chuàng)作、發(fā)表過程?
彭國(guó)梁:當(dāng)年在《青春》雜志發(fā)表的一首叫《男人的海和女人的網(wǎng)》,使我持續(xù)三個(gè)月收到各地讀者來信,累計(jì)起來有近萬封吧,《詩(shī)選刊》也曾予轉(zhuǎn)載。
這首詩(shī)是我去大連漁村小住了一段時(shí)間,聽漁民們講述了出海時(shí)生離死別的故事,恰好當(dāng)時(shí)我又癡迷洛蒂的小說《冰島漁夫》,人生中聚散兩依依的情緒感染了我,寫完時(shí),自己也被感動(dòng)得熱淚盈眶。
寫完這首詩(shī)時(shí),我已經(jīng)小有名氣了,有刊物約稿了,給一般刊物發(fā)表根本不成問題,連《人民文學(xué)》這樣的大刊物,我都上過頭條,而且一發(fā)就是一組三首。當(dāng)時(shí),在青年及大學(xué)生中影響巨大的《青春》我還沒發(fā)表過詩(shī)作,我鼓起勇氣,把詩(shī)投給了《青春》,不到一個(gè)月,我就收到了《青春》詩(shī)歌組長(zhǎng)馬緒英老師的親筆回信,告知我準(zhǔn)備刊發(fā)。(在當(dāng)時(shí),有影響的文學(xué)刊物的詩(shī)歌組長(zhǎng)親筆給一個(gè)大學(xué)生回信,并說今后詩(shī)作可直接寄他本人收,那可是莫大的榮幸)。
1987年,我旅行結(jié)婚時(shí),專程到南京拜訪了馬緒英老師。
姜紅偉:在大學(xué)期間,您參加或者創(chuàng)辦過詩(shī)歌社團(tuán)或文學(xué)社團(tuán)嗎?擔(dān)任什么角色?參加或舉辦過哪些詩(shī)歌活動(dòng)啊?
彭國(guó)梁:大學(xué)期間,我并沒在學(xué)校創(chuàng)辦詩(shī)社,只是輔導(dǎo)八一級(jí)、八二級(jí)的同學(xué)創(chuàng)辦“一多文學(xué)社”(因我上學(xué)的云南師大前身是赫赫有名的西南聯(lián)大),但我和云南的一群中青年詩(shī)人一起倡導(dǎo)創(chuàng)立了“紅土高原詩(shī)派”,以現(xiàn)代詩(shī)表現(xiàn)云南人文、地理、歷史、自然風(fēng)光為主,當(dāng)時(shí)除愛情詩(shī)外,我在各地發(fā)表的詩(shī)作,寫云南風(fēng)光的最多,僅瑞麗江、麗江、中甸(今天的香格里拉)我就寫了有幾十首之多。記得有一年《人民文學(xué)》的冼寧老師來云南組稿,她從瑞麗回昆明后說:“到瑞麗江一看,一點(diǎn)也沒有彭國(guó)梁寫得美。”也因?yàn)檫@個(gè)原因,她把我的《瑞麗江的黃昏》發(fā)在了《人民文學(xué)》的詩(shī)歌類首條,排在了很多著名作家之前。
1986年,徐敬亞主持的《深圳青年報(bào)》和《詩(shī)歌報(bào)》聯(lián)合舉辦中國(guó)詩(shī)壇1986年現(xiàn)代詩(shī)群體大展,我與同校詩(shī)友劉揚(yáng)以“黃昏主義”詩(shī)派參展。至于到各大學(xué)組織詩(shī)歌講座,幾乎每月幾次,太頻繁了。最令我感動(dòng)的是,有一年我到麗江采風(fēng),麗江師專的近千名詩(shī)歌愛好者在雨中聽我演講朗誦。
姜紅偉:“紅土高原詩(shī)派”在當(dāng)年影響很大,能否為我們介紹一下這個(gè)詩(shī)派的主要成員、主要作品、主要刊物和影響?
彭國(guó)梁:“紅土高原詩(shī)派”的創(chuàng)立,源于1979年轟動(dòng)藝術(shù)界的一件大事,即袁運(yùn)生、連維云、費(fèi)正的壁畫“潑水節(jié),生命的贊歌”在北京首都機(jī)場(chǎng)出現(xiàn)。這是在中國(guó)的公眾場(chǎng)所,第一次出現(xiàn)裸體女人,并以現(xiàn)代手法展現(xiàn)云南的原生態(tài)文化。當(dāng)時(shí),云南的畫家如蔣鐵峰、丁紹光、毛旭輝、潘德海、裴鳳安、張曉剛(這些人中不少后來都成了馳名世界的繪畫大師)等人,率先嘗試以現(xiàn)代手法表現(xiàn)云南,米思及、湯世杰、胡延武、我、劉揚(yáng)、沈駿康等也經(jīng)常聚會(huì)在咖啡館,探討用現(xiàn)代詩(shī)歌手段表現(xiàn)云南的歷史、人文、風(fēng)光,當(dāng)時(shí)組織了很多次在報(bào)刊上的詩(shī)歌群體出現(xiàn),評(píng)論界也搖旗助威,在當(dāng)時(shí)對(duì)云南的文學(xué)青年影響巨大,延續(xù)了很多年(后來我不認(rèn)識(shí)、沒聽說過的不少人都號(hào)稱是“紅土高原詩(shī)派”創(chuàng)始人、主將。令人啼笑皆非)。也獲得外省著名詩(shī)人如新疆楊牧、周濤、貴州李發(fā)模的贊譽(yù)。
姜紅偉:能否談?wù)勀蛣P(yáng)創(chuàng)辦黃昏主義詩(shī)派的過程?
彭國(guó)梁:劉揚(yáng)是我同校摯友,我們之間可以說每天形影不離,從交流詩(shī)藝、交流戀愛經(jīng)驗(yàn)、又互借書籍,無所不談。當(dāng)時(shí)他的一位女崇拜者,從北京郵來日本抒情音樂創(chuàng)始人小田和正(即人們熟悉的《東京愛情故事》主題歌“突然降臨的愛情”創(chuàng)作者)的磁帶,我們常常在一起聽,小田和正那帶有東方情調(diào)又憂傷抒情的音樂,使我們?nèi)绨V如醉,我們喜歡的詩(shī)也大多相似,所以,我們一直認(rèn)為:柔情如黃昏,寧?kù)o如黃昏,是詩(shī)的至美境界,所以當(dāng)時(shí),徐敬亞在《深圳青年報(bào)》舉行現(xiàn)代詩(shī)群大展,我們便以“黃昏主義”為名參展了。
參展之后,云南一批認(rèn)同我們觀點(diǎn)的青年詩(shī)人如:亞楠、伍林偉、王坤紅、段瑞秋、徐剛等也加入了“黃昏主義”詩(shī)派,《昆明日?qǐng)?bào)》還發(fā)過專版予以介紹。
姜紅偉:您參與創(chuàng)辦過詩(shī)歌刊物嗎?您參與創(chuàng)辦過詩(shī)歌報(bào)紙嗎?編印或出版過詩(shī)集嗎?
彭國(guó)梁:當(dāng)年各地高校均有詩(shī)歌刊物,我大學(xué)二年級(jí)時(shí),各地文學(xué)雜志及大學(xué)生詩(shī)刊的約稿已應(yīng)接不暇了,所以沒親自辦刊物。
雖發(fā)表詩(shī)歌總計(jì)六百多首,但經(jīng)商后無暇整理出版。1987年,云南作協(xié)與云南人民出版社要出一套青年詩(shī)叢,大學(xué)生中選了我、于堅(jiān)、劉揚(yáng)三人,全國(guó)著名詩(shī)人評(píng)論家曉雪為我的詩(shī)集寫了序,這算我們第一次正式出書吧。至于被選家選入各種詩(shī)集、詩(shī)選的有50余首。
前三年,自己整理了兩本詩(shī)集,一直忙,未付梓出版。姜紅偉的采訪再一次勾起了我的激情,但愿今年能了此心愿。
姜紅偉:作為20世紀(jì)80年代云南大學(xué)生詩(shī)壇的兩大巨頭,您和于堅(jiān),始終是當(dāng)年大學(xué)生詩(shī)歌愛好者崇拜的偶像,能否談?wù)勀陀趫?jiān)當(dāng)年的交往故事?
彭國(guó)梁:我和于堅(jiān)同為八○級(jí)學(xué)生,也是當(dāng)時(shí)云南大學(xué)生詩(shī)人中在云南省內(nèi)外發(fā)表作品最多的,云南大學(xué)和云南師大僅一街之隔。我們幾乎每周都參加對(duì)方的詩(shī)社活動(dòng),他好像是五十年代初出生的,閱歷比我這個(gè)應(yīng)屆畢業(yè)生豐富,所以我們的創(chuàng)作風(fēng)格各異,他的詩(shī)作更凝重、粗獷,受聶魯達(dá)、埃利蒂斯、桑德堡、艾略特、馬爾克斯影響更多;我的詩(shī)清麗細(xì)膩,受葉賽寧、弗羅斯特、西門內(nèi)斯、艾呂雅影響更多。當(dāng)時(shí)我們出現(xiàn)在各種大學(xué)生詩(shī)歌活動(dòng)時(shí),個(gè)人衣著風(fēng)格也各異,他是牛仔褲配粗格衣服,美國(guó)西部牛仔風(fēng)格;我則滿頭卷發(fā),一襲雪白的西服,佩黑領(lǐng)結(jié),紳士風(fēng)度十足,有詩(shī)友評(píng)價(jià)說:“于堅(jiān)討男人喜歡,彭國(guó)梁討女人喜歡。”當(dāng)時(shí),我們崇拜者不少,也很狂。記得一次參加作協(xié)組織的火把節(jié)活動(dòng),我、于堅(jiān)、劉揚(yáng)在一處風(fēng)景獨(dú)秀、身后有三座山峰的地方曾三人在一起,各擺了一個(gè)造型,拍過一張合影,拍攝后于堅(jiān)對(duì)著一群文學(xué)青年說:“這張照片就叫三大師吧,一定會(huì)留名文學(xué)史。”
當(dāng)我們的第一部個(gè)人詩(shī)集出版時(shí),我經(jīng)商幾年了,擔(dān)任云南一家知名藥廠的營(yíng)銷總監(jiān),當(dāng)時(shí)各自簽名送了對(duì)方一本自己的詩(shī)集,以后便很少聯(lián)系了。
他一直堅(jiān)持寫詩(shī)至今,成就卓著,殊為不易。
姜紅偉:上世紀(jì)80年代大學(xué)生詩(shī)人們最熱衷的一件事是詩(shī)歌大串聯(lián),您去過哪些高校嗎?和哪些高校的大學(xué)生詩(shī)人來往比較密切最后成為好兄弟啊?
彭國(guó)梁:給詩(shī)友寫信交流,是當(dāng)時(shí)我的最愛。交往最久、交情最深的當(dāng)數(shù)北京大學(xué)的駱一禾,他來云南,就住在我家,我們抽完了一盒盒“大重九”香煙,縱論上下五千年,可謂指點(diǎn)江山、激揚(yáng)文字。我去北京也多次去他家吃飯,沒想到89年我去他家時(shí),他姐姐說,他腦溢血住院,我趕到醫(yī)院,隔著窗看到他正在昏迷中,沒說上一句話。沒想到,回昆明沒幾天,就聽到了來自北京的噩耗,他英年早逝,我至今每每回憶起來,都覺得如夢(mèng)一般。一個(gè)文靜、才華橫溢的年輕人,怎么說走就走了呢,真叫人心痛。蘭州大學(xué)的封新成也是書信來往較多的一位,我記得他的字極雋秀,后來得知他創(chuàng)辦新銳雜志《新周刊》任執(zhí)行總編,也許因?yàn)橛亚榈木壒拾桑抑两袢允恰缎轮芸返闹覍?shí)讀者。
黑龍江的潘洗塵是和我通信最多的,《大學(xué)生詩(shī)壇》剛創(chuàng)辦,他即向我約稿,他熱情、精力充沛,無愧于大學(xué)生詩(shī)歌運(yùn)動(dòng)急先鋒稱號(hào)。因?yàn)樗脑颍蚁群笈c楊川慶、蘇歷銘通信。87年我出差北京時(shí),還抽空去找了蘇歷銘,他好像在國(guó)家計(jì)委,我們一起在餐廳吃了飯。
像安徽的曹漢俊、上海的張小波、王寅、湖南的陳惠芳、廣東的辛磊,都有過書信往來。
四川大學(xué)的程寶林通了幾封信,他只身到云南來找我了,在我家住了好幾天,我們徹夜長(zhǎng)談。(后來聽說移民美國(guó)了)。
駱一禾、蘇歷銘、程寶林是所有通信詩(shī)友中見過面的三位。
姜紅偉:在您印象中,您認(rèn)為當(dāng)年影響比較大、成就比較突出的大學(xué)生詩(shī)人有哪些?哪些詩(shī)人的詩(shī)歌給您留下了比較深刻的印象?
彭國(guó)梁:葉延濱、王小妮、徐敬亞、許德民、駱一禾的詩(shī)我比較喜歡,經(jīng)常通信的詩(shī)友的詩(shī)也很喜歡,其它的太久了記不太清了。
姜紅偉:20世紀(jì)80年代大學(xué)生詩(shī)歌運(yùn)動(dòng)之所以風(fēng)起云涌、波瀾壯闊,應(yīng)該說,很多詩(shī)歌報(bào)刊和文學(xué)報(bào)刊居功至偉。據(jù)您了解,哪些報(bào)刊在20世紀(jì)80年代大學(xué)生詩(shī)歌運(yùn)動(dòng)形成過程中發(fā)揮了推波助瀾的重要作用?在您寫詩(shī)的歷程中,哪些報(bào)刊的編輯對(duì)您的幫助比較大?
彭國(guó)梁:對(duì)大學(xué)生詩(shī)歌運(yùn)動(dòng)推動(dòng)最大的刊物(以持久執(zhí)著程度論)當(dāng)數(shù)《飛天》、《詩(shī)人》、《星星》、《青年詩(shī)人》、《滇池》、《綠風(fēng)詩(shī)刊》、《青年文學(xué)》等。
我很幸運(yùn),剛步入文壇即有眾多伯樂悉心扶植、諄諄教誨,也許受當(dāng)年解放軍剛解放云南時(shí),昆明軍區(qū)文化部長(zhǎng)馮牧扶植青年作者的傳統(tǒng)影響吧。五十年代,云南涌現(xiàn)了一批聞名中國(guó)的名作家、名詩(shī)人,如公劉、白樺、公浦、張昆華、劉祖培、周良沛、饒階巴桑等等;當(dāng)時(shí)家喻戶曉的電影,如《五朵金花》、《邊寨烽火》、《山間鈴響馬幫來》、《神秘的旅伴》、《阿詩(shī)瑪》等,均出自這批青年作家之手。所以,云南的前輩作家在扶植新人、青年方面,有良好的傳統(tǒng),我是最受益者之一。
對(duì)我?guī)椭畲蟆⑴囵B(yǎng)最多的編輯,當(dāng)數(shù)《滇池》雜志的詩(shī)歌組長(zhǎng)米思及老師,我的第一首詩(shī)是他發(fā)表的,以后關(guān)系日密、感情日深,已超越了師生、編輯和作者關(guān)系,成為忘年交,我每有新作皆會(huì)先讓他看,征求意見,后來發(fā)展到他竟很信任地讓我?guī)退踹x投給《滇池》的稿件,對(duì)我初選的稿件,逐一評(píng)價(jià),這一階段對(duì)我的創(chuàng)作、鑒賞水平提高很大。可以說,當(dāng)時(shí)小有名氣,或已聞名詩(shī)壇的詩(shī)人的投稿,我?guī)缀醵际堑谝粋€(gè)閱讀者,也許,因?yàn)槲沂谴髮W(xué)生的緣故吧,我的傾向性也強(qiáng),所選之詩(shī)多為大學(xué)生的詩(shī)。《滇池》當(dāng)時(shí)所刊詩(shī)歌頗受大學(xué)生喜歡,我自覺還有我一份功勞。
米思及老師為人耿直、公平公正,后來我小有名氣時(shí),他曾對(duì)我說:“彭國(guó)梁呀,你現(xiàn)在到外省大刊物發(fā)作品不困難了,《滇池》今后每年最多發(fā)你兩次,多留點(diǎn)機(jī)會(huì)給其它小青年吧!”幾十年過去了,這句話我至今記憶猶新。
云南當(dāng)時(shí)發(fā)行量達(dá)60萬份的《春城晚報(bào)》有一個(gè)“山茶文學(xué)副刊”,其負(fù)責(zé)人胡延武老師也是我的詩(shī)歌啟蒙人之一。《春城晚報(bào)》第一次發(fā)表我的詩(shī),鬧得四鄰震動(dòng),我的鄰居、父母親的同事都知道了,紛紛對(duì)我父母說:“你兒子了不起,《春城晚報(bào)》上有他的作品。”和胡延武老師也建立了師生,好朋友的關(guān)系,我的個(gè)人作品討論會(huì)、詩(shī)作獲獎(jiǎng),《春城晚報(bào)》都予以報(bào)道,發(fā)表作品就如同在自家的自留地摘果一樣。2012年11月8日,我過50歲生日,邀請(qǐng)了一群國(guó)內(nèi)知名企業(yè)家和云南的老師、詩(shī)友們齊聚昆明,胡延武老師欣然參加,他當(dāng)著詩(shī)友的面問我:“彭國(guó)梁,你還記得嗎?有一次你拿了首情詩(shī)找我,說三天后是你女朋友生日,想在《春城晚報(bào)》發(fā)表這首詩(shī),送她做生日禮物,我在你女朋友生日那天給發(fā)表了。”我說:“當(dāng)然記得。”當(dāng)時(shí)有詩(shī)友說:“原來彭國(guó)梁這么狂呢?你以為晚報(bào)是你家的呢。”
三十多年后說起這段往事,我真是心潮澎湃,我和胡老師的關(guān)系由此可見一斑。
云南的文學(xué)名家,如曉雪、周良沛、饒階巴桑、張長(zhǎng)、張昆華,對(duì)我這個(gè)20出頭的小青年當(dāng)時(shí)也是倍加呵護(hù)關(guān)心。
我記得《大西南文學(xué)》的詩(shī)歌組長(zhǎng)張永權(quán)老師,也對(duì)我倍加提攜,一有外省編輯到云南組稿,說起新人,對(duì)我、于堅(jiān)、劉揚(yáng),他都熱情推薦。
雖然已過去了近三十年,我依然記得甘肅《飛天》雜志開辟了“大學(xué)生詩(shī)苑”,在全國(guó)大學(xué)生中影響巨大,我很幸運(yùn),第一次投稿即被選中了一組三首“寄自瑞麗江畔的詩(shī)”,張書紳老師經(jīng)常來信教誨,情真意切,至今難忘。我記憶最深的是,我參與創(chuàng)立“紅土高原詩(shī)派”,張書紳老師在給我的信中,說過一句經(jīng)典的話,他說:“一個(gè)流派起來了,詩(shī)人的個(gè)性就倒下了(當(dāng)然,流派中創(chuàng)始人不在此列)”這句話我銘記至今,在日后創(chuàng)立推廣品牌時(shí)也始終不忘。
大學(xué)期間,扶植關(guān)心過我的編輯、名詩(shī)人很多,如《星星》的鄢家發(fā)老師、《詩(shī)刊》的王燕生老師、《人民文學(xué)》的韓作榮、冼寧老師、《中國(guó)青年報(bào)》的董月玲、《青春》的吳野、馬緒英老師、《百花園》的王中朝、《北方文學(xué)》的王野老師,還有《詩(shī)人》的梁謝成老師,《青年詩(shī)人》的何鷹老師和《人民日?qǐng)?bào)》的一位老師(因年代久遠(yuǎn)記不清編輯的名字了),都對(duì)我培養(yǎng)扶植、亦師亦友。
真應(yīng)了著名作家白樺的一句名言:“春天對(duì)我如此厚愛。”
姜紅偉:當(dāng)年您擁有大量的詩(shī)歌讀者,時(shí)隔多年后,大家都很關(guān)心您的近況,能否請(qǐng)您談?wù)劊?/p>
彭國(guó)梁:一九八八年下海,無意中被命運(yùn)推到了健康產(chǎn)業(yè)掌門人的位置,商海拼搏,漸漸遠(yuǎn)離了詩(shī)歌。記得那是在一九九一年的十月份,當(dāng)時(shí)影響極大、訂閱范圍至全國(guó)各基層團(tuán)支部的《中國(guó)青年報(bào)》通知我,我第一次寫作的散文《荒原上的小店》獲得了該報(bào)紀(jì)實(shí)文學(xué)一等獎(jiǎng)。此時(shí),我已以不足30歲的年齡出任當(dāng)時(shí)中國(guó)最大的保健品企業(yè)——太陽(yáng)神集團(tuán)的東北公司總經(jīng)理,正率團(tuán)隊(duì)奔赴市場(chǎng),所以無暇參加頒獎(jiǎng)儀式,這是我與文學(xué)界的最后一次聯(lián)絡(luò),沒想到,竟如故人分手,一別就是二十三年之久。在這23年間我雖也偶爾動(dòng)筆寫詩(shī)緬懷舊友、追懷往事,但與文學(xué)界的接觸卻從此中斷了。
商海沉浮二十余年,我曾創(chuàng)立打造了不少業(yè)內(nèi)知名品牌,但內(nèi)心始終未敢忘記詩(shī)歌,我一直視它為我生命中的精神家園。
首次出訪法國(guó)時(shí),我曾經(jīng)久久漫步在塞納河畔,一遍遍吟頌阿波利奈爾的《米拉波橋下》;在先賢祠中尋找詩(shī)歌大師,與大師們的靈魂對(duì)話。
一次出訪德國(guó),世界500強(qiáng)德固賽的高級(jí)總裁宴請(qǐng)我時(shí),專門挑選了一處幽靜的古堡,席間他說:“彭先生是詩(shī)人,這是當(dāng)年歌德常來吃飯的地方。”此事令我感佩不已,深感自己因涉足藝術(shù)而被人尊重的無限榮光。
姜紅偉先生不知從何處獲得我的電話,與他通話的片刻間,一股青春的暖流一時(shí)間涌上心頭,熱遍全身。是啊,商海二十余年,我的一個(gè)簽字可以決定一個(gè)人的貧富、榮辱,但我一次次告誡部下:“鳥翼上系了黃金,這鳥就永遠(yuǎn)不能飛了”(泰戈?duì)栐?shī)),竟無人知曉何意,也無人理會(huì)。
詩(shī)歌,這門高雅的藝術(shù),現(xiàn)在,如山間清泉在穿過人欲橫流的大都市時(shí),被金錢污染得不成樣子了,以至于一個(gè)泱泱文化大國(guó),竟讓韓寒、郭敬明之輩擁有粉絲萬千、馳騁文壇、占據(jù)熒屏,不能不說是國(guó)家、民族的一大悲哀。感謝姜紅偉先生為寫詩(shī)歌運(yùn)動(dòng)訪談錄對(duì)我的采訪。這仿佛把我又領(lǐng)到了一片純情的青草地,讓我又一次重返精神的家園。
88年下海至今,歷經(jīng)磨難,曾執(zhí)掌過多個(gè)大型健康企業(yè)和上市公司,領(lǐng)導(dǎo)過的部下有幾萬人之多,現(xiàn)以自己公司專注做解決食品安全(清除農(nóng)藥殘留)系列高科技產(chǎn)品,自覺是在做一件功德無量之事。
我感覺自己活得很健康、很充實(shí),但也很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