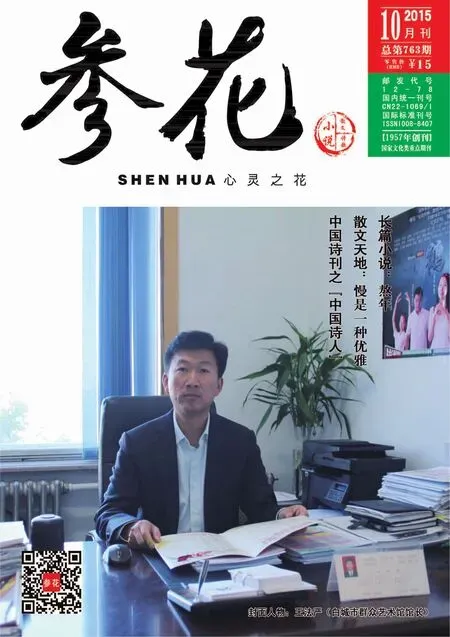鄉 愁
◎ 向以鮮
鄉愁,簡單地說,就是對故鄉(地理和精神層面的)一種眷戀情懷。故鄉就是我們的出發點,也是我們最終要回去的地方。故鄉對于一個人的影響是一生的,且別無選擇。故鄉是我們的回憶之母,我們向心靈回溯的溫暖之源。我們知道美國作家福克納(William Cuthbert Faulkner)在小說中,曾構建了一個名叫“約克納帕塔法”(Yoknapatawpha)的世界,實際上,這個令世人著迷的地方就是以作家故鄉密西西比州奧克斯福 (Oxford)為原型而創造出來的。正是這片如“郵票般大小”寧靜而僻遠的南方小城,蘊育出福克納超凡入圣的想象力。故鄉對于任何時代、任何人群而言,都是極為重要的精神財富,尤其是在當下,在人們幾近喪失故鄉之時,我們重返故鄉,記住鄉愁,顯得尤為迫切:沒有故鄉或沒有鄉愁的人,將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沒有故鄉的人,其漂蕩的靈魂將無處安放。
德國18世紀后期的天才詩人諾瓦利斯(Novalis)曾這樣回答關于哲學的提問:哲學就是一種鄉愁,是一種在任何地方都要想回家的沖動。當然,這兒所說的鄉愁,是一種更為形而上的比喻性說法。按照匈牙利學者盧卡奇(Ceorg Lukacs)的解釋,這個故鄉的核心是古希臘史詩時代、那時的生活與本質是同一的,人們更加真實地為實體所充盈,人們與原型家園有著更貼近的關聯,內心流淌著抒情的河流,沒有斷崖,也沒有深淵。人與物、人與天地自然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盧卡奇有如此詩意的描述:星光與火焰雖然彼此不同,但不會永遠形同路人。因為:火焰是所有星光的心靈,而所有的火焰都披上星光的霓裳。后來,這樣的物我同一的境界被割斷,甚至被對立和仇恨起來。因此,哲學家們的鄉愁,就越來越濃重悲傷。要怎樣才能回去呢?另外一位差不多與諾瓦利斯同時的德國哲學家荷爾德林(Hlderlin)認為:要回到故鄉,重新實現原初的統一性,并不能指望哲學,而應該依靠美學、藝術和詩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