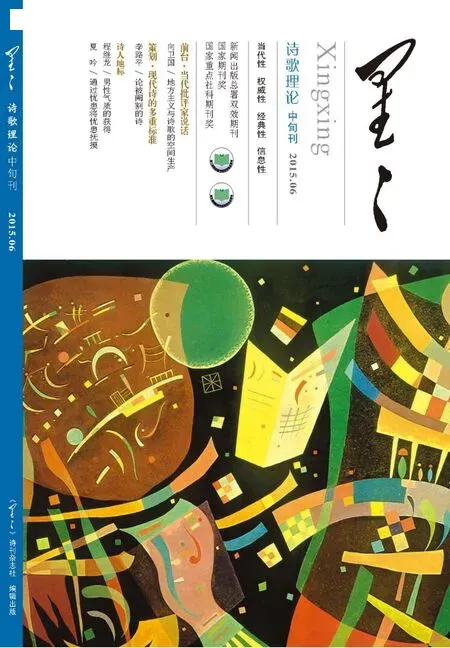論被閹割的詩
李路平
論被閹割的詩
李路平
一
我深知論述這個題目的艱難。
在我從歷史學轉向文學專業批評的那年,細讀過一個朋友送給我的一冊詩歌選本,頗為憤怒也頗為疑惑,我心目中理想的詩歌絕非這本選集中的作品所能體現,我由此寫下了人生中的第一篇比較規范和系統的詩歌批評論文《被閹割的詩》,此前我只是一個純粹的詩歌愛好者,未有接受過文學專業的系統訓練。當我將這篇近九千字的文章一字一段敲到電腦上,放進我的博客時,它給我帶來了好運,它讓我有幸結識了第一位因文結緣的“陌生”朋友兼老師趙衛峰先生,他在以后的某次通話中問我:你怎么寫出這么好的文章?
但這些文字絕非自夸,它在詩生活網站登載之后有了一定的反響,某些時候甚至令我惴惴不安,因為文章中我詳列了自己認可的詩人及作品,并批評了諸多“華而不實”之作,那可是厚達五六百頁的一個選本!曾經在歷史課堂上我便聽老師教導說要謹慎為文,不成熟,容易被人詬病的文字最好不要公之于眾。然而或許我還是一個“不毀(悔?)少作”的人,我覺得人的一生是有不同的階段和狀態,人的想法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一個時段的文字表達了一個時段的真切想法,它們的價值就存在了,至于日后有人責難,倘若我也感到了其中的不足,我定會修正自己的觀點,是為“知錯能改,善莫大焉”,如果我依然“固執己見”,假如不是老糊涂了,我想我還是有自己的立場和想法的。我只是覺得人不能畏首畏尾,因噎廢食罷了。
或許是終究沒有選擇“權威”的選本,而且文章還是一個文學入門者的文學批評“處女作”,它的命運只是在網絡上流傳,不久也便銷聲匿跡了。然而題目的深意我卻從未停止思索,并感到在這個標題下的文字說得太多,也太雜,每個部分都很粗糙,有泛泛而談之嫌。當我想重新使用這個題目再寫一篇文章時,曾師紀虎對我的觀點也很謹慎,他說,現在的文學除了詩歌什么都被閹割了,特別是小說,只有詩歌沒有被閹割。我意識到了寫作的阻力以及可能潛在的壓力,但我理解他的意思,同時這也遇到了本文寫作的第一個問題。
二
我所要論述的“被閹割的詩”,是哪些“詩”被閹割了?
有人說這是詩歌最繁榮的時代,也有人說這是詩歌最糟糕的年代,這些說法都很正常,正如每個時代都會有人說“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而我認為這個時代仍舊是普通的年代,是詩歌兩極分化的時代。
上世紀80年代未,詩歌也有過一次分化,很多詩人都意識到“以前的作品失效了”,或許現在詩壇的分化也是當時流承的余緒?精英的詩人在詩路的最前面不倦探索,不斷為時代創造先鋒的具有震撼力的作品文本,在精神上和智力上為人類積累財富和遺產,而大眾的詩人仍在抒情表意,為時代制造淺顯易懂的精神消費快餐。某種程度上我甚至將這兩部分詩人劃分為“把一首詩寫得不像詩”的詩人和“把一首詩寫得太像詩”的詩人,很明顯后者要占絕大多數。也許我還應該劃分出處于二者之間的第三類詩人?但這與劃分成兩類詩人有什么不同呢?當然這樣劃分存在很大的漏洞,甚至還有邏輯上的悖論,有的人就會據此攻擊:是不是詩寫得讓人看不懂就是好詩(對“不像詩”的質疑)?太像詩的就一定是三流貨色(對“太像詩”的質疑)?
而事實確是:“不像詩”的詩才最像詩,“太像詩”的詩往往最不像詩。如果一個詩寫者存在面臨“青春期寫作”與“后青春寫作”的問題,或者說面對艾略特所說二十五歲之后還要不要成為一個詩人的問題的話,或者就有理由說詩也可以分作與此類似的存在形式:“不像詩”的詩是“后青春寫作”的詩,才是成熟或漸漸成熟的詩,而“太像詩”的詩則仍是“青春期寫作”的詩,是詩寫練習的習作。
因此詩的兩極并非截然分化的,而是存在轉變的可能,而“太像詩”的詩的存在也有了相應的意義,如上所說,它是當下詩壇最普遍的存在,本文試圖論述的也即是此“詩”。
三
換另一種說法,作為最普遍存在的詩歌,也即是在各類報刊雜志上公開發表出來的詩歌作品,在近年來的閱讀印象中,它們帶給我一種“被閹割”的感受,“被閹割”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陰柔的抒情美學。中國人習慣將祖國大地比喻為母親,長江黃河也被稱為母親河,這是否也可認為中國人自古就有一種母性情結,一種偏向于陰柔的文化內涵?然而這樣推理似乎也太牽強。尤其在二十世紀前半期,中國大地處于一種戰火紛飛、民不聊生的苦難境地,一大批優秀的詩人寫出了激昂且充滿陽剛之氣的甚至帶有戰斗性的詩篇,對于弘揚民族精神與激發勞苦大眾的斗志發揮了不可磨滅的作用。如果從特殊時代氛圍的角度切入,似乎也可以說得通,動亂年代的詩歌大多讀來有口號與號角的意味,是詩歌直接介入當下的一種表現,給人“務實”的感覺,而在和平年代,詩歌多是一種主觀抒發,是敘說或感嘆,帶有“務虛”的味道。在經濟占主導的當下,詩歌更是處于“邊緣的邊緣”,主流意識形態的引導某種程度上也削弱了詩歌的力量。
陰柔的歌聲在這個時代不斷傳唱,它必然要帶來的一個后果就是綿軟。溫和的時代氛圍就像溫和的開水,我們知道青蛙在這樣的溫水中是如何一點點放松警惕并最終失去活力的,某種意義上可以將詩人比作青蛙,他們擁有一些近似的習性和獨特之處。綿軟是一種近乎糜爛的狀態,而絕不像晚唐的溫軟,綿軟同時也是無力的表現,是無關痛癢的另一個說法。綿軟的詩就像時代溫水里的泡泡,晃晃悠悠從水底泛向水面,有的在中途就消失了蹤影,有的無聲破裂,在水面激起隱約的漣漪。
陰柔也是被時代消解或者與時代和解,有著陰柔抒情美學的詩歌有著隱忍和麻木的雙重特性,“陰”不是陰郁、陰險,陰柔偏向于“柔”,偏重于抒情時的有氣無力,偏向于刀鋒鈍化的一面,它與時代和生活沒有對抗性(或懷疑)的緊張關系,帶有消極的順從因素。陰柔的抒情是一種片面的抒情,是把個人亮的一面展示給讀者,而把暗的一面隱藏起來,這也是諸多因由混合起來的結果。
瑣碎的日常抒寫。平心而論,瑣碎的日常抒寫不應該成為被指摘的對象。“日常”是一個還沒有被詩壇咀嚼膩味的話題,或者說仍處于繁盛時期。這股潮流亦可追溯到89之后或稱90年代以來的詩歌,詩人集體式的領悟到詩歌必須從一種“反抗”的姿態中解脫出來,從“我們”回到“我”,從歷史回到日常。正如北島所言,“文學在意識形態層面的正面反抗,往往會成為官方話語的的一種回聲”,朦朧詩式的寫作已經不再適應時代,第三代的“反動”適時地做出了回應,他們把詩歌從神壇之上拉下地面,從一種對崇高的建構轉向對日常的書寫,不可否認這些轉向為詩歌展現出一篇別樣的風景,開辟出一塊創造的沃土。詩人們在日常經驗的抒寫中仿佛如魚得水,個體生活的差異也相應地為詩歌的審美提供了豐富的體驗,“日日新”的生活就像一個旺盛的繁殖母體,不斷地為當下詩人提供可資書寫的資源。
正如我在此前的一些文章表達的觀點,當詩人們把目光從天空轉向大地,從遠方回到眼前時,他們目光的容量也必然發生了變化,幽遠深邃的情思少了,更多的是普通實在的東西占據了他們的身心,這并非是指責日常就是流毒毒害了每一個詩人的身心,而是想表達當下日常書寫的作品確實不容樂觀。諸多詩人沉溺于日常的小情小趣之中而無以自拔,“淡淡的憂傷”幾乎是這一類作品共同的背景氛圍,他們如流水賬一般呈現出自己的生活常態,然后小聰明式的在行文中表達一點狡黠或故作深沉地升華主題,“小聰明”也是此類作品的一個顯著標志,它使得這樣的作品好壞比較難判定,小聰明固然在有些時候能夠彰顯大智慧,而這樣的“有些時候”更多的還是與寫作者個人的才華與涵養密切相關,囿于當下的人只能活在當下,眺望遠方的人才有可能深入歷史與未來之中。
日常經驗的引入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對詩歌的一次祛魅,它讓詩歌的功效變得與鏡子相似,當它轉向日常生活時,在其中呈現出來的亦是日常現實,幾乎沒有改動。在這樣的一次轉向中,對詩歌的另一個影響就是對想象力的消解。想象力對詩歌究竟有多重要?這必然是沒有統一答案的問題,然而我始終認為它是詩歌魅力的必然之物,沒有想象力的詩歌就像沒有翅膀的鳥,更像是沒有穿衣服的人,縱然有他的裸露之美,但他失去的遠比他得到的要多得多。日常敘事中幾乎不需要想象力的參與,或者說當下的作品表現出了這樣的一種傾向,有日常事件做框架,再耍點小聰明,一首詩的形制就呼之欲出了,然而其中包含的是什么呢?
與日常書寫相伴而來的就是敘事,本來詩中的敘事也無可厚非,《詩刊》前不久的一期中還做了關于《四兄弟》(老了)的討論,詩歌敘事性的確仍舊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敘事”可以說一直與詩歌相依存,不管是敘事詩中對故事的敘述還是詩歌書寫自身的“敘事性”(可承受范圍內的陌生化)特征,都可以說明敘事性是詩歌所固有的。只是當下有些作品已經淪為小說的分行,或瑣碎的日常記敘,一種詩歌固有的形而上的東西消失的無影無蹤,詩人們沉浸于日常生活之中,甚至忘記了抬起頭仰望星空。
無根的漂泊。當下的詩歌寫作,不僅呈現出“陰柔”與“瑣碎”,更呈現出一種“無根”的漂泊之感。陰柔的抒情美學造就了詩中的“輕”,漂泊、虛幻、若隱若現;而瑣碎的日常抒寫打開了詩歌的潘多拉魔盒,在認同其多樣性的同時也可認為是對主題(母題?)的消解。
當下詩歌中的“輕”是一種不言而明的狀態。年輕的詩人們放下了(或者尚未承擔起)前輩們沉重的思想重負,以新的審美心態進入到時下的詩歌寫作之中,對童話、未知、夢幻的書寫使他們仍被劃入“青春期寫作”的階段范疇,他們對詩的認識與尋找幾乎還是在尚未覺醒的狀態之中。而成熟的真正的與詩為鄰的詩人們那里,正在不倦地抒寫著“不像詩”的詩,因為讀者的審美能力的欠缺而無法體味到文字間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輕”;大多數庸常的寫作者尤其如此,見山寫山,遇水寫水,眼之所見心之所感寫而成詩,詩中之“重”無從找尋,幾乎可算作是旅游之詩。然而詩中的“重”是必不可缺的,沒有“重”穩住一首詩不僅結構松散搖搖欲墜,尤其不能承受時間之風的吹拂,“輕”的詩歌一吹即瓦解,而“重”的詩歌歷經風吹而巋然不動,愈加彰顯出它的質地與光澤,詩之“重”是由作者去追尋并首先體味到的,而且必須承受住,方有能力將它傳播給他人,這也是一個詩人成長的必由之路。
主題的凌亂或消解某種意義上屬于后現代范疇,然而在一個尚未真正現代化的社會談論后現代,本身就有一種滑稽之感。一些宏大的主題(此時談論宏大主題是否也充滿諷刺?)被湮沒了,充斥于詩歌中更多的是一些瑣碎的情感(甚至大多數應算作情緒),名為日常經驗的敏感體驗,實則顯得無關痛癢。我始終覺得真正的詩是寫給時間的,絕非寫給時代,不同時代有不同的生活狀態,真正的詩歌必然能夠超越于時代之上,表達出來的深層次主題仍然是一以貫之的,是對永恒的不斷探尋。主題的凌亂或許也是這個時代的寫照,人們的生活也是一種支離破碎的狀態,消費媒介的侵入使得處身其中的人們難以持守靈魂的靜土,被分割被消解的狀態也是感同身受,只是絕大多數的人們沒有找到可以抱持之物,在時代的大潮中隨波逐流,無法始終恪守內心的某種準則和尺度,并藉此在漫漫的詩歌之路上求索。
這種無根的漂泊特性,于我自身也體會深切,不論寫作還是閱讀、生活,始終都會有這樣的一種感受。我們總是“不能自己”被動地承受著時代給我們施加的一切,深感無力。詩歌應該是有根性的,而且必須是有根性的,所有建構在詩歌之上的理想才有存在的證明及存在的意義,才能被時間記錄。
觀念寫作或偽先鋒。還有一些比較小眾的現象,某些詩人的創作,有的獨樹一幟另立山頭,有的被冠以先鋒的名義,以一己的獨創的詩歌理念進行創作嘗試,這未嘗不是值得肯定的事,然而其中的有些作品,卻背離了詩歌的初衷,成為了對教條的闡釋,或者成為言說某種道理的“詩”。這種帶有觀念寫作性質的創作,仍然在“市面”上橫行。
此“觀念寫作”非劉川先生在闡述新詩標準問題時所說的觀念寫作,而是為了對認可或自創的某種教條性質的詩歌理念加以實踐,為了寫而寫就的創作方式。無可否認,對于一些具有良好理論修養、諳熟詩歌創作的詩人來說,這樣的一種創作方式是自成一格的標志,也是顯示自身創造力的一個重要方面。同樣無可否認的是,這樣的創作成果之中,定然有許多偽劣之作,囿于某種原因而仍舊充斥于這個隊伍里,雖然它們具有很明顯的嘗試特征,幾乎可以看作是某種理論的作品版,即“理論=作品”,然而我們必須對它們表示懷疑:詩歌的出發點應該是詩人內心深處情感的涌動,是混合了詩人體溫的,流動著詩人血液的具有生命力特征的作品存在,倘若加上鋼筋一樣冷硬的理論,自身又像一個半生不熟的學徒,如何讓手中的作品獨立存活于世界中呢?即使它有鮮花以假亂真的外表,它也是塑料花,是徒具形式的偽生命存在。
或許這樣的批評過于嚴厲,如果不加以警醒,這類看似深奧的作品的最終結局必將是“曲高和寡”,被打入“冷宮”之中。此種意義上,這類作品也是不完整、是被閹割過的,它們誕生于異質土壤之中,是另種意義上的二次繁殖,而自身是沒有繁殖能力的。
四
很明顯,行文中的“閹割”并非通常意義上的,此“閹割”非彼“閹割”,但其中也有共通之處,“去勢性”可以說是他們共同的特征,在“被閹割的詩”里,“去勢性”表面了當下的大眾詩歌失去了其原本的“根性”特征,而打上消費時代的印記,詩歌的發聲也由于此種缺陷而顯得殘缺和模糊不清,甚至成為時代的附庸,主動放棄發聲的權利。
“被閹割的詩”凸顯出一種陰性的抒情質地,與海外華文詩歌相比顯得駁雜而缺乏陽剛之氣,它把人拖入一種泛濫的抒情泥淖而無以自拔,囿于東奔西突的昏亂而無法給人明晰的指向,它拋棄了一個傳統,卻還未創造出一個新的傳統,它深陷于自身的矛盾之中。
這是每一個詩人都必須面對的問題,要寫出沒有“被閹割”的詩,則要從他們自身的轉變開始。
(作者單位:廣西師范學院文學院)
詩人地標
主持人語:
陳敬容(1917—1989),詩人、翻譯家,“九葉派”的重要成員。1932年開始詩歌創作,1935年發表處女作。出版有《盈盈集》、《老去的是時間》、《星雨集》等詩歌和散文集子。翻譯有《安徒生童話》、《巴黎圣母院》、《絞刑架下的報告》等。陳敬容的詩歌既有浪漫主義氣質,也有現代主義色彩,并體現出對人生、命運的深度思考,達到了一定的藝術高度,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女性詩人個體。本期推出兩篇文章。程繼龍《男性氣質的獲得》一文認為,從最初紫羅蘭般的少女情懷的抒寫,到戰亂年代向“現實感”和“現代感”的奮力躍進,再到新時期浴火再生后的重新發聲,女詩人陳敬容一路的抒情言志,似乎一直走在“去女性化”的路上,她的詩歌越來越深刻而陽剛,越來越具有男性詩人的普遍氣質。夏吟《通過憂患將憂患撫摸》指出,陳敬容詩歌總體保持了文字優雅、思緒沉靜、行文簡潔、渾厚深沉的特征。格調呈現陽剛氣,內容上有厚重的歷史感和開闊的空間感,詩歌中有通常女性詩歌少有的回味悠遠的力量美。兩篇論文都看到了陳敬容詩歌中“陽剛”的一面,同時又存在一些觀念上的歧異。希望這兩篇論文的推出,可以促進陳敬容詩歌研究的深化。
——張德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