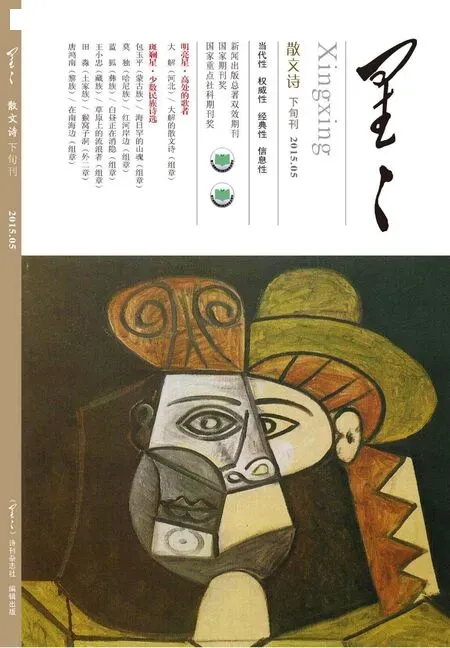猴窩子洞(外二章)
田 淼土家族
猴窩子洞(外二章)
田 淼土家族
田淼,貴州沿河人,土家族。寫作散文詩多年,已在國內多家文學刊物發(fā)表作品,出版有詩集《似與非似之間》。貴州省作家協(xié)會會員。
兀自走來,兀自穿越幽,穿越靜,穿越深,將它的處子之身看遍。
喀斯特地貌在獨奏,在洞中醉意滿懷;石壁用心鎖將自己鎖住,讓暗河在黑暗中舞蹈;面對晶亮的燈火,巖漿大象成形,寵辱不驚。
石頭都長成了花朵,在別致的洞天里縷縷瓣瓣,芳香四溢,蜂蝶們于風的紙張外或忙碌,或徘徊;幽暗的骨子里畫卷長嘯。
寂然中靈光擁抱著暗影,不留下灰色的暗花,讓笑蕩漾起來,形成壯觀的潮聲。
崇山峻嶺宛然蓮花盛開,任憑腳步怎么踩也踩不痛它的嫵媚與嬌艷。
一些按捺不住的鳥語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神情自若;景觀讓激情之心靠近,讓甘冽的秋香打濕渴望世外桃源的眼光。
無言的洞穴向外張開,如祈盼千年的焦渴,永遠接納了那些不斷開墾著的閃光燈熱烈的暴光與激情的撫慰。
小漁溪大峽谷
云樹如織,織就一聲遺世獨立的長嘯。
破山而去,峽谷便心寬體胖,原始的妖嬈楚楚可憐。
森森峭壁,面對贊不絕口的人群,仿佛還要開口說話,話語里深閨錦藏的原始生態(tài)風情萬種。
自南向北延伸,那是最曼妙的臥姿,所有的奔騰盡收眼底。
崖壁無路,腳步便是壯觀;一條狹窄淺薄的鏨道堅韌地醒著,卻讓人們從它濕滑的夢魘中艱難地穿過。
平安在花香里報喜,偶爾也將一些輕浮的贊嘆斷電,將一些瞠目結舌的假設倒掛起來,擰成生命飛翔的路。
水,從谷底下汩汩冒出,沿著清澈蜿蜒的小溪,將夢想寫在遠方,寫在白云深處的雞犬相聞中。魚蝦點亮了水,成為水里藏不住的最坦誠的畫意,蝶舞與蜂飛相伴,在水天一色中煙火旺盛。
沒有苦難自下而上地浮現(xiàn)出來,沒有石頭的悲鳴裸露貧窮與哀傷——
小漁溪,一部天書寫滿了悠然的晨昏與暮晚,寫滿了時間與空間的硬度,也寫滿了刀耕火種與深深峽谷不離不棄的長長拷問。
古皇城遺址
遺址,在枯黃里冷落成秋天的冰塊,用歷史的興亡喚不醒它的溫暖。
一面秋山漠視曾經(jīng)浩大的工程,一片秋林雜陳銹跡斑斑的腐臭。回味呀,歷史的毛病向外裸露,再長的絲線也縫合不了正在隱遁著的遺憾。
明代的鐵器連同那些空曠的號子還撒落一地,偶爾還能看到它們的身影驚現(xiàn)風采,讓我們的心驚悸成很深的傷痕,也許還會永世也不會鈣化。
東門高聳,像要喊出話來,欲把滄桑的身世扶正;陽光冷冷地落在它的肩上,像一場痛罵正在下滑,深淵正無情地向外翻卷,只有一些雜草樹干不知道還在無聲地挽留一些什么!
腐葉將東門的哨所抬高,一塊塊石頭被打磨出痛苦的花紋,它們死死拉住現(xiàn)實移動的腳步不放,還有一些刀槍與弓箭連同石器的命運卡在歷史的彈道里寸步難移。
西門瘦削不堪,單薄的肩頭扛起遍地的枯黃,那些放哨的煙火模糊中漸行漸遠,城墻結痂的暗傷像要立刻從疼痛中醒來,詛咒一場場尸橫遍野后的慘疸。
石頭涌動的心病跌落在城墻根下,巨大的石塊將神力鍛造成君王的九層壘土,那些頭盔,那些鎧甲,那些火藥的腥味無聲地走遠,它們走成饑腸轆轆的野鬼,走成深夜綠瑩瑩哭泣的磷火。還有一些土碗土筷土罐醉臥的身影任所有的毛草全都目不識丁。
陡峻的山岡上,營壘森然,惡血與草葉駁雜,全被螻蟻蛀空了畏縮的心態(tài)。銹蝕的鐘鼓將神圣的光芒坐化,陽光端坐在秋影的看臺上,靜觀深邃而喧嘩的歷史漸漸殘缺。
皇城腳下的村莊,笑意溫暖,眼窩里的秋影將沉重歷史的榮光全部擠空;村莊被歷史扶直,卻用嶄新的面貌割斷每一寸幽暗的歷史傳承,古皇城的殘骸從不被村莊拾起,也從不交給現(xiàn)實打磨成锃亮古跡。
———評《土家族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