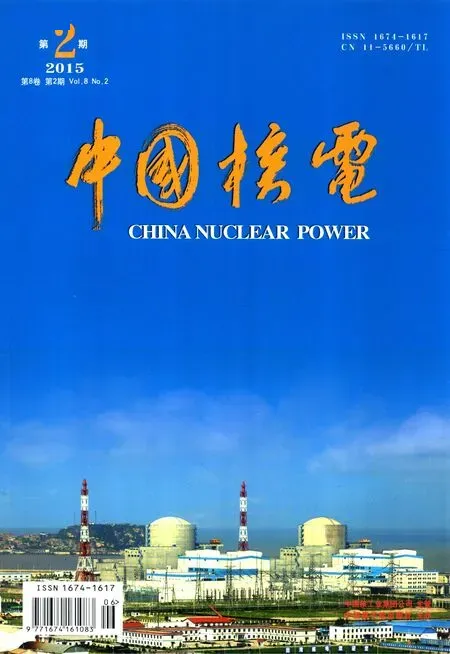核電發展勢在必行,提高核安全文化素養是關鍵
——專訪于俊崇院士
核電發展勢在必行,提高核安全文化素養是關鍵
——專訪于俊崇院士
Nuclear Power Development is Imperative Improving the Nuclear Safety Culture is the Key——Special Interview with Academician YU Junchong

于俊崇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高級工程師,博士生導師。一直從事核反應堆設計研究及工程研制工作,在核反應堆熱工水力與核安全、核動力總體等專業領域有很深的造詣。
集中優勢力量發展核電,內陸核電安全可靠
《中國核電》:經過三十多年的努力,我國核電從無到有,有了很大的發展。我國核電發展呈現多堆型、多技術的多樣性現狀,而世界核電國家目前大多使用一種或兩種技術。您對我國核電的發展以及內陸核電建設有何看法?
于俊崇:對于核電的發展,我國目前這一多樣性的現狀也是我困惑反思的問題。我國的核電發展起步不算太晚,但發展速度有些緩慢。早在20世紀80年代,我國就自主研制了30萬千瓦壓水堆核電站,當時韓國并沒有自主發展核電的能力。而如今,韓國已經將140萬千瓦的核電站出口到其他國家了,我國卻一直處于不斷引進、吸收的狀態。其中的原因我無法分析,但我國核電發展的頂層設計不充分,可能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我認為,一個國家要發展哪幾種核電堆型技術,不僅要考慮這些堆型的性能特點,還要考慮我國的國情和發展這種堆型整個產業鏈(如設備制造、燃料生產和乏燃料的處理等)所需技術研發的方方面面。比如,是不是我國近期發展所急需或是長遠無可替代的發展方向;發展完整產業鏈技術需要多少投入、這些投入是否值得等等。我無能力對我國目前4~5類堆型全面發展做出評價,但縱觀世界,連經濟最發達的國家好像也沒有這樣。就連同一種堆型,如壓水堆,世界壓水堆強國好像也不是像我國這樣有如此強大的三個集團公司,因為這是國務院剛剛批準形成這樣的“三足鼎立”,我希望他們在我國核電發展中猶如“桃園三結義”,而非變成“魏、蜀、吳”。
就我個人觀點,我不反對對新堆型的新技術做探索研究,但反對那些沒有任何技術基礎,或對國家發展戰略意義不大的堆型,馬上就立項開展工程研制,這既不科學,也不符合我國國情。對壓水堆核電站,我不反對多幾個符合資格的運營商,但他們必須對所負責的核電站從“生”到“死”負責到底,而且要與相關方利益共享。這就是說建設在別人這塊干凈的土地上,退役后要還這塊土地“干凈”,全過程產生的三廢,要無害化處理完畢。產生的乏燃料要給子孫后代留足后處理的經費。另外,還應該讓核電站環境內的單位、群眾感受到發展核電給他們帶來的實惠!對于核電技術研發,考慮這是一項高投入的尖端技術,我的觀點是總體技術不宜搞競爭,尖端技術中的常規技術,可以實行市場化競爭;尖端技術中的核心技術,要花大錢的,應組織國力形成拳頭去攻關,也不宜分散力量去競爭,避免重復浪費財力、人力、物力。縱觀國內外的經驗,好像也是這樣,20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國在較短時間內研發出了兩彈一星和核潛艇,就是這樣搞出來的。美國三喱島事故以后,研發概率風險與評價技術,以及現在的數字化反應堆技術,也是這樣搞出來的。概率風險評價技術的最終成果是WASH-1400,并沒有出現張三的PSA,李四的PSA。
關于在內陸建核電站,我的觀點是,我們應該客觀地看待內陸核電的發展問題。目前國家經濟發展、節能減排、改善環境,都需要發展一定數量的核電站。而沿海的核電廠址非常有限,不能滿足發展的需求,所以必須向內陸發展。況且,我國內陸一些地區本來就是缺煤、缺油、少電,地區經濟發展很需要外界能源補充,但往往又要花大價錢。聽說湖南一帶,一噸煤的價格要比沿海地區貴一百元錢左右,這非常影響其經濟發展。所以對于建設內陸核電站的問題,我比較支持,但和沿海的核電廠址選取相比,標準要更加嚴格。因為公眾對于在內陸建設核電站有些疑慮,認為核電站所處的地理位置位于大江、大河的上游,核電站一旦發生事故,對下游的水質影響巨大。其次,有些人認為我國內陸地質結構復雜,多處在崇山峻嶺中,大氣的沉降不利于污染物的擴散,對當地會產生不利影響。另外如地震、河流水庫決壩也會對核電站產生較大的影響。
這些擔心,我認為正是我們在進行內陸核電站選址時需要考慮、解決的問題。但我們也不能因為太離譜的假設來否定搞內陸核電。比如有人說三峽潰壩了怎么辦,這種問題已經不光是建設核電站要考慮的問題了,這應該是沿江城市都需要考慮的問題。但自然災害,如洪水、地震等是必須要考慮的。既不能建在地震帶、斷裂帶上,也不宜選擇大氣擴散條件差的地方。必須選擇不僅在正常情況下和沿海廠址一樣不對環境造成影響,就是在嚴重事故下,通過選擇最先進且成熟的堆型(華龍一號或AP1000)和完善的應急措施,也能保證內陸核電廠周邊水流域和環境安全的地方。
從一定意義上說,健康輿論的培育比建設工程本身的難度還要大。誤會、疑慮一旦形成,想糾正過來,就需要更多的途徑來做答疑解惑。在我國建設內陸核電站是可行的,但需要積極與公眾進行溝通,在認真落實內陸核電站各種設計安全措施的基礎上啟動內陸核電建設。
建立完整的核安全文化概念,把安全意識根植于內心
《中國核電》:關于核安全的問題一直是業界爭論的焦點,核能有其特殊性,特點是低風險、低事故概率,但卻高后果,可能是由于一些認識的偏差導致有些人反對發展核電,請您談談對核安全及核安全文化的理解?
于俊崇:我認為,安全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世界上“絕對安全”的事可能是沒有的,但是我們并不能因此就疏忽核安全,因其特殊性,必須十分重視核安全。其中,核電知識的普及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因為核安全文化的提高是建立在核電知識普及的基礎上。目前,不僅公眾對核知識的認識不夠,就連一些所謂懂核的人對核電方面的知識掌握的也是不夠準確的。我舉個例子,有位專家反對核電,說核電是不安全的,因為核電站的控制要求是毫秒級的,這顯然是不對的,核電站的控制并不是毫秒級的,而是秒級的,由此可以說明,我們在核方面的基本知識普及做得還遠遠不夠。現在我國核電正處于高速發展的時期,涉核的知識內容很多,而且核技術已涉及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們只有對核知識了解之后才有可能正確的對待核,既不恐核,也避免類似把放射源撿回家藏起來,結果導致一家人受到影響的事故再次發生。所以我建議應當把核知識的普及納入科普基本教育內容,甚至從小學起就可開設一些常識性的課程。
在核電站安全問題上,先進的技術和核電廠安全設施水平固然重要,但從業人員的安全文化素養也很關鍵。所謂核安全文化就是要把核安全的理念貫徹到核電站的設計、制造、安裝、運行、維護等全過程之中,只有這樣才能形成一個完整的核安全的概念。
在現實生活中,一談到核安全,大家都知道很重要,但一到具體的事情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我把它說成是“高高舉起,輕輕放下”。歷史上三次嚴重的核事故,我個人認為,都和從業人員核安全文化素養的缺乏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先說美國三哩島核事故,事故的起因是由于設備故障,但是在這個過程中由于運行人員誤判導致事故惡化。切爾諾貝利事故,除了機型和技術上缺陷的原因以外,也是因為操作員違反了操作規程,導致了嚴重事故的發生;福島核事故引起的原因是嚴重的自然災害,但日本國會獨立調查委員會最終把這次事故定位成了“人禍”,指出安全管理當局和業主對安全的漠視,事故發生以后本應該具備的措施卻沒有,就是因為那么幾個不應該被疏忽的問題疏忽了,結果導致嚴重的后果。福島核電站的周圍另有十座反應堆,由于都具備抗大海嘯的措施所以都完好,這說明20世紀70年代的核電技術加必要的措施是能抵御特大自然災害的。因此可以說提高核安全文化素養比什么都重要。
把核安全文化變成一種修養需要一個過程,不是說靠一兩次宣傳就能建立起來的,只有把安全意識扎根于每個人的腦中變成習慣才能真正建立起來。(未完待續)
本刊記者王丹何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