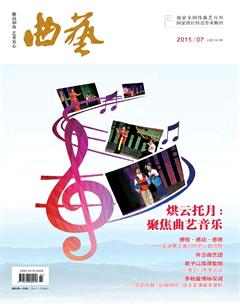懷念曲藝團
姜昆
我非常懷念中國各地的曲藝團。老一代的人們把北京曲藝團叫成“北曲”;天津的則叫“天曲”;把中國廣播藝術(shù)團說唱團稱作“ 中廣”,沒有叫“中說”的。中國有上行下效的傳統(tǒng),湖北武漢、陜西西安、內(nèi)蒙的廣播部門都效仿“中廣”成立過“說唱團”,如果分別叫成“湖(胡)說”、“陜(山)說”、“蒙(猛)說”,那就真成了我們相聲的包袱了。
現(xiàn)在曲藝團基本上沒有了。有的改成了“演藝集團”,有的改成“有限公司”,稍好一點的叫“曲藝傳承研習所”,莫衷一是,聽著特別別扭。
曾經(jīng)有過一次讓我回憶起來非常不是滋味的經(jīng)歷。在2008年的政協(xié)會上,我非常“不識時務(wù)”地和中央領(lǐng)導(dǎo)“犟嘴”來著。其實,我這個人,一直挺有尊重領(lǐng)導(dǎo)的“毛病”,可那天不知道碰著哪根筋了,非得在中央領(lǐng)導(dǎo)和政協(xié)委員開座談會時發(fā)言,“請求”“別再砍曲藝團”了!這不是哪壺不開提哪壺嗎?領(lǐng)導(dǎo)非常不高興,我還任性地現(xiàn)場找人作證,弄得雙方都有點下不來臺。咳,政治上不成熟呀!
解放以前,中國的曲藝團體存在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家族個體形式的,像走街串巷演出的墜子皇后喬清秀夫婦、常氏“蘑菇家族”的班社;一種是以演出場地為基礎(chǔ)的班社類,像北京的天橋,西單的啟明茶社,天津的勸業(yè)場,沈陽的北市場,南京的夫子廟等等,沒有名氣的當班底,有名氣的演員經(jīng)常“趕場”。
解放了,個體經(jīng)濟逐漸退出舞臺,連梨園界赫赫有名的“梅劇團”都沒了,馬連良、梅蘭芳都通過黨的“贖買政策”歸了國家的文藝團體,曲藝團也就應(yīng)運而生。
中國廣播藝術(shù)團說唱團應(yīng)該是中國曲藝的第一大團,不是因為它是中央直屬團體,是因為在成立這個團的的時候,就把中國曲藝最優(yōu)秀的人才集中在了這里。第一任團長是白鳳鳴先生,他是中國曲藝京韻大鼓“少白派”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第二任團長則是出身于部隊,曾經(jīng)任中國人民志愿軍文工團團長,黨培養(yǎng)起來的文藝干部王力葉,他為侯寶林寫過相聲《美蔣勞軍記》《采訪記》,也寫過談相聲寫作技巧的專業(yè)書籍;第三任團長是在中南海當過宣傳隊隊長的司遠同志,當年曲藝演員在中南海為毛澤東主席等中央領(lǐng)導(dǎo)演出,都離不開他的奔勞;第四任團長是中國新時期相聲的領(lǐng)軍人物馬季。
說唱團成立時,演員陣容聚集了中國曲藝界的“四大金剛”,他們分別是:相聲大師侯寶林、單口相聲大王劉寶瑞、西河大鼓金嗓子馬增芬,京韻大鼓大師孫書筠 。在當時,他們都是各個曲種的領(lǐng)軍人物。 在他們的麾下,郭啟儒、郭全寶、馬連登、馬增蕙、鐘舜華,琴師張志河、陳少武等整整齊齊地列隊其中。有這樣陣容的團體,就不難解釋為什么當時全國的曲藝后起之秀都齊聚在這里:馬季、于世猷、唐杰忠、郝愛民、李文華、趙連甲、趙玉明、劉慧琴、白慧謙、齊桂琴等。說唱團的曲藝優(yōu)秀人才,加上廣電的傳播優(yōu)勢,幾乎撐起了全國曲藝的半壁江山!
北京曲藝團也不甘示弱,把在當時“撂地演出”的名家紛紛招至麾下,單弦大王榮劍臣,北京琴書關(guān)學增,鼓曲名家魏喜奎,快板名師高鳳山,河南墜子馬玉萍,相聲名家王長友、王世臣、高德明、羅榮壽、趙世忠、陳涌泉。有了他們,才有了北京曲藝團趙振鐸、李金斗、梁厚民、王謙祥、李增瑞、種玉杰、張?zhí)N華等后來居上,人才濟濟的場面。
于是,各個曲種的名家,紛紛在各自的曲藝團里獨領(lǐng)風騷,以鮮明的地方色彩成為大師級代表人物。高元鈞、常寶華先生代表部隊;李潤杰、駱玉笙、馬三立先生代表天津;蔣月泉、周柏春代表上海;王少堂、侯莉君代表江蘇;韓起祥代表陜北;紅線女一曲《賣荔枝》進入全國人民的耳中,也讓人們認識到廣東粵曲也在曲藝行列,代表了嶺南曲藝的姣姣風采。就像一個足球隊,運動員各個是好樣的,技藝非凡,但是一定要有球星,一定要有領(lǐng)軍人物帶領(lǐng),才有看點,才有凝聚力。文藝,尤其是表演藝術(shù),人們通常稱為“角兒的藝術(shù)”。曲藝團的人才優(yōu)勢,保證了曲藝的傳承,曲藝團的組織形式,不應(yīng)該輕易去掉,歷史證明它給了曲藝藝術(shù)傳承發(fā)展以保證,為什么非要去掉?改制就在原來基礎(chǔ)上改嘛!好些地方方向改了,曲藝陣地丟了!想起來很痛心。
我懷念曲藝團,但愿我這不是“遺老遺少”般,木頭腦瓜,抱守殘缺的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