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之光
何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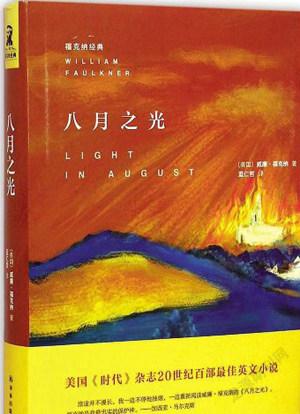
美國作家似乎不太受諾貝爾文學獎評委們的青睞。20世紀以來,在總計100多位獲獎者中,美國人只有11位。對比美國在這100多年里,政治、軍事、經濟、社會生活各個領域里的呼風喚雨,強勢的文化輸出幾乎無所不能,11座獎杯并不是一個良好的成績。
大概歐洲的評委老爺們看待美國的作家,有點看暴發戶的心態。像我們眼瞅著某個新興城市經濟飛速發展了,卻要冠以“文化沙漠”的稱號,提醒這個城市不要把尾巴翹到天上,底蘊還差得遠呢一樣。當然,在美國“暴發戶”里,歐洲大老爺們還是相當敬佩其中兩位的。歐內斯特·米勒爾·海明威算一個,我今天要給同學們介紹的威廉·福克納算另一個。
海明威大家都比較熟悉了,在這一專欄里,我也曾經介紹過他的代表作《老人與海》。“冰山運動之雄偉壯觀,是因為只有八分之一在水面上。”海明威用簡潔直白的語言,只寫出這浮現于水面上的八分之一的故事。另外的八分之七,作者對此不著只言片語。這樣寫作,你說牛不牛?
海明威這種大神,一般人是模仿不來的。不信下次老師要你寫篇作文,你用“冰山理論”創作一下試試。海明威讀得越多,只會讓你作文的得分更低。那這個世界上有沒有看了立即漲分數的小說呢?如果各種“作文指南”已經令諸位產生抗體的話,我推薦福克納的《八月之光》。
該怎么形容這本小說呢?如果說《老人與海》是一個形容枯槁、精神倔強的老頭,《八月之光》就是一位充滿生命力、期待一切也能包容一切的年輕婦人;《老人與海》用寥寥幾萬字寫盡老人的一生,《八月之光》發生在10天里的故事,作者驅策了27萬字去描摹;《老人與海》大巧不工、大智若拙,《八月之光》則濃墨重彩、栩栩如生。
《八月之光》結構復雜,故事的主線由三個人物的經歷交織、穿插而成。農村姑娘莉娜與情人相戀,被拋棄后懷著身孕獨自踏上了尋找情人的旅程;克里斯默斯,從小被送進孤兒院,因為被懷疑是“黑白混血兒”,受到社會種種虐待;海托華,自幼崇拜祖父,對現實世界漠不關心,甚至執意來到祖父喪命的地方,做一位教會牧師。
三個人的命運在美國南部小鎮杰弗生鎮短暫交匯,莉娜再次被情人拋棄,她憑借與生俱來的寬容和仁慈,生下孩子并找到真愛。海托華為莉娜接生之后,感受到生命的活力,重新回到了現實世界。克里斯默斯因為不堪社會的敵視,殺死了寄宿屋的白種主人,最終被鎮上的白人們公開處死。
我這么簡單描述一下,似乎把福克納的代表作,描述成了腦殘編劇的思路。其實福克納下筆是頗有深意的。克里斯默斯(Christmas)在圣誕之夜遭人遺棄,他來歷不明,受盡屈辱,最后在眾人的注目下承受酷刑死去。評論家們指出,克里斯默斯其實是耶穌受難記在現代美國的翻版。

莉娜的故事雖然篇幅比重較小,卻構成了故事的主線。她因為意外受孕踏上旅程,很容易讓西方的讀者聯想到圣母。更重要的是,莉娜對于人生的境遇有著超脫的感悟,任何艱辛似乎都不能在她心底激起漣漪。等嬰兒出生之后,她費盡力氣找到孩子的生父,對方幾分鐘后旋即撒謊再度逃離。莉娜“心甘情愿”放他走掉,只是發出了一聲嘆息,“現在我又只好動身了”。莉娜與其說是福克納塑造的一個人物,不如說是他有意運用的一個雋永象征,象征的是美國南方社會里亙古不變、坦蕩無憂、樸實無華的自然人生。有人說,所謂“八月之光”,就是莉娜的人性光輝。
然而這些并不是我介紹給同學們揣摩學習的。說句實在話,微言大義是福克納這類作家的題中應有之意,否則寫什么嚴肅小說,獲什么文學獎呢。我想說的是寫作的方式和技巧。戲法人人會變,境界大有不同。我們已經看過海明威是怎么變的,我們再來看看福克納。
莉娜和克里斯默斯無疑是《八月之光》的主角,他們人生最華彩的樂章,同時發生在一個相對狹小的時間(10天)和空間(杰弗生鎮)里。然而兩人并沒有交集,他們無須認識也的確互不認識,在故事里擦肩而過。但福克納從小說主題、人物遭遇、事件、行動、用品、話語、意象等細節描寫上,巧妙地大量采用了對置、對位、對應、反襯等手法,構成了不同線索之間的契合與張力,維系了小說的整體結構。
比如說,莉娜和克里斯默斯都是孤兒,曾被另一家收養,最后都以越窗的方式逃走;在同一個星期五,莉娜搭乘馬車懷著希望去會見情夫,朝杰弗生鎮悠緩地前行;克里斯默斯卻心懷殺機地消磨著時光,等待夜幕降臨去行兇;莉娜來到杰弗生鎮的一周正是克里斯默斯逃離該鎮的時候;莉娜的嬰兒在星期一誕生,克里斯默斯卻在這一天慘遭殺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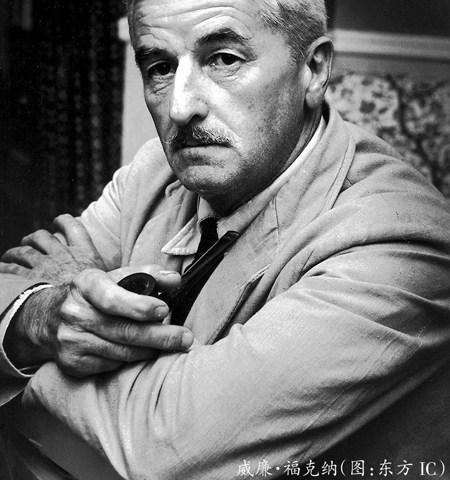
在談到《八月之光》的創作過程時,福克納說:“除非像驚險故事那樣沿著一條直線發展,否則一本小說只能是一系列斷片。這多半像是裝飾一個展覽櫥窗。要把各種不同的物件擺放得體,相互映襯,需要有相當的眼力和審美情趣。”
為了打造一個內涵豐富的“展覽櫥窗”,以便于諸多人物的經歷交錯上演,福克納甚至創造了“約克納帕塔法世系”這個人類文學史上的重要概念。“約克納帕塔法”這個繞口的名字來源于契卡索印第安語,意思是“河水慢慢流過平坦的土地”。簡單說,“約克納帕塔法”是一塊作者心目中的土地。福克納一生創作了19部長篇小說和75個短篇故事,其中15部長篇和絕大多數短篇小說均以這個虛構的王國為地理背景,《八月之光》里的杰弗生鎮也位居其列。
福克納甚至繪制了一份地圖,這個虛構王國位于密西西比州的北部,北與田納西州交界,在約克納帕塔法河和塔拉哈奇河之間,杰弗生鎮是它的中心。畫完了,作者在地圖上標明,“唯一的擁有者和業主:威廉·福克納”。作者發癔癥到這樣的程度,讀者也真是醉了。
與海明威的簡潔相比,福克納可謂話癆。同樣一件小事,海明威說九個字“繩索在身上留下傷疤”,福克納就會調轉筆頭,另寫六至八章,洋洋灑灑十數萬字交代該傷疤的來歷,然后再回到故事主線去。作家莫言說:“讀了福克納之后,我感到如夢初醒,原來小說可以這樣地胡說八道。”(原話如此,不是我編的)作家略薩曾說:“福克納對小說結構有很大的創造,他是第一個讓我一邊看小說一邊記筆記的作家。”(不記筆記,可能會忘記主線情節)作家馬爾克斯對“約克納帕塔法”也相當入迷,《百年孤獨》里的海濱小鎮馬孔多,明顯是將“約克納帕塔法”移植到了南美。
既然人物如此鮮活地存在于“約克納帕塔法”,福克納描寫起他們來,可謂手到擒來。事實上,《八月之光》里每段文字都是教科書級別。福克納寫克里斯默斯個性怯懦的養母,“‘他爹’,她叫了一聲,兩人誰也沒瞧她一眼。他們也許沒聽見,或者她壓根沒發出聲音。”寫莉娜的流浪漢情人,“大家都明白他像只蝗蟲,只是靠這片國土生存。看起來他一直東游西蕩,現在已經凌亂散落,只剩下一個透明的輕飄飄的空殼,毫無目標地隨風飄蕩。”
福克納還善于為他筆下的人物撒謊,不是說他直接寫出人物的謊話什么的。比如他描寫莉娜踏上毫無希望、不可能達到目標的尋找情人的旅途,文中卻處處是充滿希望、隨時能找尋到幸福的描寫。作為讀者深入體會到,文字是經過莉娜心靈的折射,經過篡改后再傳遞給我們的。這些細節非常精妙,不易描摹,留待同學們自己慢慢體會吧。
在諾貝爾文學獎的獲獎者中,福克納還有一個非常大的優勢,就是他的小說是相對好讀、好懂的。這大概是美國文化帶來的一個好處,因為福克納時刻都在考慮,市場是否能接受他的作品。他本人還長時間擔任電影編劇,熟悉大眾的審美口味。
一本小說,粗讀感覺愉悅,精讀大有收獲。作為讀者,還奢求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