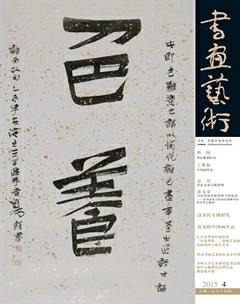惠山“聽松”二篆字論


楊帆 1978年5月生,四川高縣人。宜賓學院教師教育學院講師,南京藝術學院書法(篆刻)創作理論博士研究生。中國書協會員,四川省書協理事兼正書、篆刻藝術委員會委員。書法、篆刻獲中國書協主辦長征展三等獎、第六屆全國篆刻展二等獎,入展第二、三屆蘭亭獎。論文《論李瑞清納碑入帖與沈尹默臨學北碑對當代書法創作之意義》獲中國書協主辦當代書法創作研究國際論壇優秀論文獎。
“聽松石床”,位于無錫市錫惠公園內。原橫臥在無錫惠山寺之聽松亭內,此石六朝時已有,旁有古松兩株,相望于十數步間,故名“聽松石床”。石床長1.99米,寬0.87米,高0.56米,褐色有光澤,平坦微翹,一端如枕,可供盤礴偃仰,故又名“偃人石”。石床翹枕一端之側,長0.63米,寬0.31米,上鐫“聽松”二篆字并政和四年(1114年)題名于右。此二篆字未署年月,亦不著書、刻者姓名,宋人金石圖錄如歐陽修《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皆不載,后人遂將其托名為唐代篆書家李陽冰手筆。陽冰傳世碑版,宋時尚多,歐趙諸書尚著錄之,元、明之后,多見亡佚,雖有重立,但幾經傳刻,已失本來面目,且盛名之下,必多偽托,更有好事者,凡佚名篆書,或題記,或顏署,不辨真偽,皆歸之李陽冰名下,以致魚龍混雜,難以確評。
一、題刻年代與作者
“聽松”二篆字(圖一),清以前金石著錄均不載,其右側百余字之宋人政和四年(1114年)題名(圖二),多剝蝕殘泐,莫能辨識。今據清初拓本并各家題跋釋文,錄題名全文如下:
松石相望于十步外,不知幾何時合而相從,理若有符。政和甲午,睢陽張回仲賢始移而置之。可以盤礴,可以偃仰,遂為茲山登臨勝處,至者當自得之。惟勿遷,勿伐,俾勿壞。同來者六人:□州李永久中、廣陵俞光祖慶(長)、汝南何安中得之、□□□中將之、寺僧奉仙。(六月)丙午。
就內容與形制看,“聽松”二篆字乃金石家所稱之“題榜”。朱劍心謂蘇州“生公講臺”四篆字,及括蒼之“倪翁洞”“黃帝祠宇”兩石,不題書人姓氏,相傳以為李陽冰筆。此體摩崖者多,勒碑者少。唐宋以下,崖壁題名之處,一亭一石,往往錫以嘉名,而大書深刻于石。百余字之題跋,則乃“題名”矣,往者游覽勝跡,湖山佳處,碑碣摩崖,率有題名,姓字年月,亦可供經史考證之資,為宋以來金石學者所珍重。題名中六人已無可考,惟署年號“甲午”,當是北宋政和四年(1114年),乃聽松石床題名之最早者。另石床上平面尚有題名行書21字云:“嘉熙乙亥歲處暑日,止泓趙希袞攜家過此,與嘩侍行。”按嘉熙乙亥為南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年),趙希袞與從侄與嘩均見《宋史》,為太祖九世孫,燕王德昭裔。石床西壁另有一段題名,漫漶頗甚,有“光緒三十年,歲次甲辰十一月廿一日。常州守口化許星壁、陽□□□□王念祖,招游惠山,觀李陽冰‘聽松字”云云。
“聽松”二字首次被書家所訪得并椎拓,史料記載最早者為雍正六年(1728年)三月,篆書家王澍曾率同人往拓之,直以為是李陽冰手筆也。王澍云:
《錫山志》:“惠山寺有石床,在殿前月臺下,長可五尺,廣、厚半之,上平,可供偃仰,故名石床。頂側有‘聽松二篆字。傳是李陽冰筆,蒼潤有古色,斷非李陽冰不能。唐皮日休詩‘殿前日暮高風起,松子聲聲打石床是也。”雍正六年三月,余率同志往拓此書,一時觀者列如堵墻。蓋塵埋經久,莫有過而拂拭者,驟見捶拓,故遂驚為僅事也。右有楷跋石刻數行,日久磨蝕不可復識,悵悒良未有已。
王氏乃清初寫篆之第一作手,好臨秦《嶧山》諸刻及唐李陽冰篆碑,其小篆細瘦干枯,自視為“子昂之后,直至小生,有明三百年來不足多矣”。以此“聽松”二字酷似李陽冰風格,加之以傳聞,遂為往拓之舉。然王氏不辨題名十數行,自然附會方志所言,以為非李陽冰手筆莫屬矣。金石家黃易后得王澍拓本,以為此二篆字古雅飛動,當為李陽冰篆諸刻之上品。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二月,黃氏跋《聽松》舊拓本云:
易家藏此書,古雅飛動,在李篆諸刻之上。先子與虛舟先生論交金石又同學,李篆此本蓋斯時所獲也。易昔年客游吳楚間,扁舟嘗經無錫,總不能系覽登山一訪古刻。屢托人覓拓此書渺不可得,悵惘弗已。
由此,則黃易所得乃王澍舊拓本,亦不辨行楷題名內容,且黃氏亦未親赴惠山摩挲原石,托人拓寄亦不得。其附和前人傳聞,以為“聽松”乃李陽冰篆跡之上品,亦無考也。
乾隆末,翁方綱曾得“聽松”二字并題名拓本,其《跋“聽松”篆》云:
王翁林云此二字蒼潤有古色,非李陽冰不能作。其右有楷跋十數行,石久磨蝕不可復識。今驗拓本,“聽松”二篆之右,尚微辨行楷十行云:“松石相望于十步外,不知幾何時合而相從,理若有口。政和甲午,睢陽張回f□□□□之,可以□□,可以偃仰,遂□茲登臨勝處,至者當自得□。遂勿□,俾勿壞。同來者:□李永久中、廣陵俞光□、汝南何安中得之、□□□□□之、寺僧奉亻。□□□□丙午(原注:以下闕)。”此內有“政和甲午”云云,則文尾“丙午”當是靖康元年也。行楷筆勢似黃石谷,不知何人所作也。翁林見此在雍正六年戊申,今已六十余年,而尚可辨其概。惜不身到其地,手自摩挲,或更有所得耳。
按此題名當是同一時間所題刻,前既有“政和甲午”之語,則題名當作于北宋政和四年(1114年)無疑。翁氏以文尾“丙午”為靖康元年(1126年),顯然是矛盾的,疑此“丙午”不應指靖康元年矣。從所釋題名內容看,其持有之拓本字跡已難辨識,翁氏自會發不到其地之嘆。對于“聽松”二字的作者問題,陳澧曾見翁氏藏本,其上尚有翁氏跋語“世間所傳陽冰書第一”云云,則翁氏仍以“聽松”二字歸之李陽冰手筆矣。
乾嘉間學者桂馥亦曾跋“聽松”二字,并以為惟此二字與《顏氏家廟碑額》是李陽冰原刻,張廷濟有詩云:
少溫暮歲益豪雄,淳勁須尋大歷終。除卻顏家碑額字,更誰筆法到斯翁(原注:桂未谷跋吾家藏本云:“李監跡惟此與顏氏家廟碑額是原刻。”余謂此皆是暮年更妙之作,大歷以后筆益淳勁,趙德甫之評最審)。
張氏曾三次親赴惠山拓“聽松”二字,亦附和桂馥之看法,并以為此二字當是李陽冰暮年更妙之作也。嘉慶十年(1805年),王昶《金石萃編》成,亦將“聽松”二字歸之李陽冰手筆。今人著述中,施安昌《唐代石刻篆文》亦以“聽松”二字托名為李陽冰。殷蓀亦謂李陽冰書“聽松”之篆體書體,修整自持,挾瑰邁之氣,自屬李陽冰刻意致思之作。惟孫星衍、邢澍對此頗審慎,李陽冰諸書篆石刻,孫氏以《李氏遷先塋記》《李氏三墳記》《謙卦爻辭》《怡亭銘并序》《般若臺銘》《城隍廟碑》為李陽冰書,又以“聽松”二字、“生公講臺”四字、“倪翁洞”三字、“黃帝祠宇”四字、“天地清寧”四字為傳為李陽冰所書。
若此,則“聽松”二字出李陽冰手筆似牢不可破矣。然晚清學者陳澧亦曾親至惠山,摩挲原石,考證文字與書刻形制,直接將上述諸家陳說推倒,并認為“聽松”二字必是與題名同時書刻于北宋政和甲午(1114年),非李陽冰手筆也。陳氏《惠山“聽松”二字跋》全文云:
惠山石床“聽松”二篆,其右有行楷題記十行,自左而右,其文云:“松石相望于十步外,不知幾何時合而相從,理若有待。政和甲午,睢陽張回仲(原注:闕一字)始移而置之。可以盤礴,可以偃仰,遂為茲山登臨勝處,至者當自得之。惟勿遷,勿伐,俾勿壞。同來者六人:(原注:闕二字)李永久中、廣陵俞光祖慶(原注:闕一字)、汝南何安中得之、(原注:闕一字)中持之、寺僧奉(原注:此下一字不可辨)。丙午(原注:此下似無字)。”余過惠山,拓而讀之,乃知世傳二篆為李陽冰書者,非也。張回移石就松,則“聽松”二字必移石時所書,與題記當出一手,但不知題名六人中何人筆耳。二篆及題記在石床之頂,其廣僅尺許,故書篆于左方,余為題記地,而題記因之左行。如陽冰先有此篆,題記中何以無一語及之?且陽冰作篆何為偏左?豈逆知后人當有題記耶!云陽冰書者,乃方志無稽之言,而王虛舟《竹云題跋》乃云:“非李陽冰不能作。”翁覃溪且以為世間所傳陽冰書第一(原注:余昔得覃溪藏本,覃溪為釋文及詩跋,書于上方,其跋中有此語)。皆為方志所誤耳。二篆頗圓勁,宋人之筆自為可傳,不必托陽冰為重也。今石床上有亭,亭壁刻道光乙未署無錫縣事曾承顯所為記云:“從佛殿墀東見橫石傾欹,‘聽松二字宛然爰舁出,筑亭覆其上。”蓋昔時此石傾欹難拓,故舊拓題記多模糊不全。昔人不知張回移石事,乃多附會耳(原注:《竹云題跋》云:“楷跋磨蝕不可復識。”覃溪藏本頗佳,然“始移而置之”五字亦難辯,覃溪釋文闕此五字,故亦不知移石事也)。
按陳澧以“聽松”二字必非李陽冰手筆,當為題記中同游者六人之一所書,其理由有三:其一,前人拓本皆不佳,王澍以題名楷跋磨蝕而未識,其往拓乃僅重其篆書也,是為不考,遂附會方志傳聞。翁方綱拓本頗佳,但未辨出“始移而置之”五字,不知張回移石就松事,則此二字必為同來者六人之一所書;其二,若此二字是李陽冰所書,題名內容當語及之,然題名中未有一語及陽冰;其三,從題刻形制看,若是李陽冰所書,不當偏左,豈能逆知有后人題記。
陳澧以張回移石就松事斷“聽松”出自6人之一的手筆,理由未為充90張回等6人移石,則此前石床不在古松旁,“聽松”二字何以必在移石時所書?陳氏以為石移松下,始書“聽松”二字為合情理,然皮日休游惠山有“殿前日暮高風起,松子聲聲打石床”句,則唐末時此石當已在古松之下,且已有“聽松石床”之稱。依陳氏邏輯,皮日休游惠山時石床亦當有“聽松”題刻也,若此,則陳氏多拓得“始移而置之”五字,不足證明“聽松”為張回移石時所書。
從題名內容看,其中確無一語及李陽冰題刻“聽松”事,若“聽松”題刻于張回移石之前,則北宋政和年間必無李陽冰書之傳聞。從題刻位置看,若是李陽冰所書,亦不必僅僅占據偏左一地。云李陽冰書者,當必為元明之后的無稽傳聞,遂為方志所采,后之如王澍、翁方綱、桂馥、張廷濟等亦為所惑也。故此,“聽松”二字托名李陽冰斷不自據矣。
陳澧以“聽松”二字居左,題記因以左行,又證此二字必為移石時所書,是陳氏武斷,不知題名詩刻乃有左行一式。葉昌熾云:
諸山摩崖題名詩刻,往往自左而右,蜀碑尤甚,一部《三巴香古志》,如千佛壓、化城院諸刻,左行者居半。經幢亦有劉恭一刻,蓋其風氣然也。蕭梁諸闕,如太祖文皇帝建陵神道及蕭宏、蕭績、蕭正、蕭映,幾兩闕東西相對者,皆一闕右行,一闕左行。墓志左行者,有后漢乾祐二年《思道和尚塔銘》,經幢左行者,尚有寶歷二年廣州光孝寺一刻。猶憶為鄭盒師校勘沈小宛《范石湖詩注》,原稿書于集之上方,因左邊紙窄,即移而向右書之,一書生錄仍從右起,遂致字字顛倒。
歷來碑碣、摩崖、墓志、題名等石刻,其書刻款式自左而右并不鮮見,此行款方式被金石家稱為“左行”。1965年,徐無聞得陳長孺舊藏“聽松”二字并題名拓本,又于1985年得無錫文物管理委員會所寄題名釋文,徐氏于1988年將此釋文錄于拓本之下,此題名錄文則以自右而左釋之,前后顛倒,卒不能讀也。“聽松”二字居左,題名以左行,與題名詩刻多左行的款式是符合的,則此二字或書刻于題名之前,即唐末至北宋政和之間;或與題名書刻于同時,即出于北宋政和四年(1114年)張回等6人之一手筆的可能性更大。
字書字形與金石文字有不同,當以金石文字為準。《說文解字》乃字書之祖,自東漢以后屢經傳寫,訛誤自不免,裘錫圭云:“《說文》成書于東漢中期,當時人所寫的小篆的字形,有些已有訛誤。此外,包括許慎在內的文字學者,對小篆的字形結構免不了有些錯誤的理解,這種錯誤理解有時也導致對篆形的篡改。《說文》成書后,屢經傳抄刊刻,書手、刻工以及不高明的校勘者,又造成了一些錯誤。因此,《說文》小篆的字形有一部分是靠不住的,需要用秦漢金石等實物資料上的小篆來加以校正。”《說文解字》在唐代,就曾經過李陽冰的刊定,徐鉉云:“唐大歷中,李陽冰篆跡殊絕,獨冠古今,自云‘斯翁之后,直至小生,此言為不妄矣,于是刊定《說文》,修正筆法。學者師慕,篆籀中興。”唐末喪亂,經藉道息,《說文》得傳,實賴陽冰刊定之功。南唐時,徐鍇作《說文解字系傳》四十卷,卷三十六“祛妄”以駁難陽冰之刊定,入宋,徐鉉與句中正等人校訂《說文》,以集書正副本及群臣家藏本備加詳考,亦以見《說文》二徐本與李陽冰校刊《說文》之淵源。
秦李斯篆跡如《嶧山刻石》,雖原石早已佚,然唐宋間摹刻本多有。徐鼎丞所模《嶧山》《會稽》《碣石》諸刻,尚得秦相三昧。由石床“聽松”二字與秦篆刻石、李陽冰篆跡及《說文》二徐本之比較可知,其篆法乃承自李陽冰書篆及《說文》。徐鉉等人校訂《說文》在北宋雍熙三年(986年),“聽松”二字若作于之后一百多年的政和年間,其篆法取自徐鉉校定《說文》或受李陽冰之影響,當是合理的。
“聽松”二字之風格,往昔著錄之家多偽托為李陽冰所作,云其蒼潤有古色,斷非李陽冰所能作。黃易以為古雅飛動,張廷濟則謂是陽冰暮年更妙之作,筆益淳勁。殷蓀謂“聽松”二字,李陽冰篆法之神韻宛在,其用筆之風骨,應為李陽冰書藝故習所隨,其書法之精熟程度,遠非《城隍廟碑》等所能及之。即使如否定為李陽冰手筆之陳澧亦以為此二篆頗圓勁。清乾嘉時期《說文》學極興盛,從方法論講,學者的訪求秦漢碑刻,既可證經史,亦可助益于《說文》之研究,“聽松”二篆字遂得到眾學者之關注,加之其風格頗與代表小篆正脈的李斯、李陽冰相似,又有方志傳聞,一般都誤認為是李陽冰所作也,蓋時代風氣使然。此二字篆法—本陽冰與《說文》,線條圓渾舒展,不作摹刻《嶧山刻石》或陽冰《三墳記》《城隍廟碑》之細瘦狀,與殘本《泰山刻石》及《瑯琊臺刻石》相類,頗具玉著篆之風范。復以刻石之石床頂側并不平整,有如摩厓題榜,隨勢而發,不拘拘于碑刻之方整,頗見變化無方之妙。又石床經久摩挲,風雨侵蝕而點畫殘泐,極具蒼潤古雅之致。
此二字每字高15厘米,寬14厘米,乃大字篆榜也,其氣勢不亞李陽冰作于大歷七年(772年)的《般若臺銘》24字。《般若臺銘》字大如斗,然字字規于界格之中,難以展拓,無此“聽松”之穿插造妙,渾然天成。且輔以右側百余字之題名,前后呼應,布局寓變化于停勻之中,歷代大字篆榜少有此式,亦足供大字篆榜創作之資。
結語
惠山“聽松”二篆字托名唐代篆書家李陽冰不足據。題刻時間或為唐末至北宋政和年間,或出于政和四年(1114年)題名中張回等6人之一手筆的可能更大。“聽松”二篆字乃大字題榜,筆力勁健,與多字題名相呼應,章法天成,足供大字篆榜創作之資。(2015四川省教育廳人文社科一般項目,項目名“鄧石如的‘說文學與篆書創作”,項目號:15SB0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