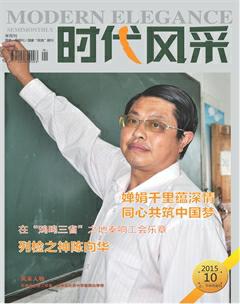僑連四海,彩云之南生死相依
王堯

細雨霏霏,山路濕滑。又一次登上昆明西山,雨中仰望南洋華僑機工抗日紀念碑,陳嘉庚先生的長孫陳立人不禁感嘆:“從1994年開始,我每次到昆明祭拜南僑機工,都會下雨。也許是老天也感念英烈們的赤子之心吧。”
是大后方,是最前線,是大通道。云南,在中國抗戰史上寫下濃墨重彩的篇章。70多年前,華僑華人在這片紅土地上以青春與熱血詮釋赤子之愛的深沉與厚重。70多年后,故人歸來,重溫戰火中的光榮與夢想,憧憬中華民族的美好明天。
為了爺爺的囑托
到昆明之前,陳立人應邀到京參加抗戰勝利70周年閱兵觀禮。9月2日,在人民大會堂,中國國家領導人習近平向其頒發了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章。
“這個獎是爺爺的,我不過是代表家族領獎。爺爺樹立了太高的標桿,后人沒法超越。”陳立人直言。
僑界為抗戰奉獻的無形豐碑上,鐫刻著陳嘉庚大寫的名字。
1939年,中國抗戰最艱難的時刻,東南山河盡陷敵手,滇緬公路成為抗戰生命線。陳嘉庚先生振臂一呼,3900多名南洋熱血青年毅然回國,以方向盤為武器,奮戰在有“死亡公路”之稱的滇緬公路上,1000多人為國捐軀。
陳嘉庚先生一直為南僑機工的際遇奔走呼吁,對犧牲者更是念茲在茲,他囑咐后人,要常去云南代他祭奠長眠于此的華僑青年們。
一個承諾,幾代堅守。10多年前,陳立人開始收集南僑機工的資料,希望找到更多機工及其后人,一一道謝、慰問。“因為他們是響應我爺爺的號召回國參戰的,在這里付出了青春和生命。”住在新加坡、年過六旬的陳立人堅持參加各地南僑機工紀念活動,不辭辛苦。“只要是有南僑機工的地方,我都有感情。我很高興看到,各地對南僑機工的紀念越來越隆重。他們不應該被遺忘。”
與早逝的南僑機工伙伴們相比,102歲的翁家貴和97歲的羅開瑚是幸福的——看到了抗戰勝利,在抗戰勝利70周年之際獲頒紀念章。在這個特殊的日子里,兩位歷經百年滄桑的老人,不顧眾人勸阻,冒雨到西山紀念碑前向戰友們獻上白菊,全程參加了所有紀念活動。
更多的人,不該被遺忘,卻湮沒在歷史的煙云中。“機工之友”侯西反先生的孫女侯韋鎂平實的講述,催人淚下。
侯西反,陳嘉庚先生的得力助手。1942年5月,滇緬公路的咽喉惠通橋被炸斷,南僑機工們集體失業,流離失所,許多南洋華僑也因躲避戰禍涌入云南。侯西反先生親至昆明視察難僑及失業機工,發起組織華僑互助會并被推舉為理事長。他四處奔走,募款求援,設立失業機工收容所,并創辦僑光學校,解決歸僑子女上學問題。
1944年11月10日,一代愛國僑領侯西反的人生戛然而止。為了主持僑光學校新校舍落成典禮,侯西反變更行程回昆,卻因飛機失事不幸罹難。1944年12月3日,昆明社會各界公祭侯西反,萬人空巷,舉城同悲。“侯先生當年葬在昆明東郊福建會館義山,墓地多年前已經被平了。1986年南僑機工成立聯誼會后,幾位歸僑幾經周折找到了他的墓碑并精心保存下來,現存放在昆明市博物館。2014年,侯先生歸葬昆明金陵陵園‘遠征園,他的家人們也有了祭拜之地。”云南省華僑機工歷史研究會常務副會長湯曉梅說。
“戰爭時期,爺爺長眠在昆明,海外的親人無法奔喪,后來聽說出殯時萬人送行,家人悲痛之余感到些許安慰。這些年,我們多次到昆明尋找他的埋骨之地,直到2009年才得知墓碑下落。過去家人對爺爺做的事不了解甚至不理解。近幾年多次從馬來西亞來昆明參加紀念活動,我們深深理解了爺爺先有國才有家的大愛精神,療愈了思念之情。”侯韋鎂說。
帶著“父親”看閱兵
2015年9月,年逾八旬的梁有成老人,成為國僑辦邀請的五名登上天安門城樓觀禮的僑界代表之一。
“收到邀請,我流淚了。當然是因為我父親梁金山在世時對國家貢獻比較大,尤其是在抗日戰爭時期,所以我一個普通老百姓才有這樣的機會。”座談會上,梁有成先生依然心潮難平。
70多年前,原籍保山的緬甸僑商巨子梁金山散盡家財、支援抗戰。他捐巨資修建滇緬公路上的重要橋梁“惠通橋”,捐獻載重汽車80輛、飛機1架。當時國民黨政府派給云南省的救國公債,他一人便購買一半多,此外堅持每天捐盧比100盾支援抗戰,直到抗戰勝利。
帶著父親的照片,帶著媒體報道他捐資救國事跡的報紙……梁有成登上天安門城樓,希望以這種方式讓父親也看到大閱兵。當過兵的梁有成觀看閱兵時心情很不平靜:“看到國家今天的實力越來越強,想起當年日本人打進來時中國那么弱,對比真是太鮮明了。落后就要挨打,這個道理一定要記得。”
云南省僑辦主任楊焱平也感慨萬千:“梁金山的事跡在保山家喻戶曉,外界卻知之不多。這次梁有成先生登上城樓觀禮,體現了國家對梁金山貢獻的肯定和重視。北京觀禮之后,我們邀請他在昆明休整幾日參加之后的紀念活動。梁先生堅持到親友處投宿,紀念活動當天才來報到,不給公家添麻煩。梁金山先生沒有給子女留下什么財產,他的后輩繼承的是為國奉獻的精神!”
在抗戰勝利前的漫漫長夜里,無數個“梁金山”以不同方式為國奉獻、無怨無悔。紀錄片《赤子丹心》,揭開一段塵封的悲壯往事:
1939年,中央飛機制造廠從杭州筧橋遷至中緬邊境的雷允。原來僅有10戶傣族人家的小村子聚集了數千人,大批華僑知識分子趕來報效祖國。
黃玉瑜,1902出生于廣東開平,早年移居美國,1925年畢業于麻省理工學院建筑系,在美國建筑界頗有建樹。1929年回到祖國,為南京、廣州等地的城市建設和建筑教育作出極大貢獻。抗戰期間,黃玉瑜毅然加入中央雷允飛機制造廠,負責廠區建筑設計工作。
1942年5月4日,飛機制造廠人員撤至保山,遭遇日軍大轟炸,傷亡1000多人。黃玉瑜也不幸中彈,傷重不治殉國,家人一直認為他受傷后下落不明。
近年來,在后人、學者與民間團體的共同努力下,這位愛國建筑家的生平事跡與作品漸漸重見天日。
血沃中華,永載史冊。正如國僑辦主任裘援平所說:“海外僑胞為這場戰爭作出的巨大貢獻與日月同輝,他們的業績為世界各國人民所銘記!”
飛虎雄鷹 榮耀歸來
9月6日晚,昆明。在身著空姐服飾的禮儀小姐護送下,15名飛虎隊老兵及2名遺屬在熱烈的掌聲中緩緩入場,接受昆明市榮譽市民稱號。15人中,有多位是祖籍廣東的美籍華人。
別以為陳納德將軍率領的“飛虎隊”清一色是美國大兵,這支部隊各部門都活躍著華裔身影,此次成為榮譽市民的黃煜臻就是其中之一。1943年,他和近千名華裔年輕人應召入伍,編入美國第14航空后勤隊,回到中國參戰。
作為駝峰航線的主要基地,昆明人民與飛虎隊員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盡管飛虎隊在1942年7月解散進入美軍編制,昆明老百姓還是習慣把美國參戰空軍都稱作飛虎隊。
“對這些年近百歲的老兵而言,這是又一次用生命作代價的飛行。”此次活動的志愿者、昆明市民吳南征說。
“一位華裔飛虎隊老兵對我說:我們的戰士受傷甚至犧牲時,云南的老百姓一定會用小板車把我們推到巫家壩機場交給部隊……云南,是我們生死相依的地方。”志愿者蘇瑞流淚了。
航空手語表演《彩云之南》、少數民族歌手合唱《友誼地久天長》……昆明市外僑辦的精心安排,顯示了東道主十足的誠意與敬意。昆明市委書記程連元在致辭中說:昆明人民永遠不會忘記,和中國人民并肩戰斗、冒險開辟“駝峰航線”、積極幫助中國運送戰略物資的美國飛虎隊;永遠不會忘記,1500多名中美空中勇士血灑長空,長眠在喜馬拉雅山和云貴高原的崇山峻嶺之中。昆明人民衷心希望美國二戰老兵、遺屬及他們的親朋好友,能“常回家看看”,共同弘揚和傳承“飛虎隊”精神,共同深化中美兩國人民的深厚友誼,共同開創和平、進步與發展的美好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