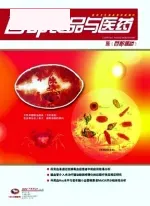平凡的基層醫生
◆本刊記者 房志雄

提起醫生,大多數人想到的可能是忙碌在大醫院各個科室的身影。但您也許忘了,離家最近的大夫可能不是他們,而是工作在鄉鎮衛生院、中心衛生室和社區衛生服務站的那些“白大褂”。作為最接地氣的大夫,他們遠離大醫院的喧囂,扎根在基層。有人說,一位優秀的基層醫生更像是他們身邊懂醫術的朋友。這些基層醫生的日常工作是如何進行的?為了解普通基層醫生的日常工作,記者來到北京市某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采訪了一位居民口中的“朋友”。
居民口中的“王主任”
下午5 時,剛剛下過雨,空氣被雨水濾過一遍,顯然很清新。這天是王大夫值晚班,在一個小時里,來了五六位病人,有的想開藥,有的要做檢查。王大夫一一為他們開了處方或化驗單,并囑咐他們保重身體。一位病人拿著處方走出了診室門口,樓道里遠遠地傳來了一句:“王主任技術好,還特幽默,真好!”
王大夫是一名全科醫生,行醫二十余年。在成為一名全科醫生前,他在一所三級醫院擔任主治醫師,上個世紀90年代,王大夫在一份報紙上了解到全科醫學,于是決定“就去干這個”。這一干就是十幾年。現工作于北京市某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在做專科大夫的那幾年,王大夫發現了許多“瞎得的病”。一到春節,一些人胡吃海塞,得了急性胰腺炎或壞死性胰腺炎。“得這種病很難受,插一肚子管子。”王大夫說,“少吃幾口就不會得這種病,我就尋思平時多跟他們嘮叨嘮叨就可能少發生一例。”
在社區,如果醫生幫助社區居民解決了困擾他們的問題,這些人便會一直找那位醫生看病。“我其實就是一個普通大夫,可找我看病的人總是王主任長王主任短地稱呼我,其實他們把‘王主任’當成了一個尊稱。”
在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社區居民在精神上給予了王大夫很大的鼓勵。一方面,這些激勵著他繼續做這個行當,同時也激勵他不斷地學習、進步。
基層醫生的煩心事
事實上,并不是所有的基層醫生都能獲得社區群眾的禮遇,例如那些畢業不久的醫學生。他們的知識儲備很豐富,可是他們見過的病例太少,實踐經驗也太少,來到社區醫院根本無法應對日常的工作,經常有醫學生面對一些常見疾病而無能為力,因此遭到患者的埋怨,這樣他們的心里也不舒服。
王大夫說,基層醫院需要的是全科醫生。但是,當前的醫學院校和醫院對人才的培養太過于專業,分科太過于精細,醫學生畢業后根本無法勝任全科醫生工作。他認為,當前培養全科醫生的土壤還不存在。“只得等我們這一代人在全科醫生的領域不斷地探索和總結,再過個二三十年,等我們的學生出師了,全科醫生才能算真正培養出來。”
有時候,除了新晉的大夫,“老大夫”們也會很發愁,例如動員社區居民建立健康檔案的事。
“你又不是警察,憑什么給你身份證號!”這是一些社區居民跟王大夫說的原話。王大夫說,這些居民的警惕性很強,一旦涉及自認為與治病無關的個人隱私問題,就變得很難打交道,建檔也就不了了之了。
然而,每年有關部門對各個地區的建檔率是有具體指標的。
“這讓我們基層醫生很為難,有些居民并沒有建檔意向,如果順著他們的意思,我們的任務肯定完不成。”王大夫說,“但如果醫生走上大街,挨家挨戶敲門建檔,大夫們也不愿意去,總覺得有點兒尷尬。”
王大夫不經意地說:“所以,有人就開始作假了。”
再一個讓大夫們頭疼的問題就是熟人買藥。
“經常有一些叔叔阿姨來找我‘點’抗生素吃。跟他們說了多少次濫用抗生素的危害,他們就是聽不進去。總能拿‘我買了先備著,等生病了再吃’一類的話應付我。”王大夫說,“平時跟這些叔叔阿姨關系也挺好的,如果不給他們開,他們就會變得很氣憤。”
患者認為重要的問題就是醫生必須面對的問題
“大夫,我現在是不是要檢查檢查腦子,我怎么感覺健忘呢?以后要是癡呆了怎么辦?比如在廚房做飯呢,想著上陽臺拿頭蒜。到了陽臺,誒,我干嘛來了?回廚房待會。哦,想起來了,要去拿頭蒜,又回去了,就是這樣。”
“您多大歲數?”
“69 了。”
“哦,我姓什么?”
“姓王!”
“那您還不算健忘。我問您,您在走向陽臺的時候想別的事了嗎?您說的這種,年輕人也經常有,這個是記憶興奮點的問題,年輕人更容易犯這個毛病。不用緊張。”
送走了這位阿姨,王大夫解釋道,該患者是3 個月前開始接受治療的老患者,知道他姓王,所以我判斷患者對重要的、感興趣的內容記憶力還行,不過確實有近期記憶減退的問題,需要做一個老年癡呆的早期測評。今天安慰她,主要目的是緩解目前的焦慮情緒,然后再開展其他治療。有的時候安慰也是幫助。
王大夫拿起杯子喝了口水,然后對記者說:“這位阿姨經常來,我們對她的基本情況已經很了解了。問問最近身體狀況、服藥情況就可以了。如果遇見頭一次來的病人,什么毛病都有,哪個醫院的方子都有,我們得跟他說道半天,都得給他捋清楚了。但多數情況下要給他減藥量,因為他吃得藥實在太多了。大醫院經常出現一種情況,比如說血管外科認為病人堵了,開個活血的藥;心內科認為他有斑塊,再開個活血的藥;神經內科認為他有個腦缺血發作,又給他開個活血的藥。然后病人拿著3 種活血的藥找我們來開,我們就必須把藥給減到一種。因為都是活血的藥,但是名字卻不一樣,病人們不懂,但是里邊的丹參、三七、銀杏都重復啊。”
王大夫還介紹說,在社區當中,有時候困擾社區居民的可能就是一些情緒上的問題。當年受毒膠囊事件影響,很多病人來了以后說不敢吃膠囊了。針對當時那種情況,全科醫生就會幫忙看一看有沒有其他制劑的,幫助病人解決問題。過了一段時間,社區居民再重新開始接受膠囊。
“說到底,醫學是個服務行業。”王大夫說,“患者認為是重要的問題就是醫生必須面對的問題。膠囊事件這對醫生來說可能是一件不值一提的事,但卻是社區居民在一段時間內最重視的問題。”
這時候,又一位阿姨走了進來。
“王主任,您好。我想開藥。這是我在醫院開的兩種‘他汀’的藥,我剛去藥房問了,他們說咱這沒有,您看看是沒有么?這個是瞧心臟時給我開的,這個是瞧腦袋時給我開的。”
王大夫聽了這位阿姨的需求,并沒有直接開藥,而是仔細地看了看兩個藥盒,然后把坐在一旁的記者叫到了跟前。“來,你看看。”王大夫說,“神經內科開的是氟伐他汀,心內科開的是阿托伐他汀,西藥這一塊還好辦,社區居民一看都叫‘他汀’,就想‘這倆能一塊吃么’。但是開中藥就會出現這個問題,這個藥是通腦的,那個藥是通脈的,第三個藥是活血的,其實里邊都是三七粉。人們不知道,很容易把藥吃多了。我們基層醫生天天看得都是這個情況,叫病人把醫院開的藥都拿來,病人拿來一捧,總是有幾樣是重復的。”
接著,王大夫轉過頭對這位阿姨說:“您別瞎吃了,周五有時間么?您把從醫院做的檢查和出院志拿過來,我給您看看。”
這時,前一位出去的阿姨又回來了。
“王主任,我說今天先不交錢,明天一起再交,收費的不讓!”
“那您今天這藥也先別拿,明天一塊兒來拿吧。”
“那明天能拿嗎?這單子會不會過期了?”
“能拿,過不了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