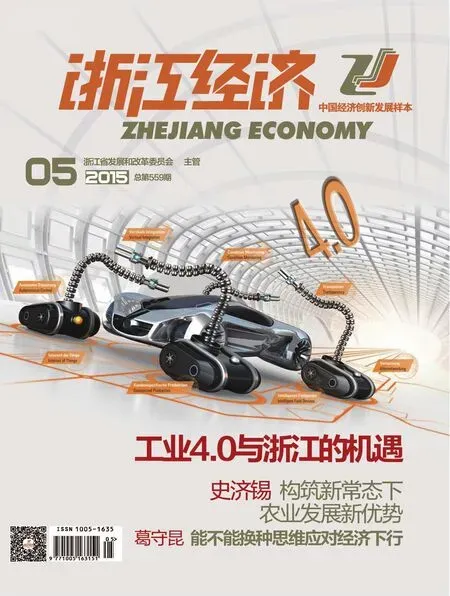說“愚色”
朱國良
說“愚色”
朱國良
常說“一部三國盡間計”,仔細想想,的確是如此。那上面差不多是三十六計的實例講解。就拿“青梅煮酒論英雄”這一回來說,雖說那劉備在聽曹操“說破英雄驚煞人”后,有“失箸”之舉,但卻能夠借驚雷巧掩飾,裝糊涂作愚色,也是“勉從虎穴暫棲身”的一著高招。雖然這恐怕上不了名堂,算不得妙計,但從“聽話聽反話,不會當傻瓜”的反思中,我則深深地感到曹操是梟雄,劉備才是奸雄啊!
善作愚色,實是高手段真功夫。蘇東坡在《賀陽修致仕啟》中寫道“大勇若怯,大智若愚”,這說出了做人的高遠和一種本領,一般人是學不來的。而作為萬物之靈的人的身上,如今愚色更多。本來,世間有些事就讓你想不透。比如,以常情論,人都希望自己多些聰明和智慧,但不知怎么,不少人卻自作多情地成了鄭板橋“難得”的知音,把那四個字高懸于廳堂以自我標榜。欣賞字抑或欣賞意?說不清。總之認為,“糊涂”很不錯。其實,“這鴨頭不是那丫頭”,生活中至少有三類糊涂者雖有愚色卻并不“難得”。
一曰“正宗型”愚蠢。真糊涂者很少承認自己糊涂。比如蔣干,明明頭腦中一盒漿糊,偏硬充多智。赤壁之戰那么大的事,他也敢毛遂自薦,跑到江東跟周瑜套近乎,然后盜書,然后弄得曹操錯殺蔡瑁、張允。他自己卻始終自認為聰明得很——那位使曹操大觸霉頭的龐士元不也是他第一個“發現”并引薦的么?現實生活中,一些連自己的事也懵懵懂懂的正牌糊涂者,辦了一大堆糊涂事,廳堂里還掛上個“難得糊涂”的條幅,豈不滑天下之大稽!
一般看,真正的糊涂者都少有自知之明,倘不幸再混上個或大或小的官兒,糊涂廟里糊涂神,又認定“權力共聰明一體,職位同智慧齊飛”,不想學習也不需要學習,懶于請教又恥于請教,一盒漿糊加十倍獨斷,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經常干些“以己昏昏,使人昭昭”的蠢事,繼之先拍胸脯而后拍屁股。如此育袞袞諸公,“難得糊涂”耶?難得不糊涂耶?掌權之后應深思,絕知此事要躬行。
二曰是“做戲型”裝愚,老百姓叫“揣著明白說糊涂”。“說糊涂”的目的不是為把事辦好,而是出于一己之私,因為要達到個人目的光是聰明不行。《紅樓夢》中的鳳姐很是聰明,“少說著只怕有一萬心眼了”,但太露,又強悍,結果聰明卻被聰明誤了。薛寶釵的聰明不遜于鳳姐兒,但懂“藏愚”之術。“藏愚”即“做戲”,在某些時間和環境下,把自己扮成“糊涂”角色,就很可愛。比如元宵節時,宮里賈娘娘制了個燈謎,派小太監送出來讓賈府的公子、小姐們猜。“寶釵見是一首七言絕句,并無新奇,口中少不得稱贊,只說‘難猜’,故意尋思,其實一見早猜著了”。這與有些人的做官之道就是做戲之道一樣。領導都是聰明的,多聰明的下屬也不能聰明過他人領導;領導也許明白下屬的有意糊涂是做戲,但也愛看,看著舒服。不信你留心觀察,這樣的糊涂戲總有人在做,自然因為有人愛看。
三曰“裝傻型”作愚。民間有“不疾不聾,不做家翁”的說法。細細想去,卻有很多意味。心里明鏡一般,卻裝得渾然不覺,目的是沾“糊涂”的便宜。唐朝武則天時有個婁師德,就是那位主張“唾面自干”的宰相,據說為官為人還不錯。他當御史大夫時,“因使至于陜,廚人進肉,師德曰:‘敕禁屠殺,但為有些?’廚人曰:‘豺咬殺羊’。師德曰:‘大解事豺’。乃食之。”身為御史大夫,掌管刑憲典章,皇上親自圈閱的禁屠宰文件,他當然清楚;廚人信口編造的“豺咬殺羊”的假話并不高明,他也當然很明白。不過,你太清楚和明白了,那烤羊肉就吃不上,所以不說破它,而且贊一句“好解人意的豺呀”,大吃一頓。這位婁大人的“糊涂”是典型的“裝傻型”作愚。
人有愚色,未必不好。“愚”而得當,也不失為一種高境界。但一味裝愚,失去真我本色,似乎也不值得。至于那種愚不可及的“愚”,則是一種悲哀了!

人有愚色,未必不好。“愚”而得當,也不失為一種高境界